宋鹤林彭耜纂集
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
天下莫柔弱于水,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,以其无以易之也。
御注曰:易以井喻性,言其不改。老氏谓水几于道,以其无以易之也。有以易之,则徇人而失己,乌能胜物?惟无以易之,故万变而常一,物无得而胜之者。
临川王安石曰:天下之物能小而不能大,能方而不能圆。水则不然,因地而为小大,随器而为方圆,不失其常,故曰无以易。
王雱曰:水方圆曲直,随物万变而初不易己,此其所以终能胜物也。夫玉石坚强矣,而持以攻物,有时而碎者,以其可易耳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柔之力甚大,日以摩乾驰骋,坚而强者皆不能胜之矣。
陈象古曰:水之为功,善利万物,入污流下,非柔而何?攻坚强者恃力违顺,故不能胜水之柔也。无以易之,其理自然,故不可改易。
清源子刘骥曰:水且尚尔,况于道乎?道之为物,惟恍惟惚,至柔至弱也。
黄茂材曰:上善若水章,言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处众人所恶,与此所言大抵略同。含垢纳污,水之德也。虽为天下王,莫能违之。柔之胜刚,弱之胜强,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。
御注曰:智及之,仁不能守之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夫水之灭火,阴之制阳,舌柔齿刚,舌存齿亡,此天下之莫不知,而世俗之所共闻也。而乃各师其心,莫能行其柔弱之道者,此老氏所以重叹息,故引圣人之言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人非不知而不能行者,何也?以其好强耻弱也。
陈象古曰:水,众人之所见,非难知之物也。莫能行,则信道不明,崇道不笃也。
是以圣人言:受国之垢,是谓杜稷主;受国之不祥,是谓天下王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圣人言者,三坟之遗文也,或老氏之谦也。垢,秽辱也。言人君能含受垢秽,引万方之罪在子一人。子一人有罪,无以汝万方,则民仰德美而不离散,可以常奉社稷而为至矣。又人君能谦虚用柔,称孤、寡、不榖,则四海归仁,六合宅心,是谓天下王矣。传曰:山泽纳污,国君含垢。盖近之矣。
涑水司马光曰:含垢纳污,乃能成其大道。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杜稷之主,如天地之大,江海之宽,容垢包浊,无所不可。祥者,善也。自是则人皆非之,不自善者,人皆美之,故王天下。
叶梦得曰:不祥重于垢,故所受弥多,所得弥大。
程大昌曰:百姓有过,在子一人。小人怨汝詈汝,则曰朕之愆,允若时,是受垢也。人之所恶,惟孤、寡、不谷,而侯王以为称,是受不祥也。二者皆庄子之所谓谦下濡弱也。
正言若反。
御注曰:言岂一端而已,反于物而合于道,是谓天下之至正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夫能行柔弱则为王为主;尚刚强,则招祸招咎。圣人受垢受恶,则永保元吉。世俗乐美乐荣,则终致灾凶。正言俗意如此,乖反明矣。
颍滨苏辙曰:正言合道而反俗,俗以受垢为辱,受不祥为殃故也。
王雱曰:此可为智者道尔。正言若反,反于小智之近情,而合于大道之至正也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皆反于俗见,故曰若反。
陈象古曰:似反于正矣。受垢为社稷主,受不祥为天下王,以言观之,
则似非正;以理观之,则至正矣。
叶梦得曰:此正言而人谓之反,以其言观之也。
黄茂村曰:合于道者反于俗。
程大昌曰:若反而实不反也。
和大怨章第七十九
和大怨者,必有余怨,安可以为善?
御注曰:复雠者,不折镆干,虽有忮心,不怨飘瓦,故无余怨。爱人者,害人之本也;偃兵者,造兵之本也。安可以为善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怨,恚也,恶也,相望也。大怨者,轻生徇死之谓也。夫国君不能无为无事,谦卑柔弱,而民乃多欲好争,奸诈并兴,怨恶相望,心气不平,遂使轻生徇死之徒攘臂于道术矣。而国君设教立法以绳之,其杀人者死,伤人者刑,而和报其恚恶怨望也。然以事和之,则翻济其怨。故知有怨而和之者,未若无怨而不和也。徒知和其大怨,而不省其大怨之所由兴,虽和之以至公,而不免有余怨。若乃大小、多少而以无心至德报之者,几乎造物哉!夫圣贤本以刑政和报其怨恶,奈何奸诈愈甚而怨望益多也。如是则安可以为善?
颍滨苏辙曰:夫怨生于妄,而妄出于性。知性者不见诸妄,而又何怨乎?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,故外虽和而内未忘也。
清源子刘骥曰:为治者不能无事无为,至于有大怨而后和之,必有余怨,安可以为善?
黄茂村曰:夫人不怒虚舟,不怨飘瓦,以其无心而已。若以为怨而和之,是有心也,安能无怨?不足以为善。
程大昌曰:怨之大者,莫大于两国干戈之雠矣。聘会以平之,诅盟以要之,皆求有以和之者也。然会稽之栖,厌然臣妾也,而尝胆抱冰,藏毒伺衅,多历年所,乃始发见。则阳浮道以示相平者,岂其可信也?况夫攻夺人之城邑,杀戮人之父兄,借使敌国之君迁延未肯轻动,而其人民子弟含痛茹耻,必且随事从臾以期报复者,人情之常也。故曰:安可以为善?
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李荣曰:古者圣人刻木为契,君执于左,臣执于右为信。又陆希声曰:圣人之心与百姓心,犹左右契耳。契来则合,而不责于人,故上下相亲,怨恶不作。
颖滨苏辙曰:契之有左右,所以为信而息争也。圣人与人均有是性,人方以妄为常,驰惊于争夺之场,而不知性之未始少亡也。是以圣人以其性示之,使之除妄以复性,待其妄尽而性复,未有不廓然自得,如右契之合左,不待责之而自服也。然则虽有大怨怼,将涣然冰释,知其本非有矣,而安用和之?彼无德者,乃欲人人而通之,则亦劳而无功矣。
王雱曰:左契取于人,右契取人,左无事而右主权,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。圣人执左契,不从事于物,而物自来合,吾应其合者耳,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。然则圣人常受天下之责,而无责人之心,是以终无怨。庄子曰:以得为在人,以失为在己。汤曰:万方有罪,罪在朕躬。此之谓也。记曰:献牛马者操右契。盖献者并券以进,是知左契乃受责者之所执。史记曰:操右券以责事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左,阳也。契,合也。左契者,天道也。天道无私,民之善恶自与吉凶相契。圣人非故责人而或子之,或夺之,但司之而已。吉凶祸福,皆民自为之也。故不私其恩,而终无归其怨。
达真子曰:左者,心之所处。契者,言其合也。圣人执心以合道,而不责于人。
清源子刘骥曰:古者结绳以为治,破木以为契,君执于左,臣执于右,契来则合,所以取信。
黄茂村曰:道无求于世,待其自至。同焉者,合而已。譬如契有左右,执其左契以待其来,合者何责于人?故有德司之。
程大昌曰:献粟者执右契,汉之剖竹为符也。右留京师,左以授守臣,谓之左符。其意度制作,皆与此应也。
故有德司契,无德司彻。
御注曰:乐通物,非圣人也。无德者,不自得其得,而得人之得,方且物物求通,而有和怨之心焉。兹彻也,祗所以为蔽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夫有德者,中古之君也。无文书法律,但刻契合符以为信约,则民自从化,故称有德也。无德者,谓远古之君也。德大无名,物皆自然,而穴处巢居,各安其分。故其君无思无虑,朝彻而见独,不为不恃,道冥而德渊,更无契可司,但司其通彻而已矣,故称无德焉。
临川王安石曰:司彻通于事,则不能无责于人。不能无责于人,则不能使人之无怨。此其所以为无德也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司契以天道契于臧否,司彻欲以聪明尽其民情,而民情安能尽之?故与则为恩,不子则为怨。
清源子刘骥曰:有德司契,亦犹是也。有德之人,真性内明,通玄究微,若合符契,而不求之于人,故谓之司契。无德之人,真性未明,博学多识,以务通彻,而不求之于己。
黄茂村曰:彻者,通也。庄子曰:乐通物者,非圣人也。
林东曰:圣人轨左契,不从事于物,而物自来合,吾应其合者耳。故有德之人司契,如右契之合左。彼无德者,乃欲人人而彻通之,则亦劳而无功矣。
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
御注曰:善则与之,何亲之有?
碧虚子陈景元曰:夫天道无所私,唯善人是与,是谓天网恢恢,疏而不失。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会,何用司契而责于人哉!此复太古之风也。
颍滨苏辙曰:契之无私,亦犹是也。惟合者则得之矣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非亲而与之,而善人自与福契,此天道也。
清源子刘骥曰:契之无私,亦犹是也,惟合者得之。
黄茂材曰:天无私亲,善则与之。为善者,非特无求于人,亦无求于天,待其自至而已。
小国寡民章第八十
小国寡民。
御注曰:广土众民,则事不胜应,智不胜察,德自此衰,刑自此超,后世之乱自此始矣。老氏当周之末,厌周之乱,原道之意寓之于书,方且易文胜之弊俗,而跻之淳厚之域,故以小国寡民为言。盖至德之世,自容成氏至于神农,十有二君,号称至治者,以此而已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国小能自守,民寡能自足,可以返乎太古矣。
颍滨苏辙曰:老子生于衰周,文胜俗弊,将以无为救之,故于其书之终,言其所志,愿得小国寡民以试焉,而不可得尔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小国民少而事务亦简,若数口之家,衣食粗足,无所用心。又以小为大,则张大而劳;以大为小,则简静而佚。
叶梦得曰:国之不能治,以大视之也;民之不能安,以众视之也。夫孰知有以大为小,以多为少之道乎?是故国大而以大治之,民众而以众为之,则有终身不能胜者。圣人之道无他,亦曰小国寡民而已。普天之下不为不广,率土之滨不为不多,而吾未尝知其广且多也。
清源子刘骥曰:本在上,末在下;要在主,详在臣。天下虽大,其本甚小,故言小国;百姓虽多,其要甚寡,故言寡民。
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。
颖滨苏辙曰:民各安其分,则小有材者不求用于世。什伯之器,则材堪什夫伯夫之长者也。
使民重死而不远徙。
御注曰:其生可乐,其死可葬,故民不轻死而之四方。孔子曰:上失其道,民散久矣。远徙之谓欤?
涑水司马光曰:爱生安土。
王雱曰:乐生遂性,故重死。安土无求,故不远徙。无道之世,贫薄士多,而利欲胜乎好生,末盛本衰,而食求在乎分外,故触刑陷险,如履平地,而车辙足迹交于四方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千金之下必有勇夫,故民重利而轻死。邦小民寡,家给事希,故乐土而不迁。
陈象古曰:人各自足以全生意,故重其死。少欲寡求,不必远就其利。
虽有舟舆,无所乘之;虽有甲兵,无所陈之。
御注曰:山无蹊隧,泽无舟梁,同乎无知,其德不离。无绝险之迹,故虽有舟舆,无所乘之。无攻战之患,故虽有甲兵,无所陈之。
临川王安石曰:民自足于性分之内,则无远游交战之患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水行则用舟,陆行则用舆。今既乐其土不迁,弗远徙而就利,民不相往来,故无用。大国不侵,小国守土,介胄戈矛,不战安用?
陈象古曰:寡欲易足,民共不争,故舟舆可闲,甲兵可偃。
清源子刘骥曰:淡然自守,不相往来,故虽有舟舆,无所乘之。恬然自足,不相纷争,故虽有甲兵,无所陈之。
程大昌曰:难于就死,则必乐生,故无盗。无盗则甲兵为虚设。安土而无外慕,无外慕则不他徙,故舟舆为长物也。
使民复结绳而用之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今将使人忘情去欲,归于淳古。
颍滨苏辙曰:事少民朴,虽结绳足矣。
清源子刘骥曰:彼民各有常性,耕而食,织而衣,含哺而熙,鼓腹而游,其行填填,其视颠颠,可以同于上古至德之世,故使民复结绳而用之。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俗,乐其业。邻国相望,鸡犬之音相闻,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。
程大昌曰:庄子备举此语而致诸伏羲、神农以上,且推论后世之失曰:今遂使民延颈举踵曰:某所有贤者,裸粮而趣之。足迹接乎诸侯之境,车轨结乎千里之外。是上好智之过也。好智而无道,则天下乱矣。故夫结绳之可复也,其必自民无外慕者始也。则愚其智,使入于无欲者,又绝其外慕之本也。
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俗,乐其业。
御注曰:止分故甘,去华故美,不扰故安;存生故乐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夫君上无欲,而民自朴。嗜好不生,民乃知足。虽蔬食藜羹之粝,而饱满淡味为甘;葛衣鹿裘之粗,而温凉无文为美;茅茨蓬荜之陋,而风雨不侵为安;南炎北沍之苦,而水土任适为乐。
涑水司马光曰:虽疏恶隘陋,自以为甘美安乐。
颍滨苏辙曰:内足而外无所慕,故以其所有为美,以其所处为乐,而不复求也。
陈象古曰:易自足也。
邻国相望,鸡犬之声相闻,使民至老死不相与往来。
御注曰:居相比也,声相闻也,而不相与往来。当是时也,无欲无求,莫之为而常自然,此之谓至德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邻国相望,犹今郡县之相接也。鸡犬之音相闻,谓民丰而境近也。民至老死,言无战敌而寿终也。不相往来,犹鱼相忘于江湖,人相忘于道术也。此可以同赫胥、尊卢之风矣。
颖滨苏辙曰:民物繁伙而不相求,则彼此皆足故也。
临川王安石曰:夫德之被于民,及其极也,则能使民无知无欲。惟知耕而食,蚕而衣,而不知其所以然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自耕自织,不阙衣食,无与无求,往来何益?
清源子刘骥曰:古之人有连墙二十年而不相谒请者,盖进此矣。
黄茂村曰:昔者容成氏、大庭氏、伯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陆氏、骊畜氏、轩辕氏、赫胥氏、尊卢氏、祝融氏、伏羲氏、神农氏,当是时,民结绳而用之,甘其食,美其服,乐其俗,安其居,邻国相望,鸡犬之音相闻,民至老死不相往来。老子之意,欲与天下之民同于上古乎?
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
信言不美,美言不信。
御注曰:道之出口,淡乎其无味貌。言,华也,故不足信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夫信实之言,淡乎无味,其犹水也,水淡则能久。不美者,以其质而苦也。美好之言,甘而滋溢。其犹醴也,醴甘则易绝。不信者,以其华而虚也。
颍滨苏辙曰:信则为实而已,故不必美。美则为观而已,故未必信。
临川王安石曰:信者,性也。言近于性,则极天下之至顺。故言之信者不美,言之美,则不能近于性矣。
清源子刘骥曰:信言合于道,美言悦于人。
黄茂村曰:天下皆知美之为美,斯恶矣。言足信于人,何用美哉?美则不信。
程大昌曰:信者,诚然也。用其诚然者言之,无所缘饰,故不美也。所谓道之出口,淡乎其无味者也。美言则涉迹而文,如春台太牢者是矣。食于母而谈其真者,不如此也。
善者不辩,辩者不善。
涑水司马光曰:吉人寡辞,盗言孔甘。
颍滨苏辙曰:以善为主,则不求辩;以辩为主,则未必善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其行实善,不假辩说;心行不善,自疑而巧说。
黄茂材曰:道无问无辩,果于善,何用辩哉?辩则不善。
知者不博,博者不知。
御注曰:知道之微者,反要而已。闻见之多,不如其约也。庄子曰:博之不必知,辩之不必慧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知者,谓知其道也。明于理而知根本,得其要而已,何必博乎?所谓少则得也。西升经曰:子得一,万事毕。博者,谓博通于物,务于事而攻异端,不知所极,所谓多则惑也。庄子曰:文灭质,博溺心。
涑水司马光曰:知者不博,一以贯之。博者不知,多歧亡羊。
颍滨苏辙曰:有一以贯之,则无所用。博学而日益者,未必知道也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精粹已知而不须广博。不知要理,徒谓多闻。
叶梦得曰:今老氏之为书,使人得以受而味焉,则近乎美;穷万物之理而无不至,则近乎辩;察万事之变而无不该,则近乎博。然固有信而不美、善而不辩、知而不博者存。
黄茂材曰:通乎一,万事毕。苟知一矣,何用博哉?
圣人无积,既以为人,己愈有;既以与人,己愈多。
御注曰:有积故不足;无藏故有余。庄子曰:圣道运而无所积。
涑水司马光曰:圣人不积,不私无物。既以为人,己愈有,德智无穷。既以与人,己愈多,损之而益。
颍滨苏辙曰:圣人抱一而已,他无所积也。然施其所能以为人,推其所有以与人,人有尽而一无尽,然后知一之为贵也。
王雱曰:圣道运乎无方,而我常无滞,故以至无供万物之求,积而有之,所得鲜矣。为人者,施于事业以治天下也。因其势而利之,则吾道不亏,而事业弥广矣。与人者,授之以道也。授之以道,如天生物,吾未尝费,而物日以伙。既云无积,故又明能淡足万物。盖唯无积,乃所以能足也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体虚善应。
清源子刘骥曰:圣人体道之妙,应物之求,以德分人,未尝费我。既以为人,己愈有;既以与人,己愈多。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,无积故也。
黄茂村曰:道与天下共也,非圣人己私物。圣人运而无积,既以为人,而在己者不加亡,故曰愈有;既以与人,而在己者不加少,故曰愈多。此道所以为善贷万物而不遗者欤!
程大昌曰:此其故何也?圣人者,道之管也。道者居于至无,而万有莫不由之以出,故不待营致藏聚,视之不足于见,听之不足于闻,而用之无时或既。庄子曰:益之而不加益,损之而不加损者,圣人之所保也。渊渊乎其若海,巍巍乎其终则复始也。
天之道,利而不害。圣人之道,为而不争。
御注曰:体天而已,何争之有?
颖滨苏辙曰:势可以利人,则可以害人矣。力足以为之,则足以争之矣。能利能害而未尝害,能为能争而未尝争,此天与圣人所以大过人而为万物宗者也。
叶梦得曰:抑尝观世之论老氏者矣,自汉盖公得其术,教曹参以相齐而齐治,窦太后好之,施于文景而天下大安。兹非其利乎?然以清虚而废实务,其流遂至于亡晋,则不可谓无害。孔子曰: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,窃比于我老彭。古今所传,以老为老氏,信斯言也。孔子所不废,兹非其为乎?然有病其搥提仁义,绝灭礼学,以为有见于上而无见于下,群起而非之,则不可谓无争。此二言者,老氏之所前知也。
黄茂村曰:圣人与天,其道一也。在天谓之利而不害,在圣人谓之为而不争,其实无二。八十一章虽名道德经,始终言道而已。
程大昌曰:此二语皆主柔而言也。凡其一书,皆主柔以达所欲,而其道原盖出于天也,是以篇终对而言之。
颍滨苏辙曰:凡此皆老子之所以为书,与其所以为道之大略也,故于终篇复言之。
道德真经集注卷之十八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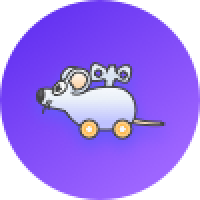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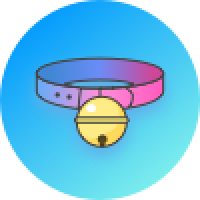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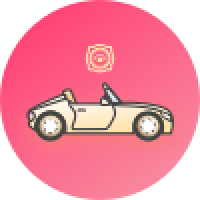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