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鹤林真逸彭耜纂集
宠辱章第十三
宠辱若惊,贵大患若身。
御注曰:宠者在下,贵者在上。居宠而以为荣,则辱矣;处贵而以为累,则患莫大焉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宠者,谓富贵庆赏诸吉也。辱谓贫贱刑罚诸凶也。夫达道之士,以形骸为逆旅,生死如赘痈,不荣通,不丑穷,知轩冕之去来,乃外物之寄托,岂有宠辱系怀而可惊怛哉?此谓中人耳。中智之士,则处安而虑危,得宠而知辱,故皆如惊者,戒慎之深也。夫心之感动,异于震惊,故谓之若惊。世俗趋末则惊辱,中智观本故惊宠。贵者,尊爱之称。大患者,轩冕宝货、外物养身之属也。且至人知身非我有,而尚外之,况尊爱他物乎?今世之人,谓轩冕宝货可以资生,故贵之如身,而不知身之与物皆是大患之本,不足贵也。
陆佃曰:宠所以为辱,贵所以为患,何也?曰:宠之与贵,皆外物者也。外物非吾所有而有之,此所以为大患大辱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以宠辱为重,甚于性命。
叶梦得曰:宠辱者,视宠犹辱也。贵大患者,以贵为大患也。惊者,猝然遇之而骇者也。身者,忧患之所从生而不欲有者也。常物之情,得其所欲则顺而安,非其所欲则逆而骇。故世不惊于宠而惊于辱。宠之过必辱,辱之复必宠。视宠犹辱而若惊者,知宠之必有辱也。贵者,人之所尊也。贵贱无常分,有贵而贱者争;生灭无定形,有身而偶者敌。视贵为患而若身者,知贵之必有贱也。
黄茂材曰:宠,人所荣也,在道则为可辱。贵,人所欲也,在道则为可患。自古以来,因宠贵之极陷于祸败者,何可胜数。譬之牺牛,衣以文绣,食以𫇴菽,及其牵而入于太庙,求为孤犊而不可得,则夫所谓宠贵者,岂不可辱可患乎?
何谓宠辱?宠为下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开元御本作宠为下,言人得富贵庆赏者,恃宠而骄盈则生祸,因宠获祸则宠为辱本,故曰为下。河上公本作宠为上,辱为下,于义完全而理无迂阔。皇甫谧本亦作宠为上,辱为下,言以得为上,失为下也。
颍滨苏辙曰:所谓宠辱,非两物也。辱生于宠而世不悟,以宠为上而辱为下者是也。若知辱生于宠,则宠顾为下矣。
陆佃曰:可得而宠者下也。
刘泾曰:宠人者为上,则宠于人者为下矣。孟子曰:赵孟之所贵,赵孟能贱之矣。
得之若惊,失之若惊,是谓宠辱若惊。
御注曰:轩冕在身,非性命之理,物之傥来,寄也。寄之,其来不可拒,故至人不以得为悦;其去不可圉,故至人不以失为忧。今寄去则不乐受而喜之,是以得失累乎其心,能勿惊乎?
碧虚子陈景元曰:世俗据其富贵,操之则栗,舍之则悲,未达得失之非我,故皆惊慑也。中智之士知祸福循环,得其宠荣必有悴辱,故戒之持胜如失之惊也。
临川王安石曰:得失若惊,此宠之所以为辱也。
黄茂材曰:宠于人则服役于人,其得也在人而不在我,故得亦惊。其失也在人而不在我,故失亦惊。夫在我者,大泽焚而不能热,河汉沍而不能寒,疾雷破山、风振海而不能惊,又何有于得失哉?
何谓贵?大患若身?
御注曰:据利势,擅赏罚,作福威,天下畏之如神明,尊之如上帝,可谓贵矣。圣人则不以贵自累,故能长守贵而无患。譬如人身,堕肢体,黜聪明,离形去智,通于大同,则无入而不自得也。世之人以物易性,故累物而不能忘势;以形累心,故丧心而不能忘形,其患大矣。
刘泾曰:前章言五色声味、驰骋田猎难得之货交攻其内外,所谓大患也。而患本于有身,无是身则无是患矣。而身者委形于造物,则安能必无哉?今享天下之贵,则事天下之事,将膻行以悦人,蒿目以忧世,其患可胜言哉!庄子曰:夫贵者,夜以继日,思虑善否,其为形也亦疏矣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世俗不知宠为致辱之大患,而返贵重致辱之患如身。
吾所以有大患者,为吾有身。及吾无身,吾有何患?
御注曰:人之生也,百骸、九窍、六脏,赅而存焉,吾谁能为亲?认而有之,皆惑也。体道者解乎此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夫人所以有大患者,谓其有身也。且人之身,无羽毛以御寒暑,必将资物以为养。而贪生太厚者,动入死地。若能外其身,不以身为身;忘其心,不以心为心。冥乎造化,同乎万物,使行若曳枯木,坐若聚死灰,则向之宠辱大患,何缘及之?又曰:无者,忘也,外也。或以无身为灭坏空寂者,失老氏之宗旨矣。
颍滨苏辙曰:性之于人,生不能加,死不能损,其大可以充塞天地,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,凡物莫能患也。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,而惟身之贵,爱身之情笃,而物始能患之矣。生死疾病之变攻之于内,宠辱得失之交撄之于外,未有一物而非患也。夫惟达人知性之无坏而身之非实,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尽去,然后可以涉世而无累矣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我因何能致大患?为有此身为致患之本,又何况身外更有不能舍弃重于身者乎?
清源子刘骥曰:人之有身,饥渴、寒暑、生老病死,莫非患也。故吾所以有大患者,为吾有身。及吾无身,吾有何患?所谓无身者,外生死,遗祸福,忘乎物,忘乎天,其名为忘己。忘己之人,是谓入于天。若然者,体合大道,心同太虚,死生无变于己,而况利害之端乎?
故贵以身为天下,若可寄天下;爱以身为天下,若可托天下。
御注曰:天下,大器也,非道莫运。圣人体道,天下乐推而不厌。其次则知贵其身而不自贱以役于物者,若可寄而已。知爱其身而不自贱以困于物者,若可托而已。
涑水司马光曰:夫贵重天下者,天下亦贵重之。爱利天下者,天下亦爱利之。未有轻贱残贼天下而天下贵爱之者也。故圣人之贵爱天下,所以贵爱其身也。如此则付以大器,必能守之。
颍滨苏辙曰:人之所以骛于权利,溺于富贵,犯难而不悔者,凡将以厚其身耳。今也禄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,则其忘身也至矣。如此而以天下予之,虽天下之大,不能患之矣。
陈象古曰:恃贵有己而为天下,非寄天下之要也。恃爱有己而为天下,非托天下之要也。故曰若可寄,若可托,言若则不可寄、不可托之义也。
叶梦得曰:不贵其贵而贵其身,虽得天下而不敢执,视之犹逆旅,兹非可以寄天下者乎?不爱其宠而爱其身,虽有天下而不敢任,处之犹蘧庐,兹非所以托天下者乎?
黄茂材曰:人不知贵其身者,以天下为重,而以身为轻尔,故不知贵其身。人不知爱其身者,以天下为大,而以身为小尔,故不知爱其身。老子之道,以身为天下,可贵可爱者皆在身。彼天下特其外物,故可寄托焉。
林东曰:达人遗宠而辱不及,忘身而患不至。有身者以其不能忘身也。忘身则无身而亦无患。若舜有天下而不与尧之非心黄屋,则几矣。贵与爱、寄与托,则一意,辞势互换然耳。
视之不见章第十四
视之不见名曰夷,听之不闻名曰希,抟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诘,故混而为一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无形之形,天地以生,谓之夷。无声之声,五音以始,谓之希。无绪之绪,万端以起,谓之微。此皆先贤举其进道之方也。若夫能忘其视听,冥其循搏,混一都无,则至矣尽矣,不可以加矣。
颍滨苏辙曰:此三者,虽有智者莫能诘也,要必混而归于一而后可尔。所谓一者,性也;三者,性之用也。人始有性而已,及其与物构,然后分裂四出,为视、为听、为触,日用而不知反其本,非复混而为一则日远矣。若推而广之,则佛氏所谓六入皆然矣。
首楞严有云反流全一,六用不行,此之谓也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大象平夷,无色可见;大音希声,默不可听;冲妙无形,虚不可执。三者谓希、夷、微也,皆无质象,不可以器位分之,故复混为一,非视听、把执、击搏之能知,似隐似见,或存或亡,不可究诘,亦若万籁一风而异声,七窍同气而殊用,思不可推,言不可议者也。
清源子刘骥曰:夷则无色,故视之不见;希则无声,故听之不闻;微则无形,故搏之不得。此三者不可致诘,随事强名。夫道一而已,故混而为一。
黄茂材曰:此章论真有也。真有虽有,视之不见,听之不闻,搏之不得,则近于无。老子虑夫人之溺于无而不知其有,于是为之别白而言曰,是道也,分之则为三,夷、希、微是也。合之则为一,混然者是也。是皆真有非无,人不能知之。乃谓老庄为虚无之学,岂足与语道哉!
其上不皎,其下不昧。
御注曰:形而上者,阴阳不测,幽而难知,兹谓至神,故不皎,皎言明也。形而下者,一阴一阳,辨而有数,兹谓至道,故不昩,昩言幽也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夫形色之物皆有涯分,惟道超然出于九天之表,处阳而不明,存乎太极之先,而不为高矣。使其学者居上,与日月齐照,而其光不皎,故曰其上不皎。沈然没于九地之外,处阴而不暗,流乎六极之下,而不为深矣。使其学者在下,与瓦甓同寂,而其明不昧,故曰其下不昧。
涑水司马光曰:皎,明也。道之升,万物以生而不可见;道之降,万物以息而未尝亡。
颍滨苏辙曰:物之有形者,丽于阴阳,故上皎下昧,不可逃也。道虽在上而不皎,在下而不昧,不可以形数推也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忽焉在上,明而不曜;倏然在下,幽而不晦。
陈象古曰:皎,明白之称也。昧,隐暗之称也。不皎,谓道行于己,不自明其功也。不昧,谓道施于物,不可隐蔽于其理也。
黄茂材曰:此又论无之非无也。其在上也,人见其皎而非皎;其在下也,人见其昩而非昩。
绳绳兮不可名,复归于无物。
御注曰:道之体若昼夜之有经,而莫测其幽明之故,岂貌像声色可得而形容乎?故复归于无物。
颍滨苏辙曰:绳绳,运而不绝也。人见其运而不绝,则以为有物矣,不知其卒归于无也。
清源子刘骥曰:绳绳兮绵绵不绝,运用无穷,不可得而形容,复归于无物。
是谓无状之状,无物之象,是谓恍惚。
御注曰:无状之状,无物之象。恍兮惚,其中有物;惚兮恍,其中有象。犹如太虚,含蓄万象,而不睹其端倪;犹如一性,灵智自若,而莫究其运用。谓之有而非有,谓之无而非无。若日月之去人远矣,以鉴燧求焉,而水火自至。水火果何在哉?无状之状,无物之象,亦犹是也。
颖滨苏辙曰:状,其著也;象,其微也。无状之状,无物之象,皆非无也。有无不可名,故谓恍惚。
迎之不见其首,随之不见其后。
御注曰:其始无首,其卒无尾,故迎之、随之,有不得而见焉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周流无端,故无首尾。
陈象古曰:不可致诘,故如是。
清源子刘骥曰:莫知其始,故迎之不见其首;莫知其终,故随之不见其后。
黄茂材曰:此又论无有之非无有也。既谓惚恍矣,乌有其首之可迎,乌有其后之可随?虽无其首与后也,谓无其中可乎?经曰:惚兮恍,其中有象。恍兮惚,其中有物。其中何也?物与象是也。由此以言,无有之非无有可见矣。
执古之道,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,是谓道纪。
御注曰:一阴一阳之谓道。师天而无地者,或蔽于道之动而凭其强阳。师阴而无阳者,或溺于道之静而止于枯槁。为我者废仁,为人者废义,岂古之道哉?不可致诘而非有,是谓恍惚而非无。执之以驭世,则变通以尽利,鼓舞以尽神,而无不可者。此所谓自古以固存者欤?
碧虚子陈景元曰:古道者,无形无名,天地之原,万物之宗也。即视之不见、听之不闻之道也。老氏使其治身治世者,持执上古无为自然之道,制驭即今有为烦扰之俗,归乎淳风,复乎太始,使各正性命,不迁其德,是谓知道之纲纪也。
陆佃曰:能知古始,古者今之所出,始者,终之初。庄子所谓无端之纪是也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緜古不移,道也。见机而作,事也。治身者,执古之道。谓人之灵物,与造化齐生,不泯不灭。今之有者,身也,受之于阴阳,得之于父母,贷一气以有生,本五行以成质,执守神用,摄御身形,是谓执古之道不失,御今之有不亏。古谓先天之道,始谓万物之宗。能知道者,是谓执物之纪而总之。
清源子刘骥曰:圣人体道之真以治身,绪余土苴以治天下国家,所以御今之有也。能知古始,则知道之大原,故是谓道纪。
黄茂材曰: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,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,先天地生而不为久,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时有古今,道无古今,故可执而御。谓道为非有,可乎哉?太易、太初、太始、太素、太极,此五太者,时之所谓古,而道之所谓始。人能知之,可以为道之纪。
古之善为士章第十五
古之善为士者,微妙玄通,深不可识。
御注曰:列御寇居郑圃四十年,人无识者。老子谓孔子曰:良贾深藏若虚,君子盛德,容貌若愚。其谓是欤?
颍滨苏辙曰:粗尽而微,微极而妙,妙极而玄,玄则无所不通,而深不可识矣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虽在世间,人不以为异。
黄茂材曰:啮缺、王倪、蒲衣子、南郭子綦、支离疏、王骀与夫子祀、子舆、子桑户之徒,皆古微妙玄通之士,人不能识,故谓庄子寓言焉。当商周之季,士之被褐怀玉、隐居田肆,不肯出而婴于世网者,何时无之?但无所纪见。如论语载楚狂接舆、荷筿丈人、长沮、桀溺,今皆谓无是人,可乎?呜呼!人固难知,有道之士尤其难知,此经所以谓其不可识。
夫惟不可识,故强为之容。
御注曰:天之高不可俄而度,地之厚不可俄而测。曰圆以覆,曰方以载者,拟诸其容而已。强为之容,岂能真索其至?
碧虚子陈景元曰:恐后世无以为师法,故强为说其容状,指陈表仪,谓下文也。
陈象古曰:显教示信,若不强为之容,恐来者不可学也。
黄茂材曰:夫有道之士,虽为难识,天与之形,道与之貌,亦可见髣髴。
豫兮若冬涉川,犹兮若畏四邻,俨若容,涣若冰将释。敦兮其若朴,旷兮其若谷,浑兮其若浊。
御注曰:豫者,图患于未然。犹者,致疑于已事。若冬涉川,守而不失已。若畏四邻,易所谓以此斋戒者是也。敦者,厚之至,性本至厚,如木之朴,未散为器。旷者,广之极,心原无际,如谷之虚,受而能应。不刿雕以为廉,不矫激以为异,浑然而已,故若浊。与修身以明污者异矣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豫,犹豫也。言有道之士,顺从自然,而举事退藏,辄加重慎。虽履坦途,常忧没溺,如寒沍之月,揭涉长川,其心豫然,恐下沉于不测之渊也。又履虚无而不敢有为,故出处而深思,犹然而畏惧,谨于去就,而虑幽明之司察,如世人避禁而畏四邻之窃知,此戒之深也。俨然端谨而心无散乱,如宾对主人,曷敢造次?其无事无为也。夫东郭顺子正容悟物,使人意消,故田子方师仰之。李含光居于暗室,如对君父,故司马子微激赏之。此可谓能俨若客也。外虽矜庄而内心闲放,若春冰之释,涣然泮散,凝滞都亡。敦者,淳厚貌。朴者,质素貌。又形未分曰朴。有道之士,天资淳厚,而质素之材未尝分散,其语默恬和而无文饰也。旷者,宽大之称。谷者,含虚之窍。有道之士,德纯厚而不显,器宽大而含容,任善恶之去来而不挠于怀,有如空谷之应答而尝虚也。杂波流曰浑,不分明曰浊。有道之士,内心清静而外杂波流,若浊水之不明,曷分别乎妍丑也。已上七事,治国则民不识不知,复乎太古;修身则和光同尘,冥乎至道。
颍滨苏辙曰:戒而后动曰豫,其所欲为,犹迫而后应,豫然若冬涉川,逡巡如不得已也。疑而不行曰犹,其所不欲,迟而难之,犹然如畏四邻之见之也。无所不敬,未尝惰也。知万物之出于妄,未尝有所留也。人伪己尽,复其性也。虚而无所不受也。和其光,同其尘,不与物异也。
临川王安石曰:虽然,亦不可不反诸本也。故敦兮其若朴,而守之以素也。故旷兮其若谷。谷者,虚而能应者也。然而其道亦不可得而别也,故混兮其若浊而已矣。此所谓善为士者也。夫豫也,犹也,以至于混而其若浊也,皆所为不可识而强为之容也。
陆佃曰:以其先事而虑,常迫而后动,故曰豫若冬涉川。以后事而虑,常以防而后居也,故曰犹若畏四邻。以其虽以迫而后动,防而后居,而其心常俨之若容。涣若冰将释者,散而不凝于物也。敦兮其若朴者,其体无乎不圆也。旷兮其若谷者,其体无乎不虚也。敦兮其若朴,旷兮其若谷,然后冥之以无知,混之以无觉,故曰浑兮其若浊。
刘概曰:犹豫皆疑而不敢进之辞也。以其不为物先,故豫若冬涉川,犹若畏四邻。以其不为事主也,故俨若容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建德若偷,为善不伐。豫若履冰,慎之至也。犹若畏邻,密之至也。
叶梦得曰:豫者,先事而戒也。古者谓大象为豫,物大则见之者早,而冬涉川亦理之所易见而戒者也,故先事如之。犹者,后事而犹疑也。犹亦兽名,畏人而善登木。畏人登木可矣,无人登木者,疑也。四邻吾所亲狎,可以无畏而犹畏,故后事如之。俨若容,庄也。涣若冰将释,舒也。冰者,时而后散,不遽毁其坚者也。将以临民,不可以不庄,故容张之也。孔子享礼有容色,退而燕居,不可以不舒,故涣。孔子居不容,燕居申申如也,夭夭如也,弛之也。敦兮其若朴,足于己者实也。旷兮其若谷,受于物者虚也。虽然,是皆其表,吾终日暴而不知敛,则物得以窥之矣。故终之以浑兮其若浊,洁而与众异易,浊而与众异难。
清源子刘骥曰:豫者,图患于未然,若冬涉川,不得已于事也。犹者,致疑于已事,若畏四邻,退藏于密也。俨若容者,望之俨然,寂然不动也。涣,散也,散其留滞,混然融和,如列子之心凝形释,骨肉都融是也,故若冰将释。敦兮其若朴者,敦厚无华,若混沌之始朴。旷兮其若谷,旷荡无边,若天谷之至虚。浑兮其若浊者,和光同尘,浑杂如浊,与修身以明污者异矣。此七者皆古之善为士者所为,可谓良贾深藏若虚,盛德容貌若愚,所以深不可识也。此子列子居郑圃,四十年无人识者,国君卿大夫视之犹众庶也。
晦庵朱熹曰:俨若客,语意最精,今本多误作容,殊失本指。又曰:旧读俨若容止作容字,尝疑此或非老子意,后见一书引此,乃以容字为客字,于是释然,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协韵,以客韵释,脗若符契。又此凡言若某者,皆有事物之实,所谓客者,亦曰不敢为主而无与于事,故其容俨然耳。
黄茂材曰:豫兮若冬涉川,践履必加敬也;犹兮若畏四邻,常若有临于其左右前后也;俨若容,居处不敢慢也;涣若冰将释,形气无留滞也;敦兮其若朴,初不见其圭角也;旷兮其若谷,其中足以容也;浑兮其若浊,处俗而不违于俗也。皆其道德之容,睟然见于其外,使人爱慕之不厌。若乃晋人之风,蓬头跣足,不拘绳检,终日酣饮,疾呼大叫,自以为旷达,岂足言此哉!
孰能浊以静之徐清。孰能安以动之徐生。
御注曰:易曰:来徐徐。徐者,安行而自适之意。至人之用心,非以静止为善,而有意于静,非以生出为功,而有为于生也。因其固然,付之自尔,而无怵迫之情、遑遽之劳焉。故曰徐静之徐清。万物无足以挠其心,故孰能浊?动之徐生,万物无足以系其虑,故孰能安?安有止之意,为物所系则止矣,岂能应物而不伤?
碧虚子陈景元曰:言世俗之人,谁能如有道之士,心同渊泉,即其浊以澄而静之,则徐徐复其清矣。谁能如有道之士,支离其德,当其安以久而动之,则徐徐全其生矣。
颍滨苏辙曰:世俗之士以物汨性,则浊而不复清。枯槁之士以定灭性,则安而不复生。今知浊之乱性也,则静之,静之而徐自清矣。知灭性之非道也,则动之,动之而徐自生矣。易曰:寂然不动,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今所谓动者,亦若是耳。
黄茂材曰:大道泛兮,初无定名。若以为浊,静之则清;若以为安,动之则生。所以能与物为无穷。
保此道者不欲盈。夫惟不盈,故能敝不新成。
御注曰:有积也,故不足;无藏也,故有余。至人无积,亦虚而已。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者,亦已小矣,故不欲盈。经曰:大白若辱,盛德若不足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言人保守此徐清徐生之道者,善能谦以自牧,而安其虚静。夫惟不盈者,再举独有至人不矜恃盈满,故能常守弊陋薄恶,虽有新成之功,亦能持胜不动,更求进向,复增上善,不住小成,斯乃圣人之深趣也。
王雱曰:得道者未尝盈,则成道者未尝新也。道之为用,万世而不敝,以其无敝无新、不成不败故也。敝生于新,败生于成。士虽成道,而常若敝败,则终无敝败矣。苟得道之初,矜其新成,则与道异意,非大成也。经曰:大成若缺,其用不敝。此篇句句有序,以至于成,成而若敝,则尽之矣。
陈象古曰:盈,满假之谓也。志自满假,道随而污,故不可盈。古人行道,其弊不生。今人若能如古,岂有新成之弊哉?恐其奉道之不至也。故无弊者,其要在于不自盈而已。
黄茂材曰:盈对虚而为言。蔽,匿也,藏也。老子曰:良贾深藏若虚,其不欲盈可知。夫物新必有故,成必有坏。无新也,孰故乎?无成也,敦败乎?夫如是,可保此道。
致虚极章第十六
致虚极,守静笃。
御注曰:莫贵乎虚,莫善乎静。虚静者,万物之本也。虚,故足以受群实,静,故足以应群动。极者,众会而有所至。笃者,力行而有所至。致虚而要其极,守静而至于笃。则万态虽杂,而吾心常彻;万变虽殊,而吾心常寂。此之谓天乐,非体道者不足以与此。
颍滨苏辙曰:致虚不极,则有未亡也。守静不笃,则动未亡也。丘山虽去,而彻尘未尽,未为极与笃也。盖致虚存虚犹未离有,守静存静犹陷于动,而况其他乎?不极不笃而责虚静之用,难矣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以虚为虚,未极于虚也。以静为静,未极于静也。虚静兼忘,是为笃极。
叶梦得曰:知虚之为虚而致之,未必能致于虚,犹有实以为之对也。知静之为静而守之,未必能守于静,犹有动以为之别也。故致虚必极,守静必笃。致虚极则无虚,是为真虚。守静笃则无静,是为真静。
黄茂材曰:虚静之境,要在纯熟。致虚不极,则不可得而虚。守静不笃,则不可得而静。万物并作,吾以观其复。
御注曰:方其并作而趣于动出之涂,吾观其动者之必静,出者之必复,而因以见天地之心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非止于人,而万物之并作,未有不始于寂然而发于无形。及观其复也,尽返于杳冥而归于无朕,以全其真也。易曰:复其见天地之心乎!天地之心,谓寂然至无也。
颍滨苏辙曰:极虚笃静,以观万物之变,然后不为变之所乱,知凡作之未有不复者也。苟吾方且与万物皆作,则不足以知之矣。
临川王安石曰:复,本也。万物并作,吾能观其复,非致虚极守静笃者,不能与于此。
陈象古曰:物极则复,复者自静,故可以观。又曰:万物虽多,安能离吾之道哉?
黄茂材曰:人与万物同生一根,惟虚而静,则能观其复。复初也,物之根也。名为观物,实以自观。
程大昌曰:物之从枯而茁壮长者,是其作也。华实皆泯,津归于根,则其复也。老氏借浅以明赜也。虚者物莫之能昏,静者物莫之能诱,故其接物易以有见也。对奕之智,常不及旁观之明,而操舟失港,凡岸立之人,往往皆能指其曲折,故由动观动,或反与之俱,而据要观妙者,必其心不徇物,乃始能之也。
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。
御注曰:芸芸者,动出之象。万物出乎震,相见乎离,则芸芸并作,英华发外;说乎兑,劳乎坎,则去华就实,归其性宅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芸芸,茂盛貌。或作云云,动作貌。
颍滨苏辙曰:万物皆作于性,皆复于性,譬如华叶之生于根而归于根,涛澜之生于水而归于水耳。
陆佃曰:芸芸者,所谓幻化也。各归其根者,所谓空性也。幻化有灭而空性无坏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万物纷纭动作既极,必返于本,不假至人用意裁制。
清源子刘骥曰:圣人使人息其爱欲之念,归乎虚静之本,复其性命之源,譬如万物生于根而归于根也。
归根曰静,静曰复命。
颍滨苏辙曰:苟未能自复于性,虽止动息念以求静,非静也。故惟归根,然后为静。命者,性之妙也。性犹可言,至于命则不可言矣。易曰:穷理尽性,以至于命。
临川王安石曰:命者,自无始以来,未尝生未尝死者也。故物之归根曰静,静则复于命矣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复于元命,返于天真。
陈象古曰:本自清静,因物有迁也。
黄茂材曰:夫物芸芸,各归其根,穷理也。归根曰静,尽性也。静曰复命,至于命也。
复命曰常。
御注曰:复命则万变不能迁,无间无歇,与道为一,以挈天地,以袭气母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能悟之者,则行住坐卧不离乎是。
颍滨苏辙曰:方其作也,虽天地山河之大,未有不变坏不常者。惟复于性而后湛然常存矣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夫物或兴或衰,或生或灭,皆为造化之所陶铸。惟道常然。昼不能明,夜不能晦。复性命之道,则知真常。
黄茂材曰:穷理尽性以至于命,则可常存矣。知常明。
御注曰:明道之常,不为物迁,故足以鉴天地,照万物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知犹悟也。曰明或作日明,言日益明达。
颍滨苏辙曰:不以复性为明,则皆世俗之智,虽自谓明而非明也。
不知常,妄作,凶。
御注曰:随物转徙,触涂自患,故凶。易曰:复则不妄。迷而不知复,兹妄也已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不悟常道者,反以神变为妖、长生为诞,虚极静笃为空旷,归根复命为灭亡。不知强知,不识强识。易所谓不常其德,或承之羞。故曰:不知常,妄作,凶。
颍滨苏辙曰:不知复性,则缘物而动,无作而非凶。虽得于一时,而失之远矣。
黄茂材曰:常之为道,至微至妙,非夫明智玄通之士则不能达。秦汉以来,方士争言神仙之术,陷于祸败,如徐福、栾大之徒,皆妄作者也。老子:知其凶之必至。
知常,容。
御注曰:知常则不藏是非美恶,故无所不容。
颍滨苏辙曰:方迷于妄,则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敌,吾何以容之?苟知其皆妄,则虽仇雠犹将哀而怜之,夫何所不容哉?
陈象古曰:安于天理,不复争竞,何有而不能容乎?
清源子刘骥曰:知常则与天地合其德,如天地之无不覆载也。
黄茂材曰:真常之道,大无不包。知之者必有容宇宙之量。
容乃公。
御注曰:无容心焉,则不独亲其亲、子其子,何私之有?
颍滨苏辙曰:无所不容,则彼我之情尽,而尚谁私乎?
清源子刘骥曰:有容德乃大,如天地之无私覆载也,故曰公。
黄茂材曰:容有容宇宙之量,则无己、无人、无物皆冥于一。
公乃王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既能包容,乃于己无私,则襟怀荡然平夷而至公矣。既公平无私,则德用周普,天下辐辏,无有不归往者矣。
王。
颍滨苏辙曰:无所不公,则天下将往而归之矣。
黄茂材曰:以此处上,帝王天子之德也;以此处下,玄圣素王之道也。
王乃天。
御注曰:在上而无所不覆者,天也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人既归往,天将祐之。
颍滨苏辙曰:无所不怀,虽天何以加之。
临川王安石曰:王者,人道之极也。人道极则至于天道矣。
黄茂材曰:王者与天为徒也。
程大昌曰:王之能容也,无择而无弃,即天之不颇其覆者是也。
天乃道。
御注曰:天、地、人莫不由之者,道也。尽人则同乎天,体天则同乎道。
颍滨苏辙曰:天犹有形,至于道则极矣。
临川王安石曰:天与道合而为一。
黄茂材曰:天,法道者也。
道乃久,没身不殆。
御注曰:道者,万世无弊,庶物得之者昌,关百圣而不穷,蔽天地而不息。
刘泾曰:所谓自古固存。
黄茂材曰:道者,自本自根,未有天地,自古以固存,故曰道乃久,得道则可久矣。而曰没身不殆,身又可没乎?曰:身者,有形之物,安得不没?身没而谓之久,何也?其死而不亡者乎?其形化而心不与之然者乎?
林东曰:天犹有形,至于道则悠久无穷,虽没吾之身而未尝危殆。有以见体道之君子,与道周旋,虽久而安也,其源出于致虚之极、守静之笃也。
道德真经集注卷之四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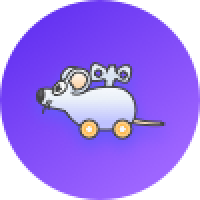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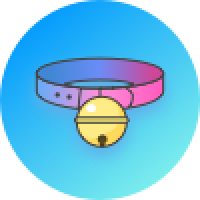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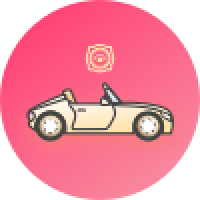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