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鹤林彭耜纂集
曲则全章第二十二
曲则全,枉则直,洼则盈,弊则新,少则得,多则惑。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圣贤之士,钩深致远,廓然见独,而蟠曲才能未尝显耀者,故欲远害而全身也,故曰曲则全。聪达明察,晓辨诸物,有大功业,立大名声,心直如猛矢,志端如朱弦,常枉己屈伏而不自伸者,此则大直之士也,故曰枉则直。人以谦卑为本。易曰地道变盈而流谦,盖设象而会意也。夫陵原川谷之变,高下之不常也。川谷洼下,则水流而满之;陵原高峻,则雨剥而颓之。人之谦下,则众仰德而归之,以致其光大也。夫自尊则众毁而辱及之,以致其危亡也。故曰洼则盈。且人有贤才,而能支离其德,弊薄其身,则众共乐推,而其道日新矣,故曰弊则新。夫少者,简易之谓也。易曰:易则易知,简则易从。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。西升经曰:子得一,万事毕。又曰:丹书万卷,不如守一。故曰少得则。夫多者,博学之谓也。庄子曰:文灭质,博溺心。列子曰:路多岐则亡羊;学多方,则丧道。庚桑子曰:万人操弓共射一雕,雕无不中。万物章章,以害一生,生无不伤。经曰:多言数穷,不如守中。此并戒其多也,故曰多则惑。道生一,一者,道之子,谓太极也。太极即混元也,亦太和纯一之气也,又无为也。夫圣人抱守混元纯一之道者,谓复太古无为之风也。经曰:天得一以清,地得一以宁。庄子曰:天无为以之清,地无为以之宁。以此可明矣。自曲则全下六事,尚有对治之迹。此云抱一无为,可以兼包之,故为天下式。
颍滨苏辙曰:圣人动必循理,理之所在,或直或曲,要于通而已。通故与物不迕,故全也。直而非理,则非直也。循理虽枉,而天下之至直也。众之所归者下也,虽欲不盈,不可得矣。昭昭察察,非道也。闷闷若将弊矣,而日新之所自出也。道一而已,得一则无不得矣。多学而无以一之,则惑矣。抱一者,复性者也。盖曲则全,枉则直,洼则盈,弊则新,少则得,多则惑,皆抱一之余也,故以抱一终之。
临川王安石曰:方则易挫,曲以应之,此所以能全也。直则易折,故枉以待之,此所以能直也。海者常处于卑,而为百川之所委,故洼则盈。无春夏之荣华,秋冬之雕落,故弊则新。少者复本则得矣,多者有为则惑矣。
王雱曰:至人冲虚,其行如水,无心于物,不与物忤,故常全也。此篇大旨与庄子养生主相类。
陆佃曰:盖其周旋动止,于物无忤,与之俱往,故谓之曲。物之变也,而天理之在我,终于完而无缺,故谓之全。
达真子曰:己虽全也,常自以为曲,所以求全不已,则卒至于全矣;是则所谓曲则全也。己虽直也,常自以为枉,所以求直不已,则卒至于直矣;是则所谓枉则直也。犹德虽盈也,常自以为不足,则若其洼;知虽新也,常自以为不明,则若其弊。以若洼之心不已其求,则卒至于盈;是则所谓洼则盈也。以若弊之心不已其求,则卒至于新矣;是则所谓弊则新也。少则约,多则详,以道散则适于多,道聚则归于少。是以少则得,得其道也;多则惑,惑其道也。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抱一则不离于道,为天下式。
陈象古曰:一者不繁不乱,可以曲,可以全,可以枉,可以直,可以洼,可以盈,可以弊,可以新,可以少,可以得,可以多,可以惑。夫小者大之端,暗者明之渐,理当然也。故圣人抱一,于数则有增,于象则有容,不自满假,先见未萌,天下若取以为式,则人人合于道矣。
叶梦得曰:曲则全,洼则盈,少则得,理也,即其体而言之也。枉则直,弊则新,多则惑,势也,极其变而言之也。曲则不忤,故全;洼则不满,故盈;少则不夸,故得,此理之必至者也。枉非以求直,而枉之极必直;弊非以求新,而弊之反必新;多非以求惑,而多之罪必惑。此势之不得不然者也。理势之相成,或更为终始,或迭为得失,纷然其不可穷,而圣人独能济之,不与之俱变者,抱一也。前言魂魄之合,而曰抱一者,一之存乎己者也。今言理势之杂,而曰抱一者,一之总乎物者也。一则万法之所从出,故以为天下式。
黄茂材曰:世皆曲,吾与之为曲,故能保其全;人皆枉,吾与之为枉,故能养其直。莫不欲盈也,孰自处于洼?吾能洼,乃所以为盈。莫不欲新也,孰自期于弊,吾能弊,乃所以为新。为道日损,损则少,其入道也近,故得。为学日益,益则多,其去道也远,故惑。曰全、曰直、曰盈,曰新,曰得,曰惑,散之则六,敛之则一。通乎一,万事毕,又何有于六乎?故曰:圣人抱一,为天下式。
不自见,故明;不自是,故彰;不自伐,故有功;不自矜,故长。夫惟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
御注曰:不蔽于一己之见,则无所不烛,故明。不私于一己之是,而惟是之从,则功大名显而天下服,故彰。人皆取先,己独处后,曰受天下之垢,若是者常处于不争之地,孰能与之争乎?
碧虚子陈景元曰:此四事皆无为之职。夫圣人无为,何尝显见己之才能,则天下自然称其明矣。故曰不自见,故明。河上公曰:圣人虽明,不以自见千里之外,乃因天下之目以视之,故能明达。夫能用天下之目者,亦不自显见之意也。音训虽异,而其旨略同矣。且圣人虚静,何尝自是而非人?盖彼我都忘,则天下自然称其是而其德彰矣。故曰:不自是,故彰。且圣人恬澹,何尝自伐?取其德美,则天下自然称其功业矣,故曰:不自伐,故有功。且圣人寂寞,何尝自矜大其贤贵,则天下自然称其有道而长存矣,故曰不自矜,故长。
颍滨苏辙曰:不自见、不自是、不自伐、不自矜,皆不争之余也,故以不争终之。
临川王安石曰:不自见,乃无所不见,故常明。不自是,乃无所不是,故常彰。不自伐,则善不丧,故有功。不自矜,则不有能,故能可久矣。夫惟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者。书曰:汝惟不矜,天下莫与汝争能。
达真子曰:如自见其全,则以为全足于己,更不求其全,由是故全或至于不能明。如自是其直,则以为直足于身,更不求其直,由是故直或至于不能彰。唯不自见其全也,常以为求全之不足,若是则全终至于明也;唯不自是其直也,常以为求直之不足,若是则直终至于彰也。推此二类,凡有于己者,皆不自足于己。如虽有功也,不自伐其功,故得其有功;己虽长也,不自矜其长,故能得其长。盖圣人不自满假,凡在于此也。
叶梦得曰:见字当读为见,乃谓之象之见。夫惟得一,故虽晦其迹,不自见而反明;虽藏其用,不自是而反彰。不伐而有功,不矜而能长。亦由前之为曲全洼盈者,天下之理同也。是以复终之以夫唯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以为万物之变,非吾所能执,及其既定,物亦莫能与我竞,此不争之效也。虽万物无不可为争,心苟存,则虽一法无所容措。
黄茂材曰:至人之处于世,未尝有我也。无我故不自见,不自是,不自伐矜。夫然,故与物无争,而物亦莫与之争。方舟而济于河,有虚船来触舟,虽有褊心之人不怒,天下孰能与之争乎?不自见而明,不自是而彰,不自伐矜,有功而长,亦其自然之理,夫何容心!
古之所谓曲则全者,岂虚言哉!诚全而归之。
御注曰:圣人其动若水,以交物而不亏其全;其应若绳,以顺理而不失其直。知洼之为盈无亢满之累,知弊之为新,无夸耀之迹。若性之自为而不知为之者,致曲而已。故全而归之,可以保身,可以尽年,而不知其尽也。是谓全德之人,岂虚言哉!
碧虚子陈景元曰:夫圣人独抱守纯一无为,何尝更有争竞之心哉?经曰:含德之厚,比于赤子。毒虫不螫,猛兽不据,攫鸟不搏。虫兽尚尔,况于人乎?然而上古有此曲全之语,岂今日之寓言哉?人能行之,诚有全德之美,而归之于身,此再三劝励之深旨也。
颍滨苏辙曰:世以直为是,以曲为非,将循理而行于世,则有不免于曲者矣。故终篇复言之曰:此岂虚言哉!诚全而归之。夫所谓全者,非独全身也。内以全身,外以全物,物我兼全而归复于性,则其为直也大矣。叶梦得曰:知此则循其本而反之,所谓曲则全者,岂虚言哉!吾诚先得其全,而后归于道,则由枉而下为可知矣。
黄茂材曰:醉者之坠车,虽疾不死。骨节与人同,而犯害与人异,其神全也。全于酒犹若是,况全于天乎?古之至人,天以其全付之,还以其全归之。
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
希言自然。
御注曰:希者,独立于万物之上,而不与物对。列子所谓疑独是也。去智与故,循天之理,不从事于外,故言自然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希者,疏也。易曰:吉人之辞寡。
涑水司马光曰:知道者不言而谕,故曰自然。
颍滨苏辙曰:道之出口,淡乎其无味,视之不足见,听之不足闻,用之不可既,此所谓希言矣。
临川王安石曰:多言数穷,故希言则自然。
陆佃曰:夫物莫能使之然,亦莫能使之不然者,谓之自然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言教出则为迹,未能因于物情,故圣人行不言之教,任自然之理。
达真子曰:道不可闻,故听之不闻则名曰希。希者,冥其声之谓也。
叶梦得曰:此章明言不足以得道,欲得道者,必即道以求之。而道之不行,世始有方术之士,各以其一曲诙诡谲怪,违理而叛道,虽幸或见,不旋踵而亡矣。
清源子刘骥曰:听之不闻名曰希。希言则听乎无声,而无声之中独闻和焉,故自然也。
故飘风不终朝,骤雨不终日。孰为此者?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,而况于人乎?
御注曰:天地之造万物,风以散之,委众形之自化;雨以润之,任万物之自滋。故不益生、不劝成,而万物自遂于天地之间,所以长且久也。飘骤则阴阳有缪戾之患,必或使之,而物被其害,故不能久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形之大者,莫过乎天地;气之广者,莫极乎阴阳。阴阳相激,天地交错,尚不能崇朝终日,何况人处天地之间,不似毫末之在马体乎?而敢纵爱欲,任喜怒,趣取速亡,不亦悲乎!
颍滨苏辙曰:阴阳不争,风雨时至,不疾不徐,尽其势之所至而后止。若夫阳亢于上,阴伏于下,否而不得泄,于是为飘风暴雨,若将不胜,然其势不能以终日。古之圣人,言出于希,行出于夷,皆因其自然,故久而不穷。世或厌之,以为不若诡辞之悦耳,怪行之惊世,不知其不能久也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飘风骤雨,谓不常也,而况人心,岂能常也?
叶梦得曰:夫言之不足尚如此。
黄茂材曰:道无可言,自然而已。自然则久。飘风骤雨,非其自然,故不能终朝日,况于人乎?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其所法也,回转而及自然,自然之功岂易到哉?
故从事于道者,道者同于道,德者同于德,失者同于失。同于道者,道亦得之;同于德者,德亦得之。同于失者,失亦得之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从,为也,顺也。言人为事当从顺于道,希言爱气,永保天和,岂可若飘风骤雨而不久长也。
颍滨苏辙曰:孔子曰:苟志于仁矣,无恶也。故曰:仁者之过易辞。志于仁犹若此,而况志于道者乎?苟从事于道矣,则其所为合于道者得道,合于德者得德。不幸而失,虽失于所为,然必有得于道德矣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圣人从事于自然之道,不强物情。道者同于道,有道者可与语道。德者同于德,谓彼此俱造于德,则可与语于德也。失者同于失,鸺鹠与枭皆以夜为昼,则难与辨其谬失也。
叶梦得曰:非失之云能得道也。因其失而正之,亦可以得乎道也。
黄茂材曰:道至大也。有从事于此,道则同于道,德则同于德,失则同于失。譬之海,广无不容,大无不纳,物之在其中也,无不各得其欲。故道者曰吾得之,德者曰吾得之,失者曰吾得之。失既以为失矣,又焉得曰失道而后德,则德也者,非失而得之乎?失德而后仁,则仁也者,非失而得之乎?失仁而后义,失义而后礼,则义与礼也者,非失而得之乎?夫是谓之大同。
信不足,有不信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仙道贵生,鬼道贵终,盖各以类应也。是以信乎道者得其道;信乎德者得其德。不信于道,轻忽于德,故道亦不应,德亦无称,举之天下岂有信之者哉?
颍滨苏辙曰:不知道者,信道不笃,因其失而疑之,于是益以不信。夫惟知道,然后不以得失疑道也。
达真子曰:信道足,则于道无不信也。信德足,则于德无不信也。
陈象古曰:言乱而理寡,故人不之信。
黄茂材曰:至道甚微,信者寡,不信者多。老子重言及此,悯世人之愚而欲其信也欤!
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
跂者不立,跨者不行。
御注曰:违性之常而冀形之适,难矣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冒进之夫,跂望非分,欲求宠荣,虽苟得之,有若延颈举踵,何能久立乎?
涑水司马光曰:心有所属,故不能两存。
颍滨苏辙曰: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。苟以立为未足而加之以跂,以行为未足而加之以跨,未有不丧失其行立者。彼其自见、自是、自伐自矜,亦若是矣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跨谓不内不外,跨其两端,不一于道也。
达真子曰:跂者非立之常,跨者非行之常。而皆性之强矫,非动之自然者也。
黄茂材曰:跂而欲立,必不能立。跨而欲行,必不能行。
程大昌曰:足之履地为立。跂则腾竦以为高,随足力所及而更迭以进,是之谓步。跨则展布以示阔,贪新失故,且将并其能行能步者而失之。
自见者不明,自是者不彰,自伐者无功,自矜者不长。其在道也,曰余食赘行。
御注曰:泰色淫志,岂道也哉?故于食为余,于行为赘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弃余之食,适使人恶。附赘之形,适使人丑。
涑水司马光曰:皆外竞而内亡。
黄茂材曰:自见其见,不可与明。自是其是,不可与彰。伐者无功,矜者不长。此皆性外事。
程大昌曰:露才扬己之谓自见曰:子既已知,则为自是。夸其劳者为自伐。眩其能者为自矜。凡此数者,不独足己自当,又且广己造大,课其所有,甚狭而无助,故不明不彰,无功不长。
物或恶之,故有道者不处也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凡物尚恶之,况有道之士乎?
叶梦得曰:智之不明,未必皆能恶也。故曰:物或恶之,惟有道者不处。岂必知道而后能辨也。
程大昌曰:见是伐矜,有道者不肯指以为居也。
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
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。
御注曰:气形质具而未相离,曰浑沦。合于浑沦,则其成不亏。易所谓太极者是也。天地亦待是而后生,故云先天地生。然有生也,而非不生之妙,故谓之物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至理湛然而常存,故谓之有物。真道万泒而莫分,故谓之混成。然而混成不可得而知,万物由之以生,故曰有物混成也。先天地生者,道之元也。经曰:吾不知谁子,象帝之先。庄子曰: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,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,先天地生而不为久,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此皆标道之大体也。
颍滨苏辙曰:夫道非清非浊,非高非下,非去非来,善恶混然而成体。其于人为性,故曰有物混成。此未有知其生者,盖湛然常存而天地生于其中耳。
陈象古曰:混成,大道之喻也。道无定象,天地有形,因道而生,故先天地之义昭矣。
叶梦得曰:易曰易有太极,是生两仪,则生两仪者,易也。然不直言易,而设为太极于中者,盖言易之生物不可以正名,故假太极以见,则易与太极固未之有分也。谓太极为生两仪,则有易居其上;谓太极为生于易,则未见太极之有间,故寄之曰有,则易为无也。老子曰: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。则天地生于混成,而混成者亦自有所生也。然不显言其生,而虚生生者于上,亦以生生者不可以正名。
黄茂材曰:有物果何物也?先天地而生天地者也。
林东曰:有物混然而成,则包含万象,圭角不露,皆所以想像道之体质也。必也先天地而生,言是道之有自来也远矣。或以为道在太极之先,则非止在天地先也,亦言其来也远之意。
寂兮寥兮!独立而不改,周行而不殆,可以为天下母。
御注曰:寂兮寥兮,则不涉于动,不交于物,湛然而已。大定持之,不与物化,言道之体。利用出入,往来不穷,言道之用。万物恃之以生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杳冥空洞,无象无质,故曰寂寥。大块卓然,无物可比,妙道廓然,何物偶对?故曰独立。物虽千变万化,出生入死,而妙道未尝迁,故曰不改。且道之用也,散则冲和之气遍于太无,敛则精纯之物藏于黍粟,周流六虚,应用不穷,故曰周行而不殆。夫物无大小,皆仰于道,得之则全,离之则殒,生之成之,咸有所赖,故曰可以为天下母。
颍滨苏辙曰:寂兮无声,寥兮无形,独立无匹而未尝变,行于群有而未尝殆。俯以化育万物,则皆其母矣。
达真子曰:致虚极则曰寂,广远极则曰寥,此有物混成之体也。
陈象古曰:母,取其始生万物也。
叶梦得曰:寂寥之中独立而周行者,彼亦不过动静之两间尔。学者多不能明寥之义与寂同为静,非也。古者谓大风之声为寥,吹万窍而怒号者,寥能覆之,则安得为静乎?寂言静也,寥言动也。惟寂故能独立而不改,惟寥故能周行而不殆,此其所以能母天下者也。
吾不知其名,字之曰道,强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,逝曰远,远曰反。
御注曰:运而不留故曰逝,应而不穷故曰远,归根曰静,静而复命故曰反。道之中体方名其大,则遍覆包含而无所殊,易所谓以言乎远则不御也。动者静,作者息,则反复其道,不离乎性,易所谓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也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凡物之大皆有边际。惟道之大,无穷无极,往无涯畔,故云大曰逝;愈逝愈远,莫究其源,故云逝曰远。虽远出八荒之外,逐之不逮,而收视反听,湛然于方寸之间,若鉴之明,应而不藏,故云远曰反。反,复也。
颍滨苏辙曰:道本无名,圣人见万物之无不由也,故字之曰道;见万物之莫能加也,故强为之名曰大。然其实则无得而称之也。自大而求之,则逝而往矣;自往而求之,则远不及矣。虽逝虽远,然反而求之,一心足矣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不可名字而强名曰道也。道非大小,既强名之,不可不谓之大矣。逝者,往也。道不止于大,又能逝而遍于万物,既以谓逝,则无往不周,虽曰远,未尝离本,故曰返。
清源子刘骥曰:不可得而名,故吾不知其名。以其万物之无不由也,故字之曰道;以其万物之莫能加也,故强为之名曰大。自大而求之,则测之益深,穷之益远,故曰逝;自逝而求之,则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,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,故曰远。虽远至六合之外,无穷无尽,然反求诸己,不离乎方寸之中,故曰反。
林东曰:字曰道,强名曰大,然其实则无得而称之也。不特如是其大,大则直块然一物矣。大而又能逝,逝而远,远而又反,则非泛然无统、虚无荒唐之说甚矣。反之一字,见大道之道,与吾儒不隔蝇翼,或者不可以老氏、孔子差殊观也。
故道大、天大、地大、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,而王处一焉。
御注曰:道,覆载天地者也。天无不覆,地无不载。王者位天地之中而与天地参,故亦大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王者,黔黎之首,不敢与天地道为比,故云亦也。域中有四大者,谓道、天、地、王也。域者,限域也。夫道大包宇宙,细入秋毫,或超象外,或处域中,自地而上皆属于天,苍苍之谓也。天在地外,地处天内。王者人伦之尊,居九州之间,此皆处于域中,故曰域中有四大也。而又王者参天地之道,而秉万物之权,于四大之中预其一焉。庄子曰:莫神于天,莫富于地,莫大于帝王。帝王之德配天地,故曰王居其一焉。颖滨苏辙曰:由道言之,则虽天地与王皆不足大也。然世之人皆知三者之大,而不信道之大也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无不化育,故曰大;无不覆焘,故曰大,无不持载故曰大。人者,三才之一,非君何以统制?域者,谓限制之名,虽有名而无边际之实,范围万物者也。凡言天则造物可知矣,凡言地则成物可知矣,凡言王则人道可知矣。灵秀智力莫出于人,而王统之大也。
清源子刘骥曰:王亦大者,王指人心而言之,经所谓心为国主五藏王是也。人心潜天而天,潜地而地,俯仰之间,再抚四海,恍惚之际,经纬万方,亦可谓大矣。故域中有四大,而王处一焉。此使人知自贵自爱,而不陷溺其良心也。
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此戒王者当法象二仪,取则至道,而天下自然治矣。夫王者守雌静,则与阴同德,其所载无私,是法地也。又不可守地不变,将运刚健,则与阳同波,其所覆至公,是法天也。复不可执天不移,将因无为,则与道同体,其所任物咸归自然,是法道自然。此谓王者之法天地,则至道也,非天地道之相法也。宜察圣人垂教之深旨,不必专事其空言而已矣。
颍滨苏辙曰:故以实告之。人不若地,地不若天,天不若道,道不若自然。然使人一日复性,则此三者人皆足以尽之矣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人与地近,形著而位分,故法则于地,而知刚柔之分。地静而承顺,法则于天,清明刚健,崇高至极,而未能混于无形,故法于道也。道无可法,自然而已。
达真子曰:道也者,固无所法也。以其相因而相成,相继而相用,固若其法尔。王者能尽人道,以人道之施为则应于地,故人法地也;以地道之化养则应于天,故地法天也;以天之运用则应于道,故天法道也;以道之充塞则应于自然,故道法自然也。然则有物混成之初,信以为天下之母矣。
道德真经集注卷之六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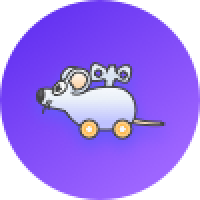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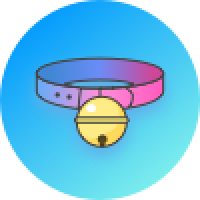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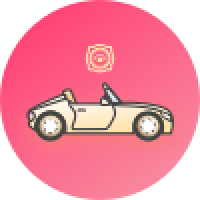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