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 鹤 林 彭 耜 纂 集
重为轻根章第二十六
重为轻根,静为躁君。
御注曰:重则不摇夺而有所守,故为轻根。静则不妄动而有所制,故为躁君。
颍滨苏辙曰:凡物轻不能载重,小不能镇大,不行者使行,不动者制动。故轻以重为根,躁以静为君。
临川王安石曰:轻者必以重为依,躁者必以静为主。
叶梦得曰:重轻在身,必有所本,故以根言之。静躁在心,必有所制,故以君言之。木之生,自拱把至合抱必有根焉,然后枝叶有所赖。不深其根而丰其末,末胜则本必拔矣。故身不可以不重。心之物为火,炎上而善缘,炎上则愈进,善缘则莫知己,非有以制之则必炽。躁者动而不知守者也,故心不可以不静。
黄茂材曰:轻躁之人不可进于道。重则其本固,故为轻根。静则其主安,故为躁君。是以君子终日行,不离辎重。
御注曰:静重以自持,则失之者鲜。君子终日行,不离辎重,是以履畏途而无患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辎,屏车也,又大车也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辎重谓保身之宝,随而资用,不可须臾离也。达真子曰:如君子虽终日行不离辎重者,盖非辎重则不可行,是则轻本于重也。
清源子刘骥曰:君子之处己,贵乎重静,戒乎轻躁,故终日行不离辎重,谓如辎车之重,不敢容易其行。
虽有荣观,燕处超然。
御注曰:荣观在物,燕处在身。身安然后物可乐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虽有荣盛可观之事,不能移其志,游观荣乐,无所系著。
清源子刘骥曰:荣观在物,燕处在己。不以物易己,不以美害生,超然自得于物外,取足于身而已。
如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?轻则失臣,躁则失君。
御注曰:天下,大物也。有大物者,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,故不可以身轻天下。不重则不威,故失臣。不倡而和则犯分,故失君。
颍滨苏辙曰:轻与躁无施而可。然君轻则臣知其不足赖,臣躁则君知其志于利。故曰:轻则失臣,躁则失君。
临川王安石曰:臣者,佐也;君者,主也。静为动之主,重为轻之佐。轻而不知归于重,则失于佐矣;动而不知反于静,则失其主矣。
王雱曰:人主以天下为根,不可以一身故轻之。
陈象古曰:王者治天下之大,当守其重,处其静,以镇轻浮,以杜僭躁。不可以欲之所纵,身之所贪,轻忽妄动,而忘治天下之道。
清源子刘骥曰:叹人不知贵爱其身,残生伤性,动之死地。是犹处万乘之尊,居大宝之位,轻身躁动,不顾天下者也。轻则妄动,故失臣;躁则扰民,故失君。圣人重而不轻,静而不躁,所以无为而天下功。
黄茂材曰: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,是其能持重也。虽有荣观,晏处超然,是其能守静也。奈何万乘之主,而以身轻天下?人身中自有一天下。万乘之主,指心为言。君者,心也。臣者,肺为相傅之官,肝为将军之官,胆为中正之官,膻中为臣使之官。仓库官,脾胃是也;传道官,大肠是也;受盛官,小肠是也;作强官,肾是也。三焦者,决渎之官。膀胱者,州都之官。失君,心乱;失臣,五脏六腑乱。
善行章第二十七
善行无辙迹;善言无瑕谪;善计不用筹筭;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;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。
颍滨苏辙曰:乘理而行,故无迹。时然后言,故言满无口过。万物之数毕陈于前,不计而知,安用筹筭?全德之人,其于万物,如母之于子,虽纵之而不去,故无关而能闭,无绳而能约。
临川王安石曰:不疾而速,不行而至,故无辙迹。巵言日出,和之以天倪,因之以曼衍,故无瑕谪。六合之内,万物之间,不能逃其数,故不用筹筭。万物不得其门而入,故无关楗而不可开。
达真子曰:善行者,以道为行者也。以道为行,故行于内而不行于外,是以善行无辙迹。善言者,以道为言者也。以道为言,故言于正而不言于邪,是以善言无瑕谪也。善计者,以道为计者也。以道为计,故计于心而不计于物,是以善计不用筹筭也。心处于道,不为外物之所入,是以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也。心聚于道,不为外物之迁离,是以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也。
清源子刘骥曰:以其不为而为,故善行无辙迹之可寻;以其道之出口,故善言无瑕谪之可累。以其通于一而万事毕,故善计不用筹筭。以其形全精复,非爱欲所能诱,故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;以其神凝气定,虽天地不能犯,故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。
黄茂材曰:行不违道,故无辙迹;言不失中,故无瑕谪。善计不用筹筭,一,可以知万也,何用筹筭?善闭,无关楗而不可开,其精固而不泄也,何用关楗?善结,无绳约而不可解者,阴阳之气自然相合也,何用绳约一?
是以圣人常善救人,故无弃人;常善救物,故无弃物。是谓袭明。
御注曰:袭者,不表而出之。袭明则光矣而不曜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常善者,谓蕴其常道,善达自然之理也。袭明者,圣人密用其常道,而能明悟任物也。
颍滨苏辙曰:彼方执筭以计,设关以闭,持绳以结,其力之所及者少矣。圣人之于人,非特容之,又善救之。我不弃人,而人安得不我归乎?救人于危难之中,非救之大者也。方其流转生死,为物所蔽,而推吾至明以与之,使暗者皆明如灯,相传相袭而不绝,则可谓善救人矣。叶梦得曰:常之为言,无时而不然也。救之为言,迫而后应之,不迫则不强施也。
清源子刘骥曰:非特圣人有是心也,人物皆有之。方其以伪丧真,以物易性,则固有之真性暗而不明,郁而不发,圣人常善救之而无弃,使之归根复命,收视返听,室虚而纯白生,宇定而天光发,如灯之明,相传袭而不绝,故是谓袭明。
黄茂材曰:凡此皆人身中物,修之而至,为之而成。经曰:恍兮惚,其中有物。人谁不具此物,迷而不知尔。圣人善救之,无弃人,亦无弃物,使之自明而已,故谓袭明。
故善人,不善人之师;不善人,善人之资。
御注曰:资以言其利。有不善也,然后知善之为利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故立天子、置三公,此将以教不善之人也。故曰:善人,不善人之师。设有不善之人,善人亦资取役使,以渐化导之。经曰:善者吾善之,不善者吾亦善之,得善。信者吾信之,不信者吾亦信之,得信。此以德化摄伏不善人,为资给役用也。
达真子曰:善人者,得此五善之人也;不善人者,失此五善之人也。得此五善之人,可以救其不善。故善人,不善人之师也。失此五善之人,故善人取以为戒,故不善人,善人之资也。然则不善人因其善人之袭己,则得其师;善人因其不善人之袭己,则得其资。是皆因袭而明也。
清源子刘骥曰:善人者,因其善而师之,故不善人之师。不善人者,因其不善而改之,故善人之资。
林东曰:善人为善,可师也。见不善而不为之,是可资也。
不贵其师,不爱其资,虽智大迷,是为要妙。
御注曰:天下皆知善之为善,斯不善已。善与不善,彼是两忘,无容心焉,则何贵爱之有?此圣人所以大同于物道之要妙。不睹众善,无所用智,七圣皆迷,无所问途。义协于此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夫圣人虽游心于自得之场,不可不立其师资也。虽立师资,复恐贵尚其师,怜爱其资,泥于陈迹,不至远达,故再举不贵其师、不爱其资者。夫人虽因师之发蒙,寻其至理,出自天性,是曰独化。故伯乐不能驭驽骀为骐骝,良匠不能伐樗栎为栋梁,将使人忘其企慕,然后可造至道之极。故列子之师老商、友伯高而得风仙,既而曰:不知夫子之为我师,若人之为我友,不知风乘我耶?我乘风耶?内外尽矣。此真忘其师资者也。圣人虽知小夫执滞言教,必以此言大为迷谬,然而垂训上士,使彼我俱忘,乃至言要妙之道也。
颍滨苏辙曰:圣人无心于教,故不爱其资。天下无心于学,故不贵其师。圣人非特吾忘天下,亦使天下忘我。又曰:圣人之妙,虽智者有所不谕也。
达真子曰:苟不贵其师,则不善者不知修;不爱其资,则已善者不知戒。若是则虽有智者,亦入于大迷矣,况其不智乎?然能以是推之,则得其道之要妙也。
黄茂材曰:以善为师,以不善为资。贵其师犹为人情所同,爱其资是何心哉?至人淡然无所贵爱,善者吾善之,不善者吾亦善之,虽有智者,于此大迷,是谓要妙。
知其雄章第二十八
知其雄,守其雌,为天下溪。为天下溪,常德不离,复归于婴儿。知其白,守其黑,为天下式。为天下式,常德不忒,复归于无极。知其荣,守其辱,为天下谷;为天下谷,常德乃足,复归于朴。
御注曰:雄以刚胜物,雌柔静而已。圣人之智,知所以胜物矣,而自处于柔静,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,故为天下溪。溪下而流水所赴焉,盖不用壮而持之以谦,则德与性常合而不离,是谓全德。故曰常德不离,复归于婴儿。气和而不暴,性醇而未散,婴儿也。孟子曰:大人者,不失其赤子之心。白以况德之著,黑以况道之复。圣人自昭明德而默与道会,无有一疵,天下是则是效,乐推而不厌,故为天下式。正而不妄,信如四时,无或差忒。若是者,难终难穷,未始有极也。故曰:常德不忒,复归于无极。书于洪范言王道曰归其有极,老氏言为天下式者,复归于无极。极,中也。有极者,德之见于事以中为至。无极者,德之复于道不可致也。为天下谷,谷,虚而能受,应而不藏。德至于此,则至矣,尽矣,不可以有加矣。故曰:常德乃足。朴者,道之常体。复归于朴,乃能备道。夫孤、寡、不谷,而王公自以为称,故抱朴而天下宾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雄,尊显也,强梁也,先也。雌,卑微也,柔弱也,退也。夫有道之士,知己之尊显,出人之先,纵之则强梁生而祸患至矣。乃处身卑微,守其柔弱,谦退下位,而天下归服其德,如水之流入深溪。既心宇如溪,是能保其常德,不离于身,去刚躁之欲心,复性归于婴儿也。婴儿者,谕其怕然淳和,是非都泯也。溪者,水注川曰溪。有道之士,知己之心字如溪,由虚室生白,昭昭明了,乃守其渊默,持之自晦,使光而不曜,此可为天下之法式矣。人既模楷法式者,是见其常德无所差忒。德不差忒,将与道冥极也。极者,言其深不可穷极也。人所归服而模楷法式,是己之尊荣,在民之先,当守其卑辱,持胜自污而受众垢。若此则天下归心,如水之投于深谷。夫器量如谷,是内德充足。德充而无名,则复归于道朴也。朴者,谓隐材器而藏用也。谷者,水注溪曰谷。
颍滨苏辙曰:雄雌,先后之及我者也;白黑,明暗之及我者也;荣辱,贵贱之及我者也。夫欲先而恶后,欲明而恶暗,欲贵而恶贱,物之情也。然而先后之及我,不若明暗之切;明暗之及我,不若贵贱之深。古之圣人,去妄以求复性。其性愈明,则其守愈下;其守愈下,则其德愈厚;其德愈厚,则其归愈大。盖不知而不为,不若知而不为之至也。知其雄,守其雌,知性者也。知性而争心止,则天下之争先者皆将归之,如水之赴溪,莫有去者。虽然,譬如婴儿,能受而未能用也,故曰复归于婴儿。知其白,守其黑,见性者也。居暗而视明,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,故众明则之以为法,虽应万物而法未尝差,用未能穷也,故曰复归于无极。知其荣,守其辱,复性者也。诸妄已尽,处辱而无憾,旷兮如谷之虚,物来而应之,德足于此,纯性而无杂矣,故曰复归于朴。
达真子曰:盖性复于婴儿,然后造于无极,造于无极,然后反于朴,固其入道之序也。德之不离,然后不忒,德之不忒,然后乃足,固其入德之序也。为众有所归,若其溪,然后为天下式,既为天下式,则万善为一己之所容,然后为天下谷,固其所至之序也。盖有常性然后有常德,有常德然后有常道,其序也。
清源子刘骥曰:天一生水,在人为精,阴中之阳也,故谓之雄。地二生火,在人为神,阳中之阴也,故谓之雌。知其雄者,保其精也;守其雌者,存其神也。纯素之道,唯神是守,守而勿失,与神为一,虚无自然也。身之虚而万物至,心之无而和气归,如水之注溪,不召而自来,故为天下溪。为天下溪,则德与性合而不离。故常德不离,复归于婴儿。婴儿者,居不知所为,行不知所之,所以俗人昭昭,我独若昏;俗人察察,我独闷闷。故知其白,守其黑也。知白守黑,则慧而不用,实智若愚,定慧相资,智恬交养。守道之精,杳杳冥冥;守道之极,昏昏默默。炼虚无之体,成自然之真,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故为天下式。为天下式,则德与性合而无差忒。故常德不忒,复归于无极。无极者,无穷无极,同于大通,与道为一。圣人体道之真,不以物易己,不以美害生,虽有荣观,燕处超然,大白若辱,盛德容貌若愚,故知其荣,守其辱也。知荣守辱,则纳污藏垢,无所不容,如谷之虚,无所不纳,故为天下谷。为天下谷,则反归真空,与道合体,故常德乃足,复归于朴。朴者,道之大全,谓如混沌之始朴,一元之初生也。
黄茂材曰:夫道,虚无恬淡,清静无为,超然出于群物之上。谓之雄可也,何以为雌?谓之白可也,何以为黑?谓之荣可也,何以为辱?盖道欲退藏,非有所眩耀于世,虽知其雄,乃自处以雌;虽知其白,乃自处以黑;虽知其荣,乃自处以辱。故能为天下溪,可以行也;为天下式,可以法也;为天下谷,可以容也。夫道至大,求之者多各从其所入。为天下溪,常德不离,复归于婴儿。孰为婴儿非道乎?此自其德之不离而入于道者也。为天下式,常德不忒,复归于无极。孰为无极非道乎?此自其德之不忒而入于道者也。为天下谷,常德乃足,复归于朴。孰为朴非道乎?此自其德之乃足而入于道者也。惟道难言,言之不足,至于再三,又使其音韵句读相类,可以诵咏于口而不忘。老子之意,所以开示后人,何其详且至耶!
朴散则为器,圣人用之则为官长,故大制不割。
御注曰: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。有形名焉,有分守焉。道则全,天与人合而为一。器则散,天与人离而为二。道之全,圣人以治身。道之散,圣人以用天下。有形之可名,有分之可守,故分职率属而天下理,此之谓官长。易曰:知微知彰,知柔知刚,万夫之望。与此同义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夫复于道朴,则浑沦窅冥,视之不见,听之不闻,此乃体冥真理者也。若于治道,则当散而为器。河上公曰:万物之朴散则为器用。若道散则为神明,流为日月,分为五行也。夫人真心之散则为念虑。念虑一动则百行彰而庶事生。庶事者,材器也。故圣人就其材器,因其贤能,而用为百官之元长,故能大制群物,任之自然而不割伤也。
颍滨苏辙曰:圣人既归于朴,复散朴为器以应万物。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长,亦因其势之自然,虽制而非有所割裂也。
陆佃曰:朴者言其合也,器者言其离也。浑则合,合则为朴;割则离,离则为器。器者朴之反也。故圣人割而用之,则为官长。故大制不割。
刘槩曰:大制不割,谓长而不宰是也。盖无为而用天下,则大制不割矣。大制者,小以成小,大以成大,吾以为之宰。守雌未及乎守黑,守黑未及乎守辱,守辱则玄之又玄。
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:旧曾自注曰:制度之大者,无裁割之迹。有山东刘正叟者,以道冲此言说于王雱,雱乃注在经中。今复别注曰:大制,天地之造物也。物自随性而成,不烦裁制也。
达真子曰:凡制物以割者使然也。今大制天下而不割,则道任乎自然矣。
陈象古曰:朴散为器,有用有形之至也。官长治,为器之主也。总其器之大小,任其材之长短,入用则合,任过则离,皆自然之道也。岂假圣人强力以割之哉!
黄茂材曰:朴者,道也,浑然而已,散则为器。圣人体道而用之,物莫尊于道,故为官长。夫以道制天下者,何用割为?
将欲章第二十九
将欲取天下而为之者,吾见其不得已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已,死也。老子以谓非徒失道,必见其不得死。
颍滨苏辙曰:圣人之有天下,非取之也,万物归之,不得已而受之。其治天下,非为之也,因万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。若欲取而为之,则不可得矣。
黄茂材曰:取天下者,汤武是也。使汤武取天下而欲为之,其不能得亦可见矣。一人之身为物之所侵寇者甚多,欲取其身于声色纷扰之涂,置于清静自得之场而乃为之,则是自乱也。
程大昌曰:因其理之当然,循而行之,不敢参以己意,是之谓以天下为天下,而非己之敢任也。若屈当然之理而自出操纵,是取天下而为之者也,故知其决不能遂也。不得已者,欲取而不遂也。
天下神器,不可为也。为者败之,执者失之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七窍凿而混沌死,鞭策威而马力竭,岂非为者败之乎?而又执而不移,自谓圣治,非惟丧于至理,亦将自失其真。故曰:执者失之。
颍滨苏辙曰:凡物皆不可为也。虽有百夫之聚,不循其自然而妄为之,必有龃龉不服者,而况天下乎?虽然,小物寡众,盖有可以力取而智夺者。至于天下之大,有神主之,不待其自归则叛,不听其自治则乱矣。
清源子刘骥曰:天下神器,谓天地神明之器,人之形体,法象天地,化契阴阳,乃神器也。游心于淡,合气于漠,顺物自然,无容私焉,而天下治。将欲取天下而为之,则以人灭天,以故灭命,吾见其不得已。黄帝南望而元珠遗,七窍始凿而混沌死,故不可为也。为则有败,执则有失。
黄茂材曰:天下神器,不可为也,不可执也。至于人身,独非神器乎?目何为而视,耳何为而听乎?足何为而动,皆其神尔。古之人能养其神,超然独存,谓之神人,是岂可为可执也欤?
故物或行或随,或嘘或吹,或强或羸,或载或隳。是以圣人去甚、去奢、去泰。
御注曰:万物之理,或行或随,若日月之往来;或嘘或吹,若四时之相代;或强或羸,若五行之王废;或载或隳,若草木之开落。役于时而制于数,固未免乎累。唯圣人为能不累于物,而独立乎万物之上,独往独来,是谓独有。独有之人,是谓至贵。故运神器而有余裕,物态不齐而吾心常一。又圣人睹万物之变迁,知满假之多累,故无益生,无侈性,无泰至,游乎券内而已。若是,则岂有为者之败、执者之失乎?故曰:繁文饰貌,无益于治。
碧虚子陈景元曰:此八事谓外物不可必也。甚、奢、泰皆过当越分,因兹甚、奢、泰致其为之,故老氏之特垂深戒。
颍川苏辙曰:阴阳相荡,高下相倾,大小相使,或行于前,或随于后,或呴而暖之,或吹而寒之,或益而强之,或损而羸之,或载而成之,或隳而毁之,皆物之自然而势之不免者也。然世之愚人,私己而务得,乃欲拒而违之,其祸不覆则折。唯圣人知其不可逆而顺以待之,去其甚,去其奢,去其泰,使不至于过而伤物,而天下无患矣。此不为之至也。尧汤之于水旱,虽不能免,而终不至于败,由此故也。易之泰曰:后以财成天地之道,辅相天地之宜,以左右民。三阳在内,三阴在外,物之泰极矣。圣人惧其过而害生,故财成而辅相之,使不至于过,此所谓去甚去奢去泰也。
临川王安石曰:安于所安,则能去甚;以俭为宝,则能去奢;以不足自处,则能去泰矣。
陈象古曰:此过常逾分之谓也。如是者何由为之?执之不知其要故也。
清源子刘骥曰:譬如万物之理,有行则有随,有嘘则有吹,有强则有羸,有载则有隳,物之变化,何常之有?唯圣人体道之常,无古无今,与道为一而合于自然。去甚去奢、去泰,则体道之自然而养其心矣。
黄茂材曰:凡物或行而前,或随而后,或嘘之则煖,或吹之则寒,或其势强,或其力羸,或始而载,载,安也,盛也。或终而隳。其行也,其嘘也,其强也,其载也,近于太过;其随也,其寒也,其羸也,其隳也,近于不及。是以圣人去甚、去奢、去泰,务适其中而已。经曰:多言数穷,不如守中。
程大昌曰:甚也,奢也,泰也,则不可不去,而未至于己甚,己奢、己泰,则置之勿论。曹参从盖公学黄老,而曰不扰狱市,以为狱市奸人之所容也,而扰之,则奸人无所容也。
道德真经集注卷之七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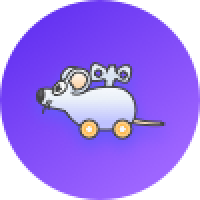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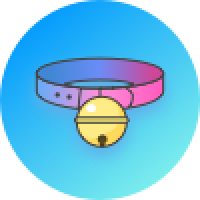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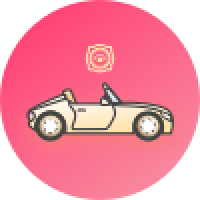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