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坤者易之门户章第一
【题解】
本章是《周易参同契》全书的纲领。乾坤门户,在丹道为炉鼎;坎离匡郭,在丹道为药物。
以《易》言之,乾、坤为纯体之卦,乾阳而坤阴,乾、坤错杂,乃生震、坎、艮、巽、离、兑六子卦,合乾、坤父母卦与六子卦,则为《易》之“八经卦”;而《周易》六十四“别卦”,皆由“八经卦”重卦而得。因众卦皆出于乾、坤,故以乾、坤为《易》之门户,众卦之父母。
《周易参同契》言“乾坤者易之门户”,别有其意。以外丹言之,乾为上釜之鼎,坤为下釜之炉,炉鼎为炼丹之神室;欲炼还丹,先设乾鼎、坤炉为神室,神室既设,变化就会在其中生成,非神室无以成丹,犹如非乾、坤则无以见《易》。乾鼎、坤炉既设,投铅、汞等药物于其中,铅取象于坎,汞取象于离,故经文所说之坎、离是为药物。坎、离药物在乾、坤鼎炉中烹炼,发生种种变化,乃至铅、汞合体,凝而至坚,化成丹宝,是谓变易。以此之故,也可以说,乾、坤为易之门户,众卦之父母。又,坎为水,离为火,火燃于器外,各种矿金置于器中,得火烹炼,熔而为水,水火气交,然后通达其情,化金水成丹。因坎水、离火二气相互含受,取象城郭之匡方、周正,即所谓“坎离匡郭”。炼丹之时,火性常动,水性常静,静以比轴,动以比毂,其运转犹如车之毂与轴,故又有“运毂正轴”之说。
以内丹言之,人之一身,法天象地,与天地同一阴阳。乾、坤既奠,阴阳自交,乾下交坤而为坎,坤上交乾而为离。就人而言,乾阳为首在上,坤阴为腹在下,丹道所谓坎,可以喻指人身中的精与炁,它关乎人之身与命;其所谓离,可以喻指人之神,它关乎人之心与性,人身之坎、离变化,实指人身当中精、炁、神的变化。坎、离匡郭、相交,喻指人之神、炁相抱、性命双修,丹家谓之“取坎填离”。易学之后天八卦,以坎、离冠首;先天八卦,以乾、坤冠首。丹家以“先天”代表人处于其性、命之真的理想状态,“后天”则喻指人本真之性、命处于异化的状态。坎中之阳填入离中之阴后,坎、离变而为乾、坤,则人可以从所谓的“后天”返回到“先天”。经文中之“毂”,可喻人之身;“轴”,可喻人之心;欲“毂”之运,必正其“轴”;同理,修内丹者,必正其心,方能修其身,从而由“凡”变易成“仙”,由“后天”返回“先天”,此则为丹道之“易”。
乾、坤者[1],《易》之门户[2],众卦之父母[3]。坎离匡郭[4],运毂正轴[5]。
【注释】
[1]乾、坤:狭义地讲,为《周易》开篇起首的两卦,其中,乾为纯阳之卦,坤为纯阴之卦。广义地讲,乾为阳的代表,坤为阴的代表,乾、坤为宇宙天地间阴、阳两气之总称。
[2]易:狭义指《易经》。广义地讲,则凡宇宙天地间所有的阴阳变化,皆可谓“易”。门户:单扇为门,双扇为户,人之出入,皆从门户,故门户有“枢纽”、“开关”之义。因乾卦之阳爻与坤卦之阴爻相互作用,成《易经》六十四卦,故乾阳、坤阴为《易经》之“门户”、枢纽。引而申之,乾阳、坤阴实乃宇宙天地间所有变化的枢机、门户。《周易参同契》此说,源自《周易·系辞》:“子曰:‘乾、坤,其《易》之门邪?’乾,阳物也;坤,阴物也。阴阳合德,而刚柔有体,以体天地之撰,以通神明之德。”又:“乾、坤,其《易》之缊邪?乾、坤成列,而易立乎其中矣。乾、坤毁,则无以见《易》。”
[3]众卦:有两层意思:一是指乾、坤两卦所生之震、坎、艮、巽、离、兑六子卦。其中,坤得乾之初爻,为长男震卦;得乾之中爻,为中男坎卦;得乾之上爻,为少男艮卦;而乾得坤之初爻,则为长女巽卦;得坤之中爻,为中女离卦;得坤之上爻,为少女兑卦。此说源于《周易·说卦》:“乾,天也,故称乎父。坤,地也,故称乎母。震一索而得男,故谓之长男。巽一索而得女,故谓之长女。坎再索而得男,故谓之中男。离再索而得女,故谓之中女。艮三索而得男,故谓之少男。兑三索而得女,故谓之少女。”另一层意思是指乾、坤父母与六子卦,构成《周易》之“八经卦”,“八经卦”为三爻之卦,“八经卦”相互重叠,而有《周易》六十四“别卦”,“别卦”皆六爻之卦,六十四“别卦”,亦皆由乾之阳爻与坤之阴爻所构成,故“众卦”亦可代指整个《周易》六十四“别卦”。父母:此处指乾阳、坤阴。凡《周易》众卦之阳爻,皆得于乾之阳;众卦之阴爻,皆得于坤之阴,故乾阳、坤阴,所以为“众卦之父母”。
[4]坎、离:狭义地讲,为《周易》上经结尾之两卦,或谓“八经卦”中的坎、离两卦。广义地讲,坎卦阴中有阳,可以取象水、月亮、铅金等;离卦阳中有阴,可以取象火、太阳、流汞等。坎、离,通常被丹道喻为“药物”。匡郭:匡,同“筐”;郭,即城郭。坎,一阳陷在两阴之中;离,一阴陷于两阳之中,坎藏于坤,离藏于乾,犹如筐中藏物,郭中藏城,即所谓“坎离匡郭”。或谓坎、离两卦相抱于外,其内空虚,合内虚与外实而成匡郭之状,如北宋周敦颐“太极图”第二圈之“坎离相抱图”所示。又,《周易参同契》以《周易》乾、坤、坎、离四卦建构了一个宇宙模型,其以乾为天、坤为地,坎为月、离为日,乾天、坤地定上下之位,坎月、离日列东、西之门,乾、坤、坎、离四卦之结构,犹如城市、垣郭之四方匡正;日、月升降于天地之间,循环而无穷,犹如城郭之垣墙首尾相联、贯通,此亦可谓“坎离匡郭”。《周易参同契》于此提出乾、坤、坎、离四正卦之说,其与汉易卦气说以坎、离、震、兑为四正卦的说法有所不同,开后来宋代图书易学先天、后天之说的先河。从外丹的角度,则坎是铅金,离是流汞,以铅、汞二宝为丹,置于鼎中,上安水,下安火,用水火“匡郭”上下釜,使鼎受水火之气,伏汞为丹。其所谓“匡”为辅之义,“郭”则为鼎器。
[5]毂(gǔ):指车轮之心,外实而持辐,内空以受轴。轴:为车下之横木,其两头贯毂而承车之体。坎月、离日于天地间升降,其象如车轴之贯毂以运车轮,一下而一上。此说源出于《道德经》:“三十辐共一毂,当其无,有车之用。”(十一章)《周易参同契》认为,乾、坤设位,坎、离成能,欲使坎、离之毂运转不偏、不倚,须得乾、坤之轴居于其正位。
【译文】
乾为纯阳、象天,坤为纯阴、象地,这两卦实乃《易》之门户,众卦之父母。坎卦象月,阴中有阳;离卦象日,阳中有阴;坎藏于坤,离藏于乾,犹如筐中藏物、郭中藏城,欲得坎月、离日交替、往来,升降于乾天、坤地之间,应该法车轮运转之理,必正其轴,方能运其毂。
牝牡四卦章第二
【题解】
本章言修丹之药物烹炼有其火候法度和数理。
以外丹言之,凡修金液还丹,鼎中有金母华池,亦谓之金胎神室,神室既设,则药物就可以在其中烹炼。乾、坤、坎、离四卦,乾、坤为鼎器,坎、离象药物;乾为阳牝,乃上鼎,坤为阴牡,为下炉。乾鼎、坤炉有阖、有辟,坎、离药物在鼎器中烹炼,有往有来,皆如橐籥气出、气入之状。阴阳,可以指铅金、流汞二味药物,铅金为阳,流汞为阴,金在中而时动,汞居外而常转,汞欲逃逸,金能制之,故一阴一阳,乃变易之道。鼎在炉中、药在鼎中,皆得外面火、水所制,故“处中以制外”。炼丹当守御鼎器,牢牢固济,恐其有所走失。炼丹有进火、退符,如一月三十日刚柔各半,昼为刚阳,夜为柔阴,刚柔相交之时,喻指金、汞会合之际,炼外丹讲究要择元日泥灶,火日杀汞,成日合捣,收日炼冶,闭日入鼎,建日祭炉,王、相日服药,如此等等,其法度、数理合于律、历之数。阴阳以气言,刚柔以形言,变化始于气而后成形,形为金汞,气乃烹炼时的水火之气,以水火之气变金汞之形,炼成至宝之丹。此章概言炼丹要依天地之大数,协阴阳之化机,如果能控御不差,运移不失,有如善工者准绳墨以无差,能御者执衔辔而不挠,合其规矩轨辙,则可以外交阴阳之符,内生龙虎之体,炼成金丹。
以内丹言之,乾、坤鼎器为修道之人的上、中、下三丹田,坎、离药物为修道之人身中的精、炁与神,故以乾、坤、坎、离四卦涵盖、总括人身之阴阳,其功能有如橐籥生风,能造化生成万有。人之心神可以统率一身阴阳之精炁,其与月受日光、为日之所使在理上是相通的。修道之人只要一心不乱,念念归中,处其理于中,则自能制其妙于外,从而行无差忒,动合自然,神、炁相抱,神妙不测之变化历历于身内外出现,不必刻意关注功夫与效验,而功夫、效验自来,且有其法度与数理,如同律、历一般精准无误。此亦犹工匠准绳墨于内,而规矩自能正于外;驾驭车马者执衔辔于内,而车轮之轨辙自能随合于外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,除乾、坤、坎、离四卦为鼎炉、丹药,丹道用余下的六十卦表示炼丹之火候。
牝牡四卦[1],以为橐籥[2]。覆冒阴阳之道[3],犹工、御者[4],准绳墨[5],执衔辔[6],正规矩[7],随轨辙[8]。处中以制外[9],数在律历纪[10]。月节有五六[11],经纬奉日使[12]。兼并为六十[13],刚柔有表里[14]。
【注释】
[1]牝(pìn)牡:“牝”指雌性、阴性的事物,“牡”指雄性、阳性的事物。四卦:《周易》中,乾为纯阳牡卦,坤为纯阴牝卦;坎卦阴中有阳,离卦阳中有阴,为牝牡相交之卦。因乾、坤、坎、离四卦覆盖、涵蕴纯阴、纯阳、阴阳相交之道,故谓之“牝牡四卦”。另外,也有以震、兑、巽、艮为“牝牡四卦”的说法。因《周易参同契》月体纳甲法中,坎月、离日相互作用,产生种种月相,其中,乾纯阳代表月之望;坤纯阴代表月之晦;初三日弯弯之娥眉月生明,以震为代表;初八日月至上弦,以兑为代表;而巽为月之生魄、艮为月之下弦。震、兑、巽、艮四卦所代表之月相变化,如风箱之鼓动,有缓急的变化,亦可谓“牝牡四卦”。
[2]橐(tuó)籥(yuè):即风箱,冶工用以鼓风之器具。橐,即鞴囊、方袋子,无孔。籥,为其管、楗,有孔以出气。风箱形似方形的袋子,上面插有管、楗,拉动风箱,则有风出。丹法位乾鼎、坤炉于上下,投坎、离药物于其中,乾鼎、坤炉有阖、有辟,坎、离药物在鼎器中烹炼,有往有来,皆如橐籥气出、气入之状。所以,经文说“牝牡四卦,以为橐籥”。此说源出老子《道德经》:“天地之间,其犹橐籥乎?虚而不屈,动而愈出。”(五章)
[3]覆冒:有覆盖、涵蕴之义,或者包、裹之义。阴阳之道:在天地间,如昼夜之更替,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时之迭运,十二月、二十四气、七十二候之循环往复等,皆为阴阳之道。于丹道言,阳鼎、阴炉,铅汞药物,刚火、柔符等等,皆需依天地之数、契阴阳之机,此谓丹家的阴阳之道。
[4]工:指工匠。御:指驾车者。
[5]准绳墨:准,为工匠用以验平的器具。绳,为工匠用以验直的绳线,通常以黑墨浸泡之,故谓“绳墨”。《周易参同契》以此谓炼丹自有一定的法度、火候,亦犹工者准绳墨,而能得平、直之线、面一样。
[6]衔辔(pèi):衔,指马口之铁,俗称“马嚼子”。辔,指马缰绳。衔辔,于丹法言,乃统领、运行阴阳的主宰。
[7]规矩:规,为画圆之器。矩,为画方之器。
[8]轨辙:谓行车的轨道与辙迹。驾车者执衔辔于上,而车轮行驶之轨、辙自能随合于外。丹法喻指药物在鼎器中烹炼,其升降自有该遵循的法则。轨,为两个车轮之间的距离。辙,为车轮行地之痕迹。
[9]处中以制外:于内丹言,即神居中而御炁,神与炁相抱、不离;或谓炼外药以归身内之鼎炉。外丹以金为君处中,以汞为马处外,汞欲逃逸,金能制之,故说“处中以制外”。或谓鼎在炉中,得外之火、制之;药在鼎中,得外之火、水所制,亦有此义。处,居处之义。中,内丹指人之心与神,或指丹田、“规中”;外丹指居鼎中之“金”。制,治理、统御之义。外,内丹指气或药;外丹指居鼎外之水、火。
[10]数在律历纪:指炼丹之火候,其数理应律吕之十二声、历之十二月、纪之十二年。当然,丹家于此仅为譬喻,非谓修道者必以律吕、历数刻板地计算炼丹火候之数。数,此处指炼丹时,其火候有一定之数理。律,指十二律、吕,其中,阳律有六,即黄钟、太蔟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;阴吕有六,即大吕、夹钟、仲吕、林钟、南吕、应钟。十二律、吕与一年十二月节气相贯通。历,指一年十二月节气之数。纪,谓以十二律、吕与岁历记炼丹火候之数,或谓“纪”乃计年之单位,“一纪”为十二年。
[11]月节有五六:指一月共有三十日,中涵一节、一气,如正月建寅,有立春之节和雨水之气,每个节气共三候,每候共五日,三十日共分为六候。
[12]经纬奉日使:丹道理论以乾鼎、坤炉定南北之位,是为“经”。坎、离药物于鼎炉中烹炼、升降,其妙用有如日、月之东西升降,是为“纬”。奉日使,喻炼丹火候遵循天道运行之法则,其候与天同运、随日升沉,没有差异。
[13]兼并为六十:《易》有六十四卦,除乾、坤、坎、离四卦之外,剩余六十卦。以六十卦与日相配,古代一日共计十二个时辰,每天用两卦直事,一卦六爻,则每一爻值一时,两卦计十二爻,对应一天中的十二时辰。以一月三十日计之,一日两卦,一卦为经、一卦为纬,朝用屯则暮用蒙,朝用需则暮用讼,以至于既济、未济,昼夜各用一卦,一月三十日共得六十卦。其中,乾、坤、坎、离四卦为鼎器、药物,不计入一月昼夜火候之数,故说“兼并为六十”。此句《周易参同契》其他版本亦有作“兼并为六十四卦”者。
[14]刚柔有表里:指配日之卦象,其内外刚柔之体,朝在上则暮在下,刚在表则柔在里,如早晨火候所用之需卦上为坎水、下为乾天,晚上火候所用之讼卦则上为乾天、下为坎水,如此之类。丹道中,刚为阳,柔为阴;刚为金,柔为水;刚为铅,柔为汞;刚为炁,柔为神;刚为命,柔为性;刚为表卫,柔为里卫。阳刚阴柔,水火金木,亦互为表里,故以卦爻象刚柔、表里之变化,喻丹道火候之进火、退符,这也是对“刚柔有表里”的一种理解。
【译文】
乾为纯阳牡卦,坤为纯阴牝卦,坎卦阴中有阳,离卦阳中有阴,坎、离为牝牡相交之卦,合而言之,则乾、坤、坎、离为牝牡四卦,涵盖、总括炼丹中的阴阳变化之道。丹法位乾鼎、坤炉于上下,置坎、离药物于其中,则乾、坤之阖辟,坎、离之往来,俨然如橐籥,枢辖、总括阴阳气出、气入之理。修丹者知此四卦的功能、效用,则可以像工匠准绳墨而正规矩,驾车者执御辔而使车轮运转循于轨辙一样,处其理于中、制其妙于外,从而行无差忒,动合自然,故炼丹进火、退符之火候、法度,皆合于律历之数理。于丹法言,乾鼎、坤炉定南北之位,是为“经”;坎、离药物于鼎炉中烹炼,东西升降,是为“纬”;炼丹火候遵循天道运行之法则,其候与天同运,随日升沉,如月亮奉太阳之“使”一般,没有差异。《易》有六十四卦,除乾、坤、坎、离四卦之外,恰有六十卦;一月三十日,丹家以卦来表征一月中炼丹火候的变化,则一日用两卦:一卦为经,一卦为纬,亦得六十卦。炼丹中,进火为刚,退符为柔,刚柔互为表里,迭相为用;而《周易》卦象亦有内外、刚柔之体,它们交错变化,互为表里,可以用来表征丹道的火候进退之理。
朔旦屯直事章第三
【题解】
本章以一月论炼丹之火候,侧重于月初。每月三十日,周而复始,逐日用功,丹道火候的时刻、早晚,可以用《周易》六十卦喻之,此章即专门论述其月初的凡例。
《周易参同契》论炼丹,凡昼夜、阴阳、升降变化之火数,皆依约《周易》卦爻来表示,朝阴则暮阳,昼动则夜静,昼夜各用一卦直事,如以屯、蒙二卦为首,则朔日朝为屯、暮为蒙,以此为次序,则朝需暮讼,朝师暮比,依次而用,六十卦布于一月三十日内。昼夜十二时,亦恰应两卦十二爻之数。丹道火符有进、有退,有消息盈虚、主客递分。进火之时,不能有些许之谬误;退符之时,亦当防毫发之差错,抽、添须辨药之浮、沉,运用要审时之昏晓。修丹者当因《周易》卦爻象以求其中之深意,得其意则可以忘其象。
自外丹言之,每月初一朔日,以屯值事。屯卦坎在上、震在下,坎是药汞,震有仰盂之象,为鼎,从子至午,器仰,是谓“屯卦直事”。暮用蒙值事,蒙卦艮在上、坎在下,艮有覆碗之象,为器覆,从午至子,转器向下,是谓“蒙卦直事”。故昼屯夜蒙,即是反转鼎器。此后,昼需暮讼,依次而用,阴阳相交,循环不绝。屯为物始生之卦,刚柔始交而难生;蒙为物之稚,阴昧而阳明,阴困童蒙,阳能发之,故屯、蒙两卦皆有阴来就阳之义。丹道中,刚者为金,柔者为流汞,金能用事,汞故求之,阴求于阳,金、汞得水火之气而相交,动转于器中,一仰一覆,然后通达其情,而成丹宝。
自内丹言之,屯卦初九之一阳动于下,有朝之象,代表一阳初生;蒙卦上九之一阳止于上,有暮之象,代表阳之升而至于极。本只是一气周流,终而复始,循环无端,因其有上、有下而分为阴阳,故以屯、蒙两卦示之。或谓坎中一阳,实为生物之本,屯卦坎上、震下,蒙卦艮上、坎下,震为长男,艮为少男,所谓“屯直事”,指震之长男如果能制伏坎中之阳,则可以重施生物之功;所谓“蒙当受”,指艮之少男如果能聚坎中之阳,则可以行温养之功。六十卦阴阳迭互,互施生养,皆涵蕴此理。
朔旦屯直事[1],至暮蒙当受[2]。昼夜各一卦[3],用之依次序[4]。
【注释】
[1]朔旦:朔,指农历每月的初一日。旦,指每天的清晨、平明之时。屯:《周易》次于乾、坤之后的一卦,屯卦上坎、下震。《周易·序卦》说:“屯者,物之始生也。”王弼说:“此卦阴求于阳,弱者不能自济,必依于强。”于丹道言,弱者为流汞,强者为金。金既用事,流汞来顺之;金能应汞,所以铅金与流汞相交。《屯·彖》说:“刚柔始交而难生。动乎险中,大亨贞。”“刚”指金而“柔”指汞,金、汞得水火之气而相交,生成金水而动,轮转于鼎器中,此时防微杜渐,甚有必要;阴阳既交,然后通达其情,而成丹宝,故谓“大亨贞”,即亨通、贞正之意。直事:直,当值,轮值;“直事”谓执行其职责。炼丹之初,阴阳始交,正为屯难、险陷之际,故以屯卦之卦象、义理,指导其事。
[2]暮:指每天的傍晚时分。蒙:指《周易》之蒙卦。蒙卦上艮下坎,屯卦反之,则为蒙卦。《周易·序卦》说:“物生必蒙,故受之以蒙。蒙者蒙也,物之稚也。”《蒙·彖》说:“匪我求童蒙,童蒙求我。”于丹道言,此“我”指阳金,“童蒙”为阴汞,金能用事,汞故求金,阴求于阳,故曰“童蒙求我”。《蒙》九二说:“包蒙,吉。纳妇,吉。子克家。”《象》曰:“子克家。刚柔接也。”阳为男,阴为女,阴合于阳,故云“纳妇”。刚为金,柔为汞,金汞相交,即刚柔相接之义。
[3]昼夜各一卦:指一日十二时辰,昼用屯,则夜用蒙,一日用二卦,一月即用六十卦。
[4]用之依次序:指一日、一月、一年,皆可依次用六十卦以表丹道之火候。其次序为朝屯暮蒙,朝需暮讼,依次而用,故说“依次序”。所谓“次序”,即是依卦据爻,以明用火之数。
【译文】
一月中,炼丹之火候,农历每月的初一日清晨,用屯卦值事;至傍晚时分,则以蒙卦值事。昼、夜十二时,恰应两卦十二爻之数,自此,朝屯暮蒙,朝需暮讼,依次而用,循环往复,终而复始。丹道之进火、退符,抽添、运用,皆要合于此六十卦卦爻所示的法度、数理。
既未至晦爽章第四
【题解】
本章亦以一月论炼丹之火候,但侧重于月末,即专门论述月末所用火候之凡例。
《周易》之卦终于既济、未济。炼丹自每月初一日以屯、蒙而推其火候,至于月末晦日之旦暮,则终于既济、未济;然终则必有始,故次月之初,复自屯、蒙而始。晦朔为一月之始终,早晚谨一日之动静,一月炼丹之火候,必注意于此。
以外丹言之,既济卦上为坎水、下为离火,为水在火上、水火相济之象。汞阴中有阳、属坎,居北方,本为阳而居阴位;朱砂阳中有阴、属离,是太阳精,居南方,本为阴而居阳位。今既济变汞与朱砂之位,使汞之水居南方,朱砂之太阳精居北方,令复其本位,故为“既济”。未济卦上为离火、下为坎水,为火在水上、火水未济之象。丹药中,水银本为朱砂所生、属离,未济火在上、水在下,水银居北、未归于离南之位,未归其本位,故称“未济”。运六十卦火符,始起于屯、蒙,终于既济、未济,月朔至于月晦,一月完成之后,更依前例而起,循环往复。两卦所表征之火符,体现了《周易》一阴一阳之道,此一阴一阳之道,亦可用于炼丹。炼丹时,转动鼎器,阴阳升降,上下反复,周而复始,更互用之,阳动为早,阴静为晚,其日辰之期度,可从日、月运行法度得之。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,一天只行一度有余,故其行迟;月亮绕地球公转一周为一个月的时间,一天约行十三度有余,故其行速。外丹法中,金象日,汞象月,金、汞运转之迟速,取日、月为喻,测其运转之度数,可知日月运转之期候。炼外丹者候此动静,则知丹药凝结之早晚。
以内丹言之,人一身之中,自有日出、日入之早晚,其火候动静,一一暗合天度与卦象之理。如身内一阳来复,则行子时进火之火候;进阳火过程中,阴阳两炁相峙、相停,则行上弦卯时淋浴之火候;阳炁鼎盛,则行月之十五、十六日所代表的午时火候;退阴符过程中,阴阳两炁相峙、相停,则行下弦酉时淋浴之火候;阴阳两炁归藏、沉沦于洞虚,蕴育新一轮阴阳之消长,则行既济、未济之火候。身内炁机消长、火候之动静,皆有其早、晚,不可不察。通过循日、月之期度,察之以卦理,即可得之。然其中卦象内外刚柔之体,或上下卦体相反,或卦爻阴阳相对,皆不能拘泥。若不悟此理,必用天枢、潮候、卦象以准内丹各各不同之用功火候,则为大谬!
既、未至晦爽[1],终则复更始[2]。日辰为期度[3],动静有早晚[4]。
【注释】
[1]既、未:“既”是“既济”,“未”是“未济”,指《周易》最末之既济、未济两卦。自初一以屯、蒙而推之,以至于晦日之旦暮,则终于既济、未济,故“既”、“未”指晦日所用之卦,朝用既济,暮用未济。晦爽:月尽为“晦”,月出为“爽”,晦则昧,爽则明;“晦爽”指月晦之后、即将生明之时,也就是“月朔”。或谓“晦”为月底,“晦”又为暗,“爽”即明;“晦爽”之意,谓月底三十日之清晨与傍晚,其爽明之晨用既济,晦暗之暮则用未济,亦通。
[2]终则复更始:终是月末,为晦;始为月初,为朔;此指一月用火之功结束,次月之初,复自屯、蒙而始。更始:变化、变革后另一个周期的开始。
[3]日辰为期度:日辰,谓一天之十二个时辰。期度,即规则和法度。此处讲炼丹时,进火、退符的时间尺度和法则。以一日之时辰为期度,其动静则分早晚,其阳动而升,渐次生长,从子至午;其阴静而降,渐次敛藏,为自午至亥,务不失其早晚之时,如果火候之进退顺乎其时,则药物于其中变化,亦能恰到好处。一日之期度,即一月乃至一年之期度,因其理相通。
[4]动静有早晚:日出而作为动,日入而息为静,阳属动,阴属静。丹道火候一动、一静,于一日十二辰中,早晚分隔,阴阳升降,火数周而复始,更互用之,自有日出、日入之早晚,与天之运度、卦象之理相合。或谓动静,指水火;早晚,指文、武火候,其意为:炼丹所用之水、火药物,须得文、武火相烹炼,方能凝成至宝。
【译文】
至于月末晦日之旦暮,丹道之火候,则终于既济、未济;然终必有始,故次月之初,复自屯、蒙而始。炼丹时,阴阳升降,上下反复,周而复始;阳动为早,阴静为晚,更互用之。其进火、退符的时间尺度和法则,可取法日、月运转之理;通过取法日、月动静之理,炼丹者可知丹药凝结的早晚之候。
春夏据内体章第五
【题解】
本章言炼丹中一年十二月阳长阴消、阴长阳消的进阳火、退阴符之火候。一日之火候,同于此理。
自十一月建子之月起,至于建巳之四月,此六月,阳长而阴消,乃阴求于阳之时;自五月建午之月起,至于十月建亥之月,此六月,阴长阳消,乃阳求于阴之时。《周易》别卦有内外二体。内卦三爻,法一年之春夏、一日之子后午前;外卦三爻,法一年之秋冬、一日之午后子前;内卦法阳,外卦法阴,故有阴阳交泰之义。炼丹时,一天之火候、十二时辰更替,与一年十二月之气候变化,其理正同。其中,“春夏”以喻“朝”,“秋冬”以喻“暮”;“内体”谓前卦,如屯、既济之类;“外用”谓后卦,如蒙、未济之类。炼丹之进阳火,自子至辰、巳;退阴符,自午至戌、亥,此内外之体,盛衰之理,皆可以《周易》卦爻象则之。
以外丹言之,烹炼时翻转鼎器,皆据子午、前后来反复。其中,阳动则以“朝”为喻,阴静则以“暮”为喻;而“春夏”亦为阳动,“秋冬”亦为阴静。自子至于辰、巳,乃阳动之时,此时火气行,金汞冲融,汞求于金;自午至于戌、亥,乃阴静之时,此时汞气行,则金汞凝结,金求于汞。金居内,汞居外,内外之际,皆取象《周易》卦爻之理。
以内丹言之,阳气自子生而上升,以四时为喻,则为春、夏之季,故说“春、夏据内体”;阴气自午而下降,以四时为喻,则为秋、冬,故说“秋、冬当外用”;子后进火,午后退符,与春、夏养阳,秋、冬养阴,其理一致。如以一日十二时言火候,则朝用屯,喻阳火上升之候,而屯之初九,正当身中之子,由内而外,故说“春、夏据内体,从子到辰、巳”;暮用蒙,阴符下降之候,而蒙之上九,正当身中之午,由外而内,故说“秋、冬当外用,自午讫戌、亥”。其中所说之“春、夏”谓“朝”,“秋、冬”谓“暮”;“内体”谓前卦屯,“外用”谓后卦蒙,故亦有注本以此为论六十卦之火符者。内丹火候所重点关注者,大约为一日之子、午、卯、酉四时,其中,子为进阳火,午为退阴符,卯、酉为淋浴。当然,《周易参同契》所谓春夏秋冬、子午卯酉,寅申巳亥,内体外用之说,皆为譬喻,不能泥象执文。
春、夏据内体[1],从子到辰、巳[2]。秋、冬当外用[3],自午讫戌、亥[4]。
【注释】
[1]春、夏据内体:《周易》别卦皆有六爻,分内外二体。其中,下三爻为内,上三爻为外。内卦三爻,可法一年之春夏、一日之子后午前。亦有观点认为,此处承上两章六十卦火候之说,春、夏喻指“朝”,下句之秋、冬则谓“暮”;“内体”指前卦,下文之“外用”谓后卦,如屯、既济为内体、为朝,蒙、未济为外用、为暮,诸如此类。春、夏两季阳气日盛,乃阴求阳之时。于卦象而言,为内卦或者前卦。
[2]从子到辰、巳:阳火自冬至后十一月建子起,历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,进至四月建巳。此六月,皆阳长阴消,阴求于阳。春、夏两季当养阳,炼丹发火亦从子起,终于辰、巳,阳气于此亦至于鼎盛。到,他本或作“至”。
[3]秋、冬当外用:《周易》别卦之外卦三爻,可法一岁之秋冬、一日之午后子前。秋、冬两季阴气盛,乃阳求于阴之时,于卦象而言,为外卦或者后卦。
[4]自午讫戌、亥:阴符从五月夏至建午起,历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,至十月建亥。此六月,阴长阳消,阳求于阴。秋、冬两季当养阴,炼丹退阴符从午起,阴生于午,而终于亥,于亥之时,阴气亦至于鼎盛。
【译文】
丹道强调春、夏养阳,秋、冬养阴;子后进火,午后退符。一年之春、夏两季,一日之子后午前,皆阳长阴消、阴求于阳之时,故以《周易》内卦或前卦喻阳火上升之候。一岁之秋、冬,一日之午后子前,皆阴长阳消、阳求于阴之时,故以《周易》外卦或后卦喻阴符下降之候。一天十二时以应一年十二月气候,从子至于辰、巳,自午讫于戌、亥,其阴阳升降、盛衰之理,内体外用之说,皆可以《周易》卦爻象则之。
赏罚应春秋章第六
【题解】
本章言炼丹之刑德沐浴火候。与前章所说“从子到辰、巳”,“自午讫戌、亥”,为定冬至阳长、夏至阴长之“二至”阴阳进火、退符火候不同;此章所说“赏罚应春秋”,“爻辞有仁义”,则为定春分、秋分二分之刑德沐浴火候。
修金液还丹,若非取法天地造化自然之法则,则无以为成。在《易》言之,天道有阴阳,地道有刚柔,人道有仁义。天道中,阳至于春则发生,阴至于秋则肃杀。人道法天之道,当阳之发生,则施仁以赏;值阴之肃杀,则行义以罚。赏为阳,罚为阴;仁为阳,义为阴;喜为阳,怒为阴。朝则行阳以应春夏,暮则行阴以应秋冬。如此顺应四时之气,自然得五行之理。
自外丹言之,炼丹有文、武火候,如加炭为武火,灭炭为文火。炼丹火候应顺四时、五行,不违天道。如春生万物,犹天之行赏,炼丹时,火气行则金汞冲融,亦可以“春”为喻;秋杀百草,犹天之行罚,炼丹时,水气行而金汞凝结,亦可以“秋”为喻。一日昼夜所用之火候,与一年寒暑之功不相违背。《周易》卦爻六画之内有阴、阳,阳则生物,故称“仁”;阴则成物,故称“义”;在阳则舒,故喜;在阴则敛,故怒。炼丹时,金得水气则喜,汞得火气则怒。外丹金水受气成形,其理亦如此。通过顺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时之气,依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之用,则金、汞不失其宜。合大丹、大药,伏制成败在火;火若均调,文武得所,药则无失;火若不顺,药虽精华,即有飞散。
自内丹言之,修真之士动静语默之间,须谨慎从事。春属木,于此时当体春之阳气发生,于自身阳气大壮之时,运转河车、飞金精直上昆仑峰顶;金精于五行之性属坎之水,水能生木,故有施仁之义。秋属金,于此时体秋阴气之肃杀,于自身阴气正盛之时,而采药归炉;离宫之药于五行之性属火,火能制金,乃讨叛之义。自身内阴阳二气之潜藏飞跃、进退加减,各随其时,如是顺四时之气,五行皆得其理。或谓丹为至阳之精,若有纤毫阴气煅炼未尽,终不能有所成就。至如人好生利物、仁慈宽恕、惠爱忠信、和喜清静、真实不妄之类,皆为阳;好杀害物、残忍嫉忿、贪悭凌侮、骄傲狠愎、淫昏、虚诈不实之类,皆为阴,修行人戒阴修阳,阴将自亡;阴尽阳纯,自然成真。
赏罚应春秋[1],昏明顺寒暑[2]。爻辞有仁义[3],随时发喜怒[4]。如是应四时[5],五行得其理[6]。
【注释】
[1]赏罚:阳至于春则发生,春生万物,如天之行赏;阴至于秋则肃杀,秋气杀百草,如天之行罚,故赏为阳,罚为阴。应春秋:修炼之士于阳气壮大之时,体春阳生生之意,保阳、护阳,施仁以爱之;于阴气正盛之时,体秋阴之肃杀,以火制金,有讨叛之义。故象阳之发生,而施仁以为赏;象阴之肃杀,则行义以为罚。
[2]昏明:“昏”即暮,“明”即朝。顺寒暑:寒暑立晷而占日影,以知气候变化之理,昏明寒暑,人当顺其时,方可不违天道。详见《汉书·天文志》。丹道一日之火候,其理与一年之火候同,朝则行阳火以应春夏,暮则行阴符以应秋冬。虽一日昼夜所用,而不违一年寒暑之候。
[3]爻辞:狭义之爻辞,指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之爻辞;广义之爻辞,指《周易》经、传之语。仁义:为儒家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,“仁”有“爱”之义,“义”有“宜”之义。亦有以“仁义”作“阴阳”解者,认为一卦六爻之内有阴、阳,阳则生物,故称“仁”;阴则成物,故称“义”,此合于易学理论的“三才”(或“三材”)之说,即所谓天道有阴阳,地道有柔刚,人道有仁义。《周易·系辞》谓:“《易》之为书也,广大悉备,有天道焉,有人道焉,有地道焉,兼三才而两之,故六。六者非它也,三才之道也。”《周易·说卦》亦谓:“立天之道曰阴与阳,立地之道曰柔与刚,立人之道曰仁与义,兼三才而两之。”
[4]随时:春、夏阳长阴消,秋、冬阴长阳消;自子至于辰、巳,为阳火之候。自午讫于戌、亥,为阴符之候。顺应四时阴阳消长变化之节律,是谓“随时”。喜怒:喜为阳,怒为阴。在丹道中,为文、武火候;于十二辰中,运其火符,昏明寒暑,仁义喜怒,爻象不得纤毫参差,此谓“随时发喜怒”。
[5]四时:指一年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。春温、夏热、秋凉、冬寒,四时各有其气候。
[6]五行: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。其中,春木、夏火、土旺四季、秋金、冬水,五行有其次序。丹法中,还将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“五行”配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“五常”,具体为木主仁,火主礼,金主义,水主智,土主信。
【译文】
春生万物,犹天之行赏;秋杀百草,犹天之行罚。炼丹时,鼎炉中阴阳之气潜藏飞跃、进退加减,皆随春生、秋杀之理;其一日昼夜所用之火候,与一年寒暑变化之理亦不相违背。《周易》卦爻六画之内有阴与阳,阳则生物,故称“仁”;阴则成物,故称“义”;在阳则舒,故喜,在阴则敛,故怒。炼丹时,亦有阳文、阴武火候之不同,其与《周易》卦爻辞阴阳、喜怒、生杀之理不异。修炼之士通过顺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时之气,依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之用,则丹道火候方可不失其宜。
天地设位章第七
【题解】
本章论坎、离之中爻在丹道中的作用。丹道以乾坤为神室、列阴阳配合之位,使坎、离交于其中,以成变化之功,坎中之阳、离中之阴相互交感,化生万物,而为道之纲纪。
自外丹言之,乾为天,是谓上鼎;坤为地,乃谓下炉。“设位”指鼎炉作雄雌相合,也指丹药在鼎炉中阴阳相合,或谓“设位”指鼎炉之上排列有方位、星辰、度数,以定运火之时间与刻度,故“设位”有阴阳配合之意。坎为月,可喻铅金;离为日,可喻流汞,故经文中之坎、离主要喻指丹药;“易”字上日下月,总喻丹药。铅、汞丹药居乾鼎、坤炉之内,就是经文所谓“天地设位”,“易行乎其中”之意。坎、离为药,乾、坤为鼎,坎、离二药在乾、坤鼎炉中,常被水火攻迫,运转飞伏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上、下六位,故有“二用”、“六虚”之说,喻指铅金、流汞得水、火烹炼,发生变化之义。水、火之气相蒸,金、汞之形常转,自然往来不定,上下无常。外丹用土、金花等为泥筑成鼎炉,包囊铅金、流汞,将之纳于其中,铅金潜匿于流汞中,流汞得铅金而沦没,二物相伏隐于鼎中,故“幽潜沦匿”;丹药为水、火烹炼,得文、武火迫,龙虎相吞,乃无常位而成大还丹,此谓“道之纪纲”。
自内丹言之,乾为天,坤为地,指明人身之鼎器;离为日,坎为月,指出修丹之药物。天道与人道相通,天地之阴阳相交,化生万物,变易无穷;人身之坎、离药物,运行于乾、坤丹田、鼎器之内,亦变化而无常位。金丹之母,不过先天一炁,此先天一炁裂而为阴阳,阳至于极则阴生,以离卦之中爻喻之;阴至于极而阳生,以坎卦之中爻喻之;离中之阴乃乾之用,坎中之阳乃坤之用,坎、离运乾、坤之阴阳,周流于六虚之内,实喻指修炼之人神入炁中、炁入脐中,神与炁相抱,时至则炁自化,静极则机自发。虚中生炁,为至阳之炁,至阳之中,藏肃肃之至阴,无中含有,为乾中之离;炁中凝精,为至阴之精,至阴之中,藏赫赫之至阳,有中含无,为坎中之阳。离阴、坎阳或上或下,或往或来,不可以为典要,而包囊万物,为道之纲纪。
天地设位[1],而易行乎其中矣[2]。天地者,乾坤之象也;设位者,列阴阳配合之位也[3]。易谓坎离[4]。坎离者,乾坤二用;二用无爻位,周流行六虚[5]。往来既不定,上下亦无常[6];幽潜沦匿,变化于中[7];包囊万物,为道纪纲[8]。
【注释】
[1]天地设位:乾为天,坤为地,喻指丹道中之鼎器。设位,指天尊、地卑,一高一低。此说源于《周易·系辞》:“天尊地卑,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陈,贵贱位矣。”
[2]易行乎其中:天地既立,变易乃生;天阳而地阴,阴阳气交则万物化生,即所谓“变易”。乾坤相交,乾之一爻,入于坤腹,实而成坎;坤之一爻,入于乾体,虚而成离;坎为月,离为日,天地之间,日、月升降,成四时、昼夜之更迭,此则为“易”。于丹道言,则鼎器法乾天、坤地,复于鼎器中,置坎、离药物,药物在鼎器中,得阴阳符火煅炼而变化成丹,故说“天地设位,而易行乎其中矣”。《周易参同契》于此引用《周易·系辞》原文:“天地设位,而易行乎其中矣。”以论坎、离之中爻在丹道中的作用。
[3]天地者,乾坤之象也;设位者,列阴阳配合之位也:《周易·说卦》:“乾为天”、“坤为地”。乾天在上,坤地在下,阴阳二气则运行于其中,一升一降,往来不穷。炼丹以乾、坤为神室,于其中列阴阳配合之位,使坎、离药物交于其中,以成变化之功。阴阳之气相互作用,阴禀而阳受,谓之“配合”。
[4]易谓坎离:离中之阴,乃坤卦中正之阴;坎中之阳,乃乾卦中正之阳。乾、坤为体,坎、离为用,坎离具乾坤中正之德,代乾坤施为,犹如天地无为,日月变化。离为日,坎为月,上日下月组合成“易”字。日、月升降往来,成天地间之变易;于丹道中,坎、离为药物,成丹道之变易。
[5]坎离者,乾坤二用;二用无爻位,周流行六虚:坎、离独得乾坤之中气,故坎、离中爻乃乾坤之妙用,其进退升降于六爻,往来上下而无常位,即谓之“二用”。此说出于《周易·系辞》:“若夫杂物撰德,辩是与非,则非其中爻不备。”或谓坎、离为药物,乾、坤为鼎炉,故此四卦不同六十卦,自有其用,此为“一用”;铅、汞居鼎内,须水火伏制而成大丹,水火上下煅炼乾、坤之鼎炉,此为“二用”。还有以乾之用九、坤之用六为乾、坤“二用”之说,认为乾、坤二卦六爻中九、六各有定位,唯用九、用六无定位,二用虽无爻位,而常周流于乾、坤六爻之间,六爻之九、六,即此用九、用六之周流升降。汉易纳甲之法,乾纳甲、壬,坤纳乙、癸,震纳庚,巽纳辛,艮纳丙,兑纳丁,皆有定位;而坎纳戊,离纳己,则无定位。此六卦之阴阳,即坎、离中爻之周流升降而成。东西南北上下,谓之“六虚”;“周流六虚”,变化之义。或谓“六虚”,即乾、坤之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六爻位。《周易参同契》以此喻人之精炁,上下周流于一身而无定所。此说源于《周易·系辞》:“《易》之为书也不可远,为道也屡迁,变动不居,周流六虚;上下无常,刚柔相易,不可为典要,唯变所适。”
[6]往来既不定,上下亦无常:炼丹之时,水火之气相蒸,金水之形常转,自然往来不定,上下无常。
[7]幽潜沦匿,变化于中:阴阳二气相互作用,或隐或显,或用或潜,水得火而升腾,金居水而潜匿,递相变化,凝结器中。
[8]包囊万物,为道纪纲:包囊万物,指天地包涵、收藏万物。为道纪纲,指阴阳,其中纪为阴,纲为阳。阴阳二气交感,化生万物,万物皆自此中来,故为“道之纪纲”。丹道中,包囊金水药物、使之变化万端者,为鼎器;水火相互作用于鼎器,此谓“纪纲”。
【译文】
天尊而地卑,天地既定,阴阳交媾于其中,化生万物,变易无穷。天地为乾坤之象,天阳而地阴,阴阳二气相互作用、阴禀阳受,运行于天地之间,一升一降。离为日,坎为月,上日下月组合成“易”字,日、月升降往来,成天地间之变易;坎、离药物相互作用,成丹道之变易。乾为纯阳,坤为纯阴,纯阳至于极则阴生,以离卦之中爻喻之;纯阴至于极则阳生,以坎卦之中爻喻之;离中之阴乃乾之用,坎中之阳乃坤之用,坎、离运乾、坤之阴阳,周流于一卦六爻之位,比喻阴阳之气运转于东西南北上下六虚之内。天地间阴阳二气递相变化,往来不定,上下无常;或隐或显,或用或潜,交感化生万物;万物皆自此中来,故其能包囊万物,而为道之纪纲。
以无制有章第八
【题解】
本章论坎、离交媾之妙用。离中之虚为“无”,坎中之实为“有”,以离中之阴爻化为坎之中画,变成纯阳乾卦,此谓“以无制有,器用者空”。坎、离中爻,周流升降,而成六十卦,故阴阳有消、有息;“没亡”谓坎、离两卦不计入丹道火候之数。
外丹所谓“无”,常喻指流汞,为阳之气,即丹经一般所说的“龙”;“有”常指铅金,乃阴之质,即丹经一般所说的“虎”。或谓金汞之质为“有”,水火之气为“无”,水火之气相交,金汞、龙虎自合。“消息”指阴阳升降,消时灭炭,息时加炭;升时器向上,降时器向下。坎为铅金,离为流汞,流汞得铅金之华相配,变化成丹,故有“没亡”之说。
内丹以太虚为鼎炉,而太虚清静无为之中自有天然妙用,此太虚清静即为“无”,天然妙用即为“有”,以无制有,即指明“清虚”、“无为”、“自然”在内丹修持中的功用。或谓修丹者以性火真空制命水至宝,性火真空为“无”,命水至宝谓“有”,以“无”可以制“有”。另有谓“有”指万物,“无”指一阳之气;“有”为人之魄,“无”乃人之魂之说,皆譬喻之言。
以无制有,器用者空[1]。故推消息[2],坎离没亡[3]。
【注释】
[1]以无制有,器用者空:丹道以“无”为神、为汞、为离、为性、为火、为龙、为一阳之气、为真空、为魂;以“有”为气、为铅、为坎、为命、为水、为虎、为万物、为妙有、为魄,如此等等。如大车之轮、陶器、房室皆实有其功用之利,而其所以有车、器、室之功用,皆有赖于虚其中。如毂虚其中,故可以行车;陶器虚而圆,故可以成器皿之用;屋内空阔,故有室之用。器虽有形,而其用乃在其形之空处。《周易参同契》所谓“以无制有,器用者空”,实用老子之说,以明丹道中“存无守有”之功。《道德经》谓:“三十辐共一毂,当其无,有车之用。埏埴以为器,当其无,有器之用。凿户牖以为室,当其无,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为利,无之以为用。”(十一章)汉易纳甲之法:乾纳甲、壬,坤纳乙、癸,震纳庚,巽纳辛,艮纳丙,兑纳丁,皆有定位;而坎纳戊,离纳己,则无定位。《周易参同契》认为,表征月相的震、兑、乾、巽、艮、坤六卦之阴阳,即由坎、离中爻周流升降而成。以坎、离之无位,制六卦之有位。或谓离虚为无,坎实为有,离虚能受坎实,离中之阴爻化为坎之中画,则变成纯乾,丹道以取坎填离、成纯阳之体为其理想之追求。
[2]消息:消,指自乾卦三阳为起点,为阳消而阴息的过程。这个过程经历巽卦之一阴长,艮卦之二阴长,而极于坤卦之三阴。息,指自坤卦三阴为起点,为阳息而阴消的过程。这个过程经历震卦之一阳长,兑卦之二阳长,而极于乾卦之三阳。因此,所谓“消”,为退阴符之候,由乾之三阳,三变而成坤之三阴;所谓“息”,为进阳火之候,由坤之三阴,三变而成乾之三阳。
[3]坎离没亡:指坎、离无位之意。以一月言之,自每月初之朔旦,一阳生起,为震卦用事;此后历兑卦二阳生,至乾卦三阳,此为阳息长的过程。十五月望之后,一阴生起,巽卦用事;此后历艮卦之二阴生,至坤卦之三阴,此为阳消的过程。其间,不论坎、离之爻位,此之谓“坎离没亡”。或谓坎、离非“没亡”,因坎、离行于六虚之间,往来不定,没有固定的位置,亦可称“没亡”。或谓“消息”为“有”,“没亡”为“无”。
【译文】
离虚为无,坎实为有,以此之无,制彼之有;器以空为用。离虚能受坎实,离中之阴爻与坎中之阳爻相互作用,阴生阳退,阳起阴潜,一消一息,故有消息变化;坎、离交媾,变成纯乾,失其坎、离之体,故说“坎离没亡”。
言不苟造章第九
【题解】
本章明坎、离药物所涵蕴的阴阳土德之功。
自外丹言之,日月为金水之验,阴阳为神明之度。欲知金水之会合,但候日月之运移。日月相推之谓变,阴阳不测之谓神。日下置月成“易”字,丹道之理,皆据《周易》爻象运火,取其法则,合其同类,有其征候、效验。坎为水,离为火,水火之气,熏蒸金汞之形,凝结成丹。其中,铅精象月,为坎,属戊;汞光象日,为离,属己。土无正形,常旺四季,即于炉之四面,以土终始而为罗络,是为土鼎;若是用金、铁之鼎,即用黄土涂鼎内,因土能生金;或黄土涂鼎内后,上又用黄土镇之,则鼎内汞、金相配,日久火养自化成丹。之所以要以土为鼎、或以土涂鼎,因为五行之理,土能制水。或谓青是东方木,为青龙之汞;赤是南方火,即朱砂;白是西方金,即金精;黑是北方水,即铅;鼎为戊己中宫。药虽各居一方,但皆入鼎中烹炼,是谓“皆禀中宫,戊己之功”。
自内丹言之,坎外阴而内阳,月之象;离外阳而内阴,日之象;坎纳戊,离纳己,二土交合,则阴阳相济,刚柔相当。青、赤、白、黑,即木、火、金、水;木、火、金、水,各居一方,非得真土调和,则各自阴阳否隔、刚柔离分,不能成丹。土居中央,罗络四方,木得之以旺,火得之以息,金得之以生,水得之以止,四者皆禀土之功。然此土,于内丹究竟所指为何?北宋张伯端《悟真篇》说“东三南二同成五,北一西将四共之;戊己自居生数五,三家相见结婴儿”,“土”乃清静、自然之真意,于此杳冥中便有精、恍惚中便有物,故“东三南二”、“北一西四”,皆赖此戊己真土,得以调和水火,融会金木,从而五行、四象皆攒簇于中黄,结成大丹。
言不苟造,论不虚生[1]。引验见效,校度神明[2]。推类结字,原理为证[3]。坎戊月精,离己日光。日月为“易”,刚柔相当[4]。土旺四季,罗络始终[5]。青赤白黑,各居一方;皆禀中宫,戊己之功[6]。
【注释】
[1]言不苟造,论不虚生:《周易参同契》依大《易》、黄老之旨,以极天地阴阳之变化,论还丹炉火之功,留法传文,其中涵蕴至理,非师心自用,虚生此文,以惑乱后世。苟造,即无端编造。苟,苟且。造,造作,创作。虚生,凭空想象,不是事实。
[2]引验见效,校度神明:丹道据《周易》卦爻之象运火,皆有其效验;修丹者效日月、阴阳运行之法则,而成大还丹,如与神明相通。引验见效,指有事实、经验、功效作验证,并非虚语。校,核准之意。度,计量。
[3]推类结字,原理为证:此论造字之法,篆书上离日、下坎月,日下置月,相合为“易”字。推类结字,指古人造字,合日、月为“易”。原理为证,推原《易》卦之道理,以为丹道之符证。
[4]坎戊月精,离己日光。日月为“易”,刚柔相当:汉易纳甲之法,以坎纳戊、离纳己,因坎为中男、离为中女,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十天干中,戊、己居中,故配坎之中男、离之中女。坎外阴而内阳,月之象;离外阳而内阴,日之象。戊为阳土,己为阴土,坎月阴中藏戊阳之土,乃阴中有阳,象水中生金虎;离日阳中藏己阴之土,乃阳中有阴,象火中生汞龙;二土交合,则阴阳互补,刚柔相济,犹日月两字合之而成“易”字;“易”不外乎日月,丹道亦本于坎、离。东汉易学家虞翻曾语及“日月为易”,有观点认为虞翻之说实本于《周易参同契》。
[5]土旺四季,罗络始终:土旺四季,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之中,木旺春季,火旺夏季,金旺秋季,水旺冬季,土无正位,分旺于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中,后世有土于四季各旺十八天的说法,这就是“土旺四季”之说。土气贯通于一年之终始,而起到罗络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的作用。罗络,联系、贯通、包含之义。《道藏》彭晓注作“土王四季”。
[6]青赤白黑,各居一方;皆禀中宫,戊己之功:青、赤、白、黑,木之色青,火之色赤,金之色白,水之色黑。木代表春,居东方;火代表夏,居南方;金代表秋,居西方;水代表冬,居北方;木、火、金、水各居一方,唯土居中央,分旺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,罗络一岁之始终。且木得土而旺,火得土以息,金得土以生,水得土以止;木、火、金、水四者皆禀土之功。坎戊离己,皆居中宫土位;而四方四行,皆禀土气。北宋张伯端《悟真篇》说:“四象五行全藉土。”又说:“只缘彼此怀真土,遂使金丹有返还。”皆阐明《周易参同契》此义。
【译文】
《周易参同契》留法传文,不苟造虚言。其所论丹道之理,皆据《周易》卦爻之象,效日月、阴阳运行之法,有其征验,犹如与神明相通。日、月两字合之而成“易”,“易”不外乎日月,丹道亦本于坎、离;故推原《易》卦之理,以其为丹道之符证。汉易纳甲之法,坎纳戊,离纳己;坎外阴而内阳,月之象;离外阳而内阴,日之象;坎、离交合,则阴阳互补,刚柔相济。戊、己皆为土,土无正位,分旺于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,故土之气贯通于一年之终始,而起到罗络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的作用。其中,木代表春,居东方,色青;火代表夏,居南方,色赤;金代表秋,居西方,色白;水代表冬,居北方,色黑。青、赤、白、黑各居一方,唯土居中央,木得土而旺,火得土以息,金得土以生,水得土以止,木、火、金、水四者皆因禀受中央土气,而得以成其功用。
易者象也章第十
【题解】
本章论丹道进火交媾之法。炼丹鼎室中,乃自是一天地,观天地日月合璧之象,而得丹道坎、离交媾之道:阴阳二物在神室中,混沌相承,如日月相交;震来受符,一阳来复,树立根基,长养、谨护以至凝神成躯,终成至宝。
自外丹言之,日月为水火之精,铅金、汞银为变化之源。铅金、汞银非水火不成,水火之气争凑于鼎器之中,熏蒸铅金、汞银之形,如车辐之辏毂;水气入,则火气卷;火气入,则水气舒,卷舒不离于鼎器,如车轮之常转。一卦六爻,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,以当丹药三百八十四铢一斤之数。水火震动之时,铅金、汞银结其精炁,如天气下降,地气上腾,日月相交,阴阳媾会,金、汞俱吐精华。雄阳乾父属天、色玄,雌阴坤母属地、色黄,乾、坤互施阴阳,交媾水火而成丹;雄阳又为武中之武,雌阴又为阴中之阴,文、武之火气既施,铅金、汞银之姿于鼎中潜转,一寒一暑,变成黄色之芽。铅金、汞银于鼎器中混沌未分之时,虽未变易,终为还丹之本;金、汞得火煅炼,先液后凝,合为一体则为神丹。《周易·系辞》说:“天地媾精,万物化生。”含灵之属俱在天地之中,皆禀阴阳而生;丹道亦然。
自内丹言之,天地之间,唯有日、月之象最为显然著明,故以其象示人,使人能洞见天地阴阳之道,而默识其神化之妙。人一身之中,自有日、月,与天地无异。修持之人既穷其神而知其化,使阴阳迭相往来,并取大《易》爻象而为节符,视日月昏明而行火候,自然夺天地之机,盗造化之妙。故丹法之生药与天地之生物同理,皆为阴阳二气一施一化而玄黄相交。晦朔之间,震来受符,乾交于坤而成震,此时身中一阳生起,人之神与炁交,炁与神合,有如天地之媾精,日月之合璧;“雄阳播玄施”为天气降而至于地,“雌阴化黄包”为地承天气而生物,阴阳二气上下交接,混而为一,即为“混沌”。混沌乃天地之郛郭、万物之胞胎,丹法以之为始而树立根基,修持之人经营于此而回光内照,则神恋炁而凝,炁恋神而住,自然交结成胎。阴阳交接之道乃宇宙生化之源,施之于人则生人,施之于物则生物,存之于己则产药,故产此一点于外,则为生生不穷之大化流行;产此一点于内,则为返本还元、成仙超脱之道。
《易》者,象也;悬象著明,莫大乎日月[1]。穷神以知化,阳往则阴来;辐辏而轮转,出入更卷舒[2]。《易》有三百八十四爻,据爻摘符,符谓六十四卦[3]。晦至朔旦,震来受符[4]。当斯之际,天地媾其精,日月相撢持[5]。雄阳播玄施,雌阴化黄包[6]。混沌相交接,权舆树根基[7]。经营养鄞鄂,凝神以成躯[8]。众夫蹈以出,蠕动莫不由[9]。
【注释】
[1]《易》者,象也;悬象著明,莫大乎日月:《周易参同契》认为,我们仰观、俯察天地之间,唯有日、月之象最为著明,故以日、月之象以明天地阴阳运化之机。当然,由此也可以进一步默识人自身之中的阴阳神化之妙。此句源出于《周易·系辞》:“是故《易》者,象也。象也者,像也。”“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,变通莫大乎四时,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。”《周易》与其他经典的相异之处,在于它除了以字、辞阐明道理之外,还以卦爻之象数来表征事物之情状。前文论及“日月为‘易’”,即以日、月相合而成“易”字,天地间最著名的物象就是日、月,丹道常以日、月喻流汞、铅银,炼丹所用七十二石之中,无过于汞、铅,故汞、铅得称日、月之号。
[2]穷神以知化,阳往则阴来;辐辏(fú còu)而轮转,出入更卷舒:能穷阴阳之道,则知变化之源。金液还丹合日月、阴阳精炁而成,故阴阳精炁一出一入,迭为上下,昼夜循环,出入卷舒,犹如车轮之运转。阳往则阴来,指阴阳迭为消长。以《周易》卦气言之,自十月坤卦纯阴,至十一月复卦一阳生,历十二月临卦二阳、正月泰卦三阳、二月大壮卦四阳、三月夬卦五阳,终于四月乾卦六爻纯阳,此为阳长阴消。乾卦之后,则阳往阴来,故五月姤卦一阴生,六月遁卦二阴长,七月否卦三阴、八月观卦四阴、九月剥卦五阴,至于十月坤卦六爻纯阴。丹道通过《周易》卦气变化,喻指炼丹时火候之加减;丹道运火转动鼎器,阳往则阴来,犹如辐之辏毂轮转不停。其中,“神”为事物变化之因;“化”为事物变化之趋势;“来”为伸,“往”为屈;“辐”为车轮之辐条,“辐辏”为车轮聚辐的方式。经文源出于《周易·系辞》: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、“阴阳不测之谓神”、“神以知来,知以藏往”、“知变化之道者,其知神之所为乎”、“穷神知化,德之盛也”。“日往则月来,月往则日来,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寒往则暑来,暑往则寒来,寒暑相推而岁成焉。往者屈也,来者信也,屈信相感而利生焉”。《道藏》彭晓注“辐辏”作“辐凑”。
[3]《易》有三百八十四爻,据爻摘符,符谓六十四卦:《周易》六十四卦,每卦六爻,共计三百八十四爻;丹道中,一斤大药计三百八十四铢。丹道与《易》道相通,故可据《周易》爻象阴阳升降之理,摘卦为符,视符而行火候。故以《易》言之则为卦,以丹道言之则谓符。“符”即爻画,或谓“爻”指卦之画,“符”指卦之合体,亦通。一说谓“一卦有六爻,一爻有三符”。
[4]晦至朔旦,震来受符:晦至朔旦,指一月的晦、朔之间,晦为月底,朔为月初。震来受符,月晦终于坤之纯阴,月朔则乾交坤一爻为震,震一阳伏于二阴之下。月晦时,纯阴坤卦执行其职责,朔旦则由震卦执行其职责,动而兴阳,如符如印,有其信验。符,信验。
[5]当斯之际,天地媾其精,日月相撢(tàn)持:月晦纯阴坤卦执行其职责后,朔旦则由震卦来执行其职责。当震卦受符、应命之时,天气下降,地气上腾,日月相交,阴阳媾会。丹道之理,与“天地媾精,万物化生”之理相同,皆禀阴阳而生。其中,“天地”指炼丹之乾坤鼎器,“日月”为坎离药物,“精”为药之精华,“撢持”有探索、接触、牵引的意思;或谓“撢”与“探”同,为自远处而取之义,犹如日、月相距虽远,然日、月能相感而生明、生蚀,经文意指坎离药物在鼎器之间得火而化,二药交媾精炁,相探扶持成丹。此段经文源出于《周易·系辞》:“天地缊,万物化醇;男女媾精,万物化生。”
[6]雄阳播玄施,雌阴化黄包:雄阳播玄施,指天气降而至于地;雌阴化黄包,指地承天气而生物。丹法之生药与天地之生物相似,皆为阴阳二气一施一化,而玄、黄相交。《周易·文言》:“夫玄黄者,天地之杂色也。天玄而地黄。”天之气,其色为玄;地之气,其色为黄。雄为阳而雌为阴,“玄施”为玄妙之施,即丹道所谓“妙合而凝”、不可图画者;“黄包”为黄中之包裹,即丹道所谓“黄芽”、“黄舆”,乃元阳之炁。“播玄施”、“化黄包”即是阴阳相交之意。或谓雄阳为坎,“播玄施”指进阳火,初变为震,次为兑,以至于为乾,乾为天,其色玄;雌阴为离,“化黄包”指退阴符,初变为巽,次为艮,以至于坤,坤为地,其色黄。雌阴化黄包,一本作“雌阴统黄化”。
[7]混沌相交接,权舆树根基:天地阴阳二气上下交接,混而为一;当其混沌之时,阴阳相互交接,成为万化之根本。故天地未分,谓之混沌,混沌乃天地之郛郭,万物之胞胎。丹法以乾坤为鼎器、神室,混沌象坎离药物相合,混而不分,融为一体之状。权舆树根基,谓阴阳肇始、建立根基之义。权舆,万物始生之义。据说度量衡中,衡始于权;车舆,亦是车始于舆,故权舆有“始”之义,如《秦风》“不承权舆”,即有不继其始之义。树,树立、建立之义。
[8]经营养鄞(yín)鄂,凝神以成躯:经营养鄞鄂,是说阴阳之气经营度旋,以培养、护育其胚胎、址基。丹法于此强调回光内照,则自然神恋炁而凝,炁恋神而住,寂然自成其丹之躯。经营,有运作、往来之义,其中,纵横度量谓之“经”,往复回旋谓之“营”。鄞鄂,鄞,犹“垠”,界限的意思;鄂,犹“萼”,根蒂之义;鄞鄂,即根蒂、胚胎、界址、边际。一说“鄞鄂”为地名,“鄞”在浙江会稽,居东;“鄂”在湖北,古为荆楚之地,居西,故“鄞鄂”以喻址基。
[9]众夫蹈以出,蠕动莫不由:阴阳交接之道,乃生生化化之源,不特人与禽兽,凡大而天地,细而蠕动,有形有气之物,俱在天地之中,任阴阳二气相陶铸,莫不由此而出。众夫,“人民”之指称。蠕动,含灵之属、有生命特征的一切存在。
【译文】
《周易》以卦爻之象来表征事物之情状;天地之间唯有日、月之象最为显著,故以其象示人,使人能洞见天地阴阳之道,而默识其神化之妙。修持之人既穷其神而知其化,使阴阳迭相往来,出入卷舒,如车轮之运转。并取大《易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为节符,视日月昏明而行火候,自然夺天地之机、盗造化之妙;例如,从月底至于月初之时,当以《周易》震卦执行其职责。此时,丹鼎之中一阳生起,阴阳气交,有如天地之构精,日月之合璧。其中,雄阳乾父属天、色玄,雌阴坤母属地、色黄,乾、坤互施阴阳,乾交于坤成震,表示天气降而至于地、地承天气而生物。故丹法之理与天地生物之道同,皆为阴阳二气一施一化而玄黄相交。阴阳二气上下交接,混而为一,即为“混沌”,混沌乃天地之郛郭、万物之胞胎,丹法从此开始,树立起根基。修丹者经营、长养、谨护丹之根本,自能使之交结成胎。阴阳交接之道乃宇宙生化之源,人与其他蠕动、含灵之属,皆禀阴阳之道而生。丹道亦同此理。
于是仲尼章第十一
【题解】
本章以言丹道火候之发端,明丹道用功之始,于混沌、洞虚之中,阴阳相求,精炁相扭,从而产药、结成丹头。
孔子序经,《易》首乾、坤;《书》称“稽古”;《诗》以《关雎》为先;《礼》以“冠婚”为重;《春秋》以“元年”为第一义,皆发明男女媾精、万物化生之道,以明阴阳相求之义。炼丹之始,亦要洞晓阴阳,深达造化,才能默会天机,与时消息,建立丹基。
自外丹言之,铅金为男,流汞为女,得火即相合和,扭结如同夫妻;金既先动,汞乃应之,即是男求女之义。冠、婚之时,男女交会,精炁扭结,金、汞相感,亦如此理。《关雎》雌雄相配之义,喻汞得金花相和顺,丹不得阴阳不成,金、汞二味成丹,正合阴阳之道。阴阳交媾,因肇立形,萌芽乃生,是雌雄相配成丹;若无雌雄,无以成丹。
自内丹言之,乾坤未分谓之“鸿濛”,阴阳相扭谓之“始初”。修内丹者,端坐守静,初则全无形质,一如鸿濛、混沌;于虚无恍惚之中,自然阴阳精炁相扭。此时,元阳震动,萌芽滋长,节节起火运符,炼至宝于虚无,取灵物于恍惚,如《关雎》之诗、冠婚之义。
于是,仲尼赞鸿濛,乾坤德洞虚[1];稽古当元皇,《关雎》建始初[2],昏冠气相纽,元年乃牙滋[3]。
【注释】
[1]仲尼赞鸿濛,乾坤德洞虚:孔子赞《易》道,辟之鸿濛,凿之混沌,分乾天、坤地为万物之首,立咸、恒为夫妇之宗,彰显《易》道之玄妙,明乾坤、阴阳之德,以通天地万物和人之情。仲尼,孔子之字。赞,赞颂,称美。鸿濛,混沌之名,乾天、坤地未分则为“鸿濛”;一说“鸿濛”为始初之气;或谓形气未具之时为“鸿濛”,形气具而未离则为“混沌”。乾坤,喻指阴阳,《周易》以乾、坤两卦为首。德,通“得”。洞虚,形气未具之状,空洞至虚。赞,他本或作“始”。鸿濛,他本或作“鸿蒙”、“洪蒙”。德,他本或作“得”。
[2]稽古当元皇,《关雎》建始初:考察上古人文之初,乃至于《关雎》所谓男女相求,其阴阳相配之理皆同,合于《易》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的理念。故天地交而万物通,男女交而其志同。稽,考核,考察。元皇,上古最初的统治者;或谓“元皇”即尧、舜二帝,《尚书》始于二《典》,赞古之尧、舜,克明俊德,为至治之首君。《关雎》,为《诗经》之第一篇,其云: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”意为求淑善之女,以配君子。《关雎》之诗取阴阳二气相扭结而言,阴阳相配,得性情之正,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开始。建,创立,创建。始初,为“开始”之义。当,他本或作“称”。
[3]昏冠气相纽,元年乃牙滋:男女成人、婚姻相配,阴阳二气相扭结;元年、岁首之时,阴阳二气相感,万物由此萌芽滋生。昏冠,《礼》重冠、昏之仪式。冠,为冠礼,乃成人之始的一种仪礼。昏,为婚礼,乃男女婚配、立人伦之始的礼仪。纽,结合。元年,岁首之年,《春秋》起首即为“元年春,王正月”。牙滋,牙,通“芽”,有“萌芽”之义;滋,有“蕃息”、“生长”之义。昏冠,他本或作“冠婚”。
【译文】
于是,孔子赞《周易》,于鸿濛混沌、空洞至虚之中,首辟乾、坤两卦为万物之始;《尚书》称“稽古”,以《尧典》为治道之宗;《诗经》咏《关雎》,正夫妇人伦之道;《礼》重冠、婚之礼,明男女成人、婚配之仪;《春秋》以“元年”为第一义,表君臣之道始立,而治化由此萌芽、繁盛之义。
圣人不虚生章第十二
【题解】
本章明丹道火候变化与天符进退、《易》卦象数变化之理相合。
自外丹言之,阴阳相感而万物化生,铅金、汞银相感而大丹成。圣人以《周易》之卦符,以准天象阴阳运行之法则。丹鼎之上釜,其底玄黑如天,下釜如地,鼎中有铅金、汞银,以象日、月,大丹则象日月之精。《易》统论天地之事,故立象以尽言,立言以尽意;天象有阴阳消长,炼丹之火候有加减炭数;丹道变化之理,与天象如符若契,皆可以《易》明之。
自内丹言之,圣人观天之道、执天之行,借天象运行之进退、阴阳之屈伸,设之以为火候法象,以《易》卦象明之。日月行于天地之间,往来出没,即此为火候;人能反求己身,即可默会自身中日月火候进退之妙。
圣人不虚生,上观显天符[1]。天符有进退,诎伸以应时,故《易》统天心[2]。
【注释】
[1]圣人不虚生,上观显天符:圣人,或指伏牺。《周易·系辞》: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”圣人仰观俯察,定《易》之象数,以法则天象运行之理,乃至于万物之情,留示后人。天符,天之符信、节度,即天象运行之法则,如月行于天,一月一度与日交合;日月、五星等天体星辰,皆有其运动轨迹,故可谓之“天符”。
[2]天符有进退,诎(qū)伸以应时,故《易》统天心:天道运行有进退、屈伸,与《易》卦阴阳升降、往来代谢之理相应,故知《易》统贯天道之理。丹道通过“观天之道,执天之行”,借天符之进退、阴阳之屈伸,设为火候法象,以之示人。《周易·系辞》说:“《易》与天地准,故能弥纶天地之道。”又说:“变化者,进退之象也。”“往者屈也,来者信也,屈信相感,而利害生焉。”诎伸,即屈伸。天心,阴消至极则为阳生之始,此乃所谓“天心”,即天地生生不已之心。北宋邵雍《伊川击壤集》之《冬至吟》谓:“冬至子之半,天心无改移。一阳初起处,万物未生时。玄酒味方淡,大音声正希。此言如不信,更请问包牺。”伸,他本或作“信”。
【译文】
作《易》之圣人观天之道、执天之行,以《易》卦爻之画以象天行之进退有节,其有大功、大德于天下,非虚生于世。天道运行有进退、屈伸,与《易》卦阴阳升降、往来之理相应,故知《易》统贯天道之理。
复卦建始萌章第十三
【题解】
本章论丹道进阳火之候。
自外丹言之,复卦一阳生于五阴之下,被用来表明炼丹起火之初,故说“复卦建始萌”。当此之时,金在下,居一阳之位;汞在上,处五阴之位,阴为阳变。复之震是乾之长子,震一阳初动于坤阴之下,故震因坤母而建立其根基。铅是乾父,母为流汞,金为长子,金由铅来,因母而化,金、汞相配欲恰到好处,用火之际须测十二钟律,如火急则药焦而失,火缓又恐不伏;亦要如斗、枢之升降,旋转鼎器,其升指鼎口向上,降指鼎口向下;又炉上安斗柄,逐月而顺转,亦同此理。火动三日,其气方达于器中,当此之时,汞居鼎之庚位,谨候月之生,即知汞之动静。月生八日,金亦随火气而动,金为君,其动迟,故八日而后行;汞为臣,其动速,故三日而己行,此时,金、汞相入、成汁,如上弦月平如绳。月至十五日,此时金合汞于鼎之甲位,而受气有金之形体。《周易参同契》以“蟾蜍月精”喻铅,以“兔魄日精”喻汞,日、月二精之气,于十五日双双明亮。每过十五天,变化一个节、气,每变一个节、气,则鼎中金、汞之形态亦有所变化。
自内丹言之,人身中一阳初动之时,即以十一月消息卦复喻之。人身之中亦有一阳生的情况,自子至巳为阳息,自午至亥为阴息,人身阴阳消息、升降之火候,与卦爻、钟律、斗枢变化之理同。农历每月初三日,黄昏时月生明在西方庚位,以《周易》震卦象之,喻人身之火候发动、河车开始运转之时;每月初八日,月为上弦,黄昏出现在南方丁位,以《周易》兑卦象之,喻人身阳火上升至一半之时;每月十五日,月望,黄昏时出现在东方甲位,以《周易》乾卦象之,喻人身阳火盛满之候。阳火自震而升,至于十五纯乾,则已满上半月之候,阳气势极,则屈曲折旋而低降。
复卦建始萌,长子继父体,因母立兆基[1]。消息应钟、律,升降据斗、枢[2]。三日出为爽,震庚受西方[3];八日兑受丁,上弦平如绳[4];十五乾体就,盛满甲东方[5]。蟾蜍与兔魄,日月气双明。蟾蜍视卦节,兔者吐生光[6]。七八道已讫,屈折低下降[7]。
【注释】
[1]复卦建始萌,长子继父体,因母立兆基:从复卦起,一阳初动于下,阳气渐立萌芽;复卦本由乾父下交于坤母之初爻而成,坤卦下变一阳爻,其内体成震,震所代表的一阳之气孕于坤母之腹,而承继乾父纯阳之体。震是乾之长子,乾为父,故说“继父体”;震孕于坤中,故坤是震之母,此为“立兆基”。一年二十四节气当中,以冬至为复;一月之中,以朔旦为复;一日之中,以夜半子时为复,其理皆同。始,初之意。萌,萌芽。兆,根基。
[2]消息应钟、律,升降据斗、枢:阳气自子至巳为息,自午至亥为消,故阴为消、阳为息,轮环不止。阴阳二气消息之法则,与钟律、斗枢的变化、升降之理相同。钟、律,古代之音律,有六阳律和六阴吕,其中,“钟”以度天上之文,“律”以测地中之气。在中国古代,音律常与历法配合,于一年十二月之内,每月换一管,一年换十二律管,以明阴阳之气消长的过程。《道藏》托名长生阴真人注《周易参同契》保留有“候气之法”,方法是以十二律管依次埋之于室内不同的方位,取芦葭灰填实于管中,以幕盖于管口之上;阴阳之气相继而至,则吹动芦葭灰,发出黄钟、大吕等不同的音律,以此便可以按时候阴阳之气,明其消息之征兆。其中,黄钟代表十一月子复卦一阳爻生之律;大吕代表十二月丑临卦二阳爻生之吕;太蔟代表正月寅泰卦三阳爻生之律;夹钟代表二月卯大壮卦四阳爻生之吕;姑洗代表三月辰夬卦五阳爻生之律;仲吕代表四月巳乾卦六阳爻生之吕;蕤宾代表五月午姤卦一阴爻生之律;林钟代表六月未遁卦二阴爻生之吕;夷则代表七月申否卦三阴爻生之律;南吕代表八月酉观卦四阴爻生之吕;无射代表九月戌剥卦五阴爻生之律;应钟代表十月亥坤卦六阴爻生之吕。斗,指北斗。枢,众星之枢纽,指北极星。升,自下而上为升。降,自上而下为降。斗、枢于一日十二时之内,每时移一位,一日移遍十二辰;丹道火候之升降亦如之,此为“升降据斗、枢”。当然,《周易参同契》于此不过取象比喻而已,不是说丹道非用律管之短长、天罡之所指而为其进火、退符时间之期度。
[3]三日出为爽,震庚受西方:每月初三日,月开始生明,于黄昏之时,呈现在天空西方之庚位,其象如娥眉,以《周易》震卦象之,因震卦一阳处于二阴之下,合于汉易纳甲之法震卦纳庚之理。爽,明也。之所以以西方为庚位,是因为中国古代以天干、地支配五行、五方,天干方面,如东方甲、乙木,南方丙、丁火,中央戊、己土,西方庚、辛金,北方壬、癸水;地支方面,亥、子为北方水,寅、卯为东方木,巳、午为南方火,申、酉为西方金,辰、戌、丑、未为中央土。此时,一阳震而动出。震庚受西方,他本作“震受庚西方”。
[4]八日兑受丁,上弦平如绳:每月初八日,月相变而为上弦月,于黄昏之时,呈现在天空南方之丁位,其象如弓之挂于墙壁,其弦平如绳索,以《周易》兑卦象之,兑卦一阴处于二阳之上,合于汉易纳甲之法兑卦纳丁之理。此时,阴阳平分各半。
[5]十五乾体就,盛满甲东方:每月十五日,月与日相望,月相变而为圆满,于黄昏之时,呈现在天空东方之甲位,以《周易》之乾卦象之,乾卦三阳,故汉易纳甲之法,以乾卦纳甲。此时,月既望而全受日光。
[6]蟾蜍与兔魄,日月气双明。蟾蜍视卦节,兔者吐生光:月至于十五日,圆满出于东方,此时,卦备三阳,日、月二精之气双双焕明。蟾蜍,喻月之精。兔魄,喻日之光。月之蟾蜍与日之兔魄两气双明。或借“蟾”为“瞻”,借“兔”为“吐”,日吐其光、月则瞻日之光,指十五望夕之月,全受日光。或谓蟾蜍与兔都居月亮之中,其他日子则亏缺而不能得见两兽之全貌;至十五日,两兽之气双双明于月亮之中。“蟾蜍”喻月,上半月为阳长,以《周易》卦爻象之,为震、兑、乾;下半月为阴长,以《周易》卦爻象之,为巽、艮、坤,故说“蟾蜍视卦节”;月为太阴,日为太阳,阳主吐而阴主纳,月本无光、受日之光而明,故说“兔者吐生光”。兔魄,他本或作“兔焕”、“兔影”。气双明,他本作“两气双”。
[7]七八道已讫,屈折低下降:阳火自震而升,至于十五日,成纯阳之乾,则已满上半月之候;月满则亏,阳极则阴长,十六日以后,则开始退阳火、用阴符。七、八,指每月的十五日;十五日后,月圆之形渐渐消缺。
【译文】
复卦用来表明炼丹起火之初,本由乾父下交于坤母之初爻而成,其内体为震,震所代表的一阳之气孕于坤母之腹,而承继乾父纯阳之体。自一阳而后,六阴、六阳一消一息,应黄钟、大吕等十二钟律之变化;其屈伸升降,应北斗、北极枢星之旋转。例如,农历每月初三日,月亮开始生明,于黄昏之时,呈现在天空西方之庚位,其象如娥眉,以《周易》震卦象之,喻丹道进阳火之时;每月初八日,月相变而为上弦,于黄昏之时,呈现在天空南方之丁位,其象如弓之挂于墙壁,其弦平如绳索,以《周易》兑卦象之,喻丹道阳火上升至一半之时;每月十五日,月亮与太阳相望,月相变而为圆满,于黄昏之时,呈现在天空东方之甲位,以《周易》乾卦象之,喻丹道阳火盛满之时。此时,兔魄之日、蟾蜍之月二精之气双双焕明。蟾蜍喻月之精气,月相的消长与《周易》卦爻之变其理相合。如丹道上半月火候为阳长阴消,月相依次为娥眉月、上弦月、圆月,分别以《周易》八经卦的震、兑、乾卦象之;下半月火候为阴长阳消,月相变化分别以《周易》八经卦的巽、艮、坤象之,故说“蟾蜍视卦节”;兔魄喻日,月亮本无光、受太阳之光而明,太阳主吐而月亮主纳,故说“兔者吐生光”。七、八相加为十五,指上半月从初一至十五这段时间,丹道进阳火,自震而升,至于十五日纯乾,则已满上半月之候,阳气的势力达到极盛;极盛之后,阳气开始走低,屈折往下而降。
十六转受统章第十四
【题解】
本章论丹道退阴符之候。
自外丹言之,于加热鼎器至于极盛之后,十六日,开始退火,作伏火而成其丹的前期准备工作;此时,月象巽卦,清晨没于天空西方之辛位,丹道以巽卦之象,以喻其减炭退火之候。二十三日清晨、平明时分,月亮运行至天空南方丙位,此为下弦之月,以艮卦象之,艮卦有覆碗之象,亦有止而不动之意,丹道以艮卦喻药在鼎中阴阳平平、如山之静止而不剧烈翻动。三十日,月没于天空东方乙位,坤卦本居西南、为阴,今没于东北阳方,以阴就阳,故有“东北丧其朋”之说。铅、汞得火交媾后,于此时可伏火,而小还丹成。如果要制作大丹,于前一月之功完毕后,还要添减药物,入鼎重修,月月循环,周而复始,周天火气足后,方能成就大还丹之功。
自内丹言之,月至十六日,光明乍亏,其象如巽,清晨没在天空西方之辛位,合于汉易纳甲法巽卦纳辛的道理,以人身火候言之,则为退阴符之初候,为阴符包阳、阳不得奔逸,性归于命之初之时;月至二十三日为下弦,光明半亏,其象如艮,清晨没在天空南方之丙位,合于汉易纳甲法艮卦纳丙的道理,以喻人身之中阴符下降至一半之候,为性归于命至于半之时。月至三十日为晦,光明尽丧,其象如坤,清晨没在天空东方之乙位,合于汉易纳甲法坤卦纳乙的道理,以喻人身阴符穷尽之候,一点阳魂全体敛入阴魄之中,为性返归于命之时。一月既尽,则阳又受阴之禅,复变阴为阳、成震之龙。其实,内丹于一息之间,便有月之晦、朔、弦、望四象:所谓上弦,即气之方息;下弦即气之方消;望即气之盈;晦即气之嘘,学者知之、行之,绵绵若存,用之不勤,自能体会《周易参同契》此说之精义。
十六转受统,巽辛见平明[1]。艮直于丙南,下弦二十三[2]。坤乙三十日,东北丧其朋[3]。节尽相禅与,继体复生龙[4]。
【注释】
[1]十六转受统,巽辛见平明:月亮于十六日后,阳始消退而阴始生长,月亮由圆乍变而为亏缺,如纯乾得坤一阴而成巽卦。清晨时分,在天空西方辛位出没,其象如巽,合于汉易纳甲法以巽卦纳辛之理。或谓十六日后,月出于天空东南巽位,运行至天空西方辛位,即为清晨、平明时分。以丹道火候言之,此则为阳受阴禅、峰回路转之时。统,统领之意。十六日后,坤变乾一爻为巽卦,巽一阴爻生、伏于二阳之下,巽受乾统,故说“受统”。平明,清晨。
[2]艮直于丙南,下弦二十三:月亮至二十三日,为下弦,光明半亏,清晨时分,在天空南方丙位出没,其象如艮,一阳爻在上,二阴爻在下,合于汉易纳甲法以艮卦纳丙之理。以丹道火候言之,此则为阴符下降至一半的时候。直,当值,即执行其职责之意。
[3]坤乙三十日,东北丧其朋:月亮至于三十日为晦,清晨没于天空东方之乙位,光明丧尽,其象如坤,合于汉易纳甲法以坤卦纳乙之理。以丹道火候言之,此则为阴符消尽阳火、阴符穷尽之时。经文“东北丧其朋”语出《周易·坤》卦辞:“元亨,利牝马之贞。君子有攸往,先迷后得主,利,西南得朋,东北丧朋。安贞吉。”《坤·彖》:“‘西南得朋’,乃与类行。‘东北丧朋’,乃终有庆。”或谓《周易参同契》于此借《周易·坤》之“朋”字以作“明”字用,“丧朋”即“丧明”之意,故此句他本或作“东方丧其明”、“阳路丧其朋”等等。
[4]节尽相禅与,继体复生龙:一月之内,阳长阴消各居一半,三十日共分为六节:自朔旦至初五日为第一节,月相主要表现为娥眉月,以震卦象之;六日至十日为第二节,月相主要表现为上弦月,以兑卦象之;十一日至十五日为第三节,月相主要表现为圆月,以乾卦象之;十六日至二十日为第四节,月相主要表现为下缺之凸月,以巽卦象之;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为第五节,月相主要表现为下弦月,以艮卦象之;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为第六节,月相逐渐消尽,以坤卦象之。一月六节既尽,则日月合朔之后,阳又受阴之禅,循环重复如初,复变为震,继阴之体,而复生阳,震为龙,一阳动于二阴之下,故说“继体复生龙”。节尽,指一月之终、六节皆尽。禅与,月终为阴、月初为阳,于下月之朔旦,阴让位于阳,即禅与之意。宋末学者俞琰对《周易参同契》将汉易纳甲与月相结合,以月相变化及其出没方位明丹道之火候有一详细考察。他认为,就一年来讲,春夏秋冬四季,昼夜短长各不相同,春夏一般昼长夜短,秋冬一般昼短夜长。通常情况下,如果值昼短夜长的秋冬季,太阳没于西方申位,月亮则现于西方申位而望于东方寅位;如果值昼长夜短的春夏季,则太阳没于西方戌位,月亮则现于西方戌位而望于东方辰位。因此,一年十二月之中,初三日所现之娥眉月,未必尽现于西方庚位,现于西方庚位者,其实是二、八月昼夜均平之时的月亮;而昼短夜长的秋冬季,初三日的月亮则现于西方申位;昼长夜短的春夏季,初三日的月亮则现于西方戌位。故一年中,初三日的月亮有时候现在庚位,有时候则现在申位与戌位。同理,十五日之月也未必尽见于甲。见于东方甲位者,也是二、八月昼夜均平之时的月亮。而昼短夜长的秋冬季,十五日的月亮则现于东方寅位;昼长夜短的春夏季,十五日的月亮则现于东方的辰位。故一年中,十五日的月亮有时候现在甲位,有时候则现在寅位与辰位。而且,由于日月合朔有先后,有大月与小月之区分,因此,上、下弦也未必尽在八日、二十三日,望、晦日也未必尽在十五日、三十日。《周易参同契》之所以谈月相变化,论月出没之方位、律历盈缩短长之法,只是取其象来说明丹道火候的进退,如一阳生即三日月生之震象,二阳长即八日月弦之兑象,三阳满即十五日月圆之乾象,一阴生即十六日月亏之巽象,二阴长即二十三日月弦之艮象,三阴足即三十日月没之坤象。丹法中,所谓“冬至”、“晦朔之间”等,皆以之比喻炼丹时阴极阳生之时,如以月言之则为月晦之夜,如以年言之则为仲冬之节,如此而已。继体,他本或作“继际”。
【译文】
月至十六日,光明乍亏,其象如巽,清晨没在天空西方辛位,合于汉易纳甲法巽卦纳辛的道理,丹道以之喻进阳火之后、退阴符之初候。月至二十三日为下弦,光明半亏,其象如艮,清晨没在天空南方丙位,合于汉易纳甲法艮卦纳丙的道理,丹道以之喻阴符下降至一半之候。月至三十日为晦,光明尽丧,其象如坤,清晨没在天空东方乙位,合于汉易纳甲法坤卦纳乙的道理,丹道以之喻阴符穷尽之候。一月既尽,则阳又受阴之禅,复变阴为阳、成震之龙,开始下一轮新的阴阳消长循环。
壬癸配甲乙章第十五
【题解】
本章论丹道一月之中的乾、坤八卦纳甲之火候。而丹道一年与一日之火候,亦同其理。
以十天干论,甲是阳之始,壬是阳之终;乙是阴之始,癸是阴之终。汉易纳甲法,以乾纳甲、壬,坤纳乙、癸,故乾启其初始,坤成其有终。以《易》言之,七为少阳,八为少阴,九为老阳,六为老阴,此为《易》之四象;四象和合,实即阴阳和合。
自外丹言之,金、汞煅炼、变易成丹之道,要顺其阴阳,阴至则藏,阳至则出。阴阳水火之气,能煅金、汞之形,甲乙青龙是汞,壬癸玄武为铅,以二物相配,变化成丹。初发火,从坤阴之下生起乾阳,即是起始;乾阳至于极盛,则其下生起坤阴,坤主于终,至月末阳气渐灭藏,为伏火之时。七、八、九、六,一月一周旋,常以乾、坤二卦火候,循环使用。炼丹时,八卦列布于鼎炉之八方,周回列以二十八宿,模拟日、月往来之路径,日月、群星、列曜运转,皆受居中天之斗、枢指挥;鼎中药物升降、变化有其理路,其运火转鼎,亦皆不失其理。
自内丹言之,火候之抽添与月之盈亏无异。易之纳甲,实可以为丹道火候之取象。上半月乾阳用事,属木、火,“七”为火之成数,“八”为木之成数,合之得十五;下半月坤阴用事,属金、水,“九”为金之成数,“六”为水之成数,合之亦得十五;由木八、火七之阳,历金九、水六之阴,共得三十。一月中,月相经由初三震一阳生之娥眉,初八兑阴阳相持之上弦,十五乾三阳之月盈;至十六巽一阴生,二十三艮之阴阳相持之下弦,至于三十日坤阴月晦,光明尽灭,内丹理论借此以论人身中八卦火候之进退,进阳火、退阴符皆有其序,合于其序,则还丹可成。“中”即指黄道,作丹之时,心猿不能奔逸于外,如果能收视返听,凝神于内,使人身之精炁与神皆归于黄道而不失其中,则氤氲交媾,结成一滴露珠,而飞落丹田之内。
壬癸配甲乙,乾坤括始终[1]。七八数十五,九六亦相应;四者合三十,阳气索灭藏[2]。八卦布列曜,运移不失中[3]。
【注释】
[1]壬癸配甲乙,乾坤括始终:乾为阳,坤为阴。汉易纳甲之法,以乾纳阳干甲、壬,坤纳阴干乙、癸,故说甲、乙配壬、癸;十天干始于甲、乙,终于壬、癸,甲是阳之始,壬是阳之终;乙是阴之始,癸是阴之终,故说“乾坤括始终”。八卦之中,唯有乾、坤纳二干,余卦只纳一干。此言丹道于一月中,乃至于一年、一日中,皆用乾、坤二卦运火。初发火,坤阴之下生起乾之阳,故乾之阳为初始;乾阳至于极则其下又生起坤之阴,坤阴主于终末。常用乾、坤二卦,以明丹道阴阳变化一周旋、循环相联结。《周易·系辞》:“乾知大始,坤作成物。”即此为始终之义。括,包括、联结之意。
[2]七八数十五,九六亦相应;四者合三十,阳气索灭藏:七、八、九、六,四者合为三十日,应一月之日数。三十日中,少阳数七、少阴数八,合之得十五;老阳数九、老阴数六,合之得十五;四者合之得三十,可应一月之数。阴阳各分其半,丹道顺其阴阳,阴至则藏,阳至则出,至三十日数尽,阴符、阳火俱终,则日月合璧,月亮体化纯坤之阴,光明灭尽,故以《易》卦所表象的种种月相,亦索然而灭藏。索,尽之意。或谓上半月乾阳用事,属木、火,“七”为火之成数,“八”为木之成数,合之得十五;下半月坤阴用事,属金、水,“九”为金之成数,“六”为水之成数,合之亦得十五;由木八、火七之阳,历金九、水六之阴,共得三十,此时月亮之光明尽灭。经文此说基于《周易·系辞》所保留之古筮法,其以大衍之数五十,经过“四营”、“十八变”,最后得七、八、九、六之策数。阳气,他本或作“易气”。
[3]八卦布列曜(yào),运移不失中:当丹道一月运火之时,皆应循八卦、列曜运行之理而行;火符阴阳运移不失其理,则可以准造化而无差,应卦爻而不忒。八卦,为乾、坤、坎、离、震、巽、艮、兑。布列曜,鼎炉之八方布以八卦,周回列以二十八宿,模拟日、月往来之路径。中,指斗、枢居中天,运转群星,有其不变之理,外丹法以“中”喻鼎;或谓“中”指天文学上的黄道;或谓“中”指“天心”;还有以“中”为二至,即冬至、夏至的说法。八卦布列曜,他本或作“八卦列布曜”、“八卦列布辉”等。《道藏》所保留的容字号无名氏《周易参同契注》等注本,在“八卦列布辉,运移不失中”前,还有“象彼仲冬节,草木皆摧伤。佐阳诘商旅,人君深自藏。象时顺节令,闭口不用谈。天道甚浩广,太玄元(作者案:此“元”字当作“无”字)形容。虚寂不可睹,匡郭以消亡。谬误失事绪,言还自败伤。别序斯四象,以晓后生盲”一段经文,与其他《周易参同契》注本在篇章结构上有所不同。
【译文】
甲是阳之始,壬是阳之终;乙是阴之始,癸是阴之终;汉易纳甲法,以乾纳甲、壬,坤纳乙、癸,故乾启其初始,坤成其有终。少阳数七、少阴数八,合之得十五;老阳数九、老阴数六,合之得十五;四者合之得三十,可应丹道一月火候之数,此时,日、月合璧,月亮体化纯坤之阴,光明灭尽,故以《易》卦所表象的种种月相,亦消失而无踪迹。炼丹时,八卦列布于鼎炉之八方,周回列以二十八宿,模拟日、月往来之路径。日月、列曜运转,皆受居中天之斗、枢指挥;鼎中药物升降、变化,亦有其理路,其运火转鼎、火候抽添,与以汉易纳甲所表征的月相盈亏之理无异;故丹道进阳火、退阴符皆有其序,合于其序,则阴阳和合得中,还丹可成。
元精眇难睹章第十六
【题解】
本章言炼丹要循刻漏而运符火,明抽添以分进退,火候与日月星辰行度之数相合,方能合成大丹。
自外丹言之,铅金、流汞禀精炁于鼎器中,不可见其状貌。运火当以日、月运行周天法度等法则为指导,以《周易》卦象取真符为证而测之,顺时令起火,观其气象,察其成形,谨候鼎器中铅金、流汞之消息,其凝结之期可候而知。在这个过程中,须上测星象以择吉辰,下观其地,背阴向阳,中考人情,温善和顺,天、地、人三才皆备,依乾、坤卦理运火,阳动阴静,因循卦节,无所忧虞,则还丹可成。
自内丹言之,元精生于窈冥,眇不可睹,洞晓天地之阴阳,则能深达人身之造化。神定炁和,则内外符合;神昏炁躁,则时刻差忒,之所以说立表占候,只恐失天人合发之机。内丹之道与天地之道同理,修丹者循卦节而行阳,则动可不失《周易》卦爻象变动之时;体彖辞而行阴,则静不失至柔含光之理;虚其心,运其神,则能回天关、转地轴,上应河汉之昭回,下应海潮之升降。如此,则天地虽大、造化虽妙,皆可掇入人一身之中来。乾、坤得坎、离运用于其间,则阴阳交泰而和气致祥。内丹火候之诀最为精妙,非常情所能推测,宜细推详,与之相符,卦节无差,方能成功。
元精眇难睹,推度效符证[1]。居则观其象,准拟其形容[2]。立表以为范,占候定吉凶[3]。发号顺时令,勿失爻动时[4]。上察河图文,下序地形流,中稽于人心,参合考三才[5]。动则循卦节,静则因彖辞[6]。乾坤用施行,天地然后治,可得不慎乎[7]!
【注释】
[1]元精眇难睹,推度效符证:元精乃天地元炁之精华,生于虚无,无形象之可睹;窈冥渺茫,无踪迹之可求,搏之不得,视之不见,而能潜随化机,生成万物。元精既窈冥难睹,玄远不可见其形状、容貌,故以《周易》之卦爻象推其符证,效其法度,从而洞晓阴阳,深达造化。此句经文源于《周易·系辞》:“《易》者,象也;象也者,像也。”《道德经》:“窈兮冥兮,其中有精;其精甚真,其中有信。”(二十一章)因大丹之道,与天地造化之理相符。因此,《周易参同契》以“元精”喻鼎中神灵之真精,以其为至灵、至神之宝。欲求此元精,须推日月以度寒暑,占卦象以明吉凶,运火、行卦皆法周天行度,以取真符为证。元精,即元炁。推,推理。度,衡量。符证,指用《周易》卦爻所表证的天文与地理之法则。睹,他本或作“视”、“觌”(dí)。
[2]居则观其象,准拟其形容:故仰观象天文,俯察循地理,乃可以和合天地之阴阳。丹道运火、观其鼎,不得失其理则,推阴阳消息,象其时而动,故应观其气象,察其成形,以为仪则。《周易·系辞》说:“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。”象,此处指日月、五星、二十八宿等在天所成之象。形容,元炁在地所成之形状、相貌。拟,他本或作“仪”、“法”。
[3]立表以为范,占候定吉凶:天道深远而难窥,故立表为范,因《易》象以见之;立表、占候,实欲勿失《周易》卦爻所示之天运法则。作丹之时,当立表、漏以测天运之晷刻,以验鼎炉运火之刻漏,方能交媾坎离,而成纯乾之体,不失天地之机。表,晷表,计时之器。范,法则之意。占候,特指汉易之卦气说。其以《周易》卦爻与一年之四季、十二月、二十四气、七十二候一一对应,卦气与时应之与否,会产生各种吉凶祸福。《周易·系辞》说:“吉凶者,失得之象也;悔吝者,忧虞之象也。”既有失则悔吝生,悔吝生则忧虞至;炼丹须谨候炉中消息,无所忧虞,则还丹可得。占候,他本或作“候占”。
[4]发号顺时令,勿失爻动时:炼丹时,火候进退皆要应于阴阳、四时之节令,勿违《周易》卦爻所表征之气候、时宜。发号,指发阴阳相和、刚柔相应之号令。时令,指春夏秋冬四时和一年十二月、二十四节气。爻动时,喻指汉易卦气说。卦气说将一年中二十四节气、七十二候等与《周易》卦爻相配,这样,气候之变化与《周易》卦爻相应,呈现出某种节序性与规律性。炼丹之火候,刚极则亢、阴极则邪,故应勿失四时、二十四气之节序,有如春养、秋成,夏长、冬藏,皆要合于正理,不能违背卦爻所示变化之道。
[5]上察河图文,下序地形流,中稽于人心,参合考三才:炼丹要上择吉辰,测其星象;下观其地,背阴向阳;中考人情,品性温善。三才皆备,方无休咎。以天道言之,北极和北斗七星居中运化,群星在银河内外进退、屈伸,天道示象,昭然著明。道教炼丹,火候之诀最为精妙,其与天道进退、屈伸之理相符。上察天河运化之法则,以为图文,于炼丹中方有形象、状貌可以比拟,如《周易》《观·彖》说:“观天之神道,而四时不忒。”《周易》之《贲·彖》说:“观乎天文,以察时变。”其次,立晷表于地,以测知潮候、时节之变化,此为地道流形之显著的现象,通过确定地面上万象运化、品物流形之法则,相与亏盈,以之作为炼丹之轨范,则可以“下序地形流”;或谓炼丹安置炉灶、药院等须择名山,选取胜地,顺其地形、水流之利,为“下序地形流”。再次,炼丹者顺天道、地道运行法则以行事,无过、无不及,此则为“中稽于人心”;或谓炼丹须谨慎选择同伴,考察其性情品德,如其和纯而志于道,方可将其作为自己的同志,共同从事于丹道。天、地、人三才相应,与《周易》所示卦节无有差忒、不失爻动之时,如此,炼丹者方能“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,与鬼神合其吉凶”。河图,天河之图,或谓“河图”指以《周易》卦爻所表征出来的天象图。文,天文。序,随顺、安置之意。稽,考察之意。三才,亦作“三材”,指天道、地道、人道。《周易·系辞》说:“《易》之为书也,广大悉备,有天道焉,有人道焉,有地道焉,兼三才而两之,故六。六者非它也,三才之道也。”《周易·说卦》:“立天之道曰阴与阳,立地之道曰柔与刚,立人之道曰仁与义,兼三才而两之。”人心,他本或作“人情”。参合,他本或作“参同”。
[6]动则循卦节,静则因彖辞:炼丹者以《周易》卦爻象及其变化法则作为行动的指南,以卦爻辞所阐发的道理作为恒久不变的义理。此句的主要意思是指炼丹运火要因循卦节、顺阴阳动静而变化。经文源出于《周易·系辞》:“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,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。”“彖者,言乎象者也。爻者,言乎变者也。”
[7]乾坤用施行,天地然后治,可得不慎乎:乾阳、坤阴之气为天地造化、生物之本,乾坤阴阳之气交泰则和气致祥,天下万物化生,各得其所宜。炼丹之运火同于此理,阴阳二气和则致祥、乖则致厉,这难道能掉以轻心吗?或谓乾、坤之用,即用九、用六,乾用九“见群龙无首,吉”;坤用六“利永贞”,于此比喻炼丹当法自然、无为,执守正道。亦有谓乾、坤之用为坎、离,天地得坎月、离日运行于其间,所以成四时之变化;天地一日无坎、离,则造化就停而不运,丹道法此乾坤坎离之用。治,他本或作“理”,似为避唐高宗李治之讳而改为“理”。此经文源出于《周易·文言》:“乾元用九,天下治也。”“乾元用九,乃见天则。”可得不慎乎,他本或作“可不顺乎”。
【译文】
元精乃天地元炁之精华,窈冥难睹,玄远不可见其形状、容貌,故以《周易》的卦爻象推其符证,效其法度,修丹者从而能洞晓阴阳,深达造化。丹道运火,应测鼎中药物变化之气象,察其成形,不得失其理则;通过立表、漏以测天运之晷刻,以验鼎炉运火之刻漏,方能交媾药物成丹;立表、占候,实欲勿失《周易》卦爻所示之天运法则。炼丹时,火候进退皆要应于阴阳、四时之节令,勿违《周易》卦爻所表征之气候、时宜。如炼丹要上择吉辰,测其星象;下观其地,背阴向阳;中考人情,品性温善,此天、地、人三才皆备,方无休咎。炼丹者以《周易》卦爻象及其变化法则作为行动的指南,以卦爻辞所阐发的道理作为恒久不变的义理,炼丹运火因循卦节、顺阴阳动静而变化。尤其当注意的是,乾阳、坤阴之气为天地造化、生物之本,乾坤阴阳之气交泰则和气致祥,天下万物化生,各得其所宜。炼丹运火亦同于此理,阴阳二气和则致祥、乖则致厉,这怎么能掉以轻心呢!
御政之首章第十七
【题解】
本章详论丹道起首之功、进火法度、失火候之殃咎。
自外丹言之,还丹之法,务在纳闭管口,使其坚密。炼丹起火之初,安布铅、汞二宝于鼎器中,鼎炉之固济如关锁牢结,令其微细牢密,其药则能不走失。在这个过程中,顺天道五星、二十八宿阴阳升降之候而运火,依《周易》卦爻象变化之则而行功,不时翻覆鼎器,增减药物,加减炭火,无所差失,时至则可开鼎舒器而成丹。然则吉凶悔吝生乎动,于此过程中不可有毫发差殊,如有差殊,则如天道乖离、政事错谬,丹道亦倾覆。
自内丹言之,御政之首,乃一阳初动、交媾坎离之时,其发号施令,必须谨慎,要管括元炁,使之微密紧固,即眼含其光,耳凝其韵,鼻调其息,舌缄其气,趺足端坐,潜神内守,不可一毫外用其心;眼既不视,则魂自归肝;耳既不听,则精自归肾;舌既不声,神自归心;鼻既不嗅,魄自归肺;四肢既不动,意自归脾;然后,魂在肝而不从眼漏,魄在肺而不从鼻漏,神在心而不从口漏,精在肾而不从耳漏,意在脾而不从四肢孔窍漏,五者皆无漏,则精、神、魂、魄、意相与混融,化为一炁,而聚于丹田,自可布宝于金胎、玉室。天道随斗柄以定晨昏,如失其序,则俯仰上下而乖戾集。丹道亦有其“斗”,“斗”即人之“心”,心斡运一身之阴阳,统摄一身之万化,犹网之有纲,衣之有纽,人身上、中、下三丹田,得心之斡运,则真炁上下循环,如天河之流转。如其有失,则有走泄之虞。
御政之首,管括微密,开舒布宝[1]。要道魁柄,统化纲纽[2]。爻象内动,吉凶外起[3]。五纬错顺,应时感动[4]。四七乖戾,离俯仰[5]。
【注释】
[1]御政之首,管括微密,开舒布宝:治理天下政事,首先即当依其理来执守、统御。炼丹与之同理。运符火起首之初,须先确定炼丹微密之理旨,使自己心里了然明白,同时遏制、弃绝各种凶险情况,管理、密固丹药之精,使之坚固,无走泄之虞,自然可以展示元阳至宝于金鼎、玉室之中。御,统领。政,治理。首,开始。管,管理。括,系结,约束。微,隐微。密,细密,严密。炼丹之鼎,要固济之,如关结锁籥,令其微细牢密,不轻易走失。开,开发。舒,舒畅。布,陈列,展示。宝,丹之精华。微密,他本或作“密微”。开,他本或作“阖”。
[2]要道魁柄,统化纲纽:北斗所指,斡运群星之动,顺北斗所指而行,则众星皆安,其所遵循之法则,即为天运之枢纽和纲纪。炼丹之道与天文之理同,丹道水、火进退皆有其理,有如众星随北斗所指而运一般。要道,阴阳相配合之道。魁柄,天文学上的术语。北斗七星,第一星名天枢,第二星名璇,第三星名玑,第四星名权,第五星名衡,第六星名开阳,第七星名瑶(摇)光。其中,第一至第四星组合为“魁”,第五至第七星组合为“标”(杓),合魁、杓而为北斗,“魁”为“斗”之首,“杓”为“斗”之尾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说:“北斗七星,所谓旋、玑、玉衡以齐七政。”《史记索隐》:“案:《尚书大传》云‘七政,谓春、秋、冬、夏、天文、地理、人道,所以为政也。人道正而万事顺成’。又马融注《尚书》云‘七政者,北斗七星,各有所主:第一曰主日;第二曰主月法,第三曰命火,谓荧惑也;第四曰煞土,谓填星也;第五曰伐水,谓辰星也;第六曰危木,谓岁星也;第七曰罚金,谓太白也。日、月、五星各异,故名曰七政也’。”如此说来,则北斗七星,可以使一年四季春、夏、秋、冬顺时而更迭;不仅如此,还可以使天文、地理、人道皆合于其序而运转。如果仅就天文言,则北斗七星,能使日、月和荧惑、填星、辰星、岁星、太白五星得其所主而运行不差违。炼丹之道与天文之理同,顺北斗斗柄所指而行,则五星、五行皆安;丹道水、火之进退,亦皆有其理,顺之则还丹可成,无有差忒。纲纽,网有纲,衣有纽,皆喻指关键处。柄,他本或作“杓”。
[3]爻象内动,吉凶外起:丹道进火、退符是否顺阴阳而动,是否与《周易》卦气之候相符、相应,这决定了鼎炉内丹药烹炼之顺逆、吉凶。此句源出于《周易·系辞》:“爻也者,效此者也。象也者,像此者也。爻象动乎内,吉凶见乎外,功业见乎变,圣人之情见乎辞。”外起,他本或作“始起”。
[4]五纬错顺,应时感动: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运转是顺行还是错乱,则天时与气候皆与之相应而有所感。五纬,指五星,如土星旧称“镇星”,火星旧称“荧惑星”,水星旧称“太阴星”,金星旧称“太白星”,木星旧称“岁星”。以前的人们认为五星时有迁移,而经星则亘古不易,故有经、纬之分;或谓日月为经、五星为纬;或谓五纬为五行、四时。
[5]四七乖戾,(yí)离俯仰:二十八宿布于天穹之东南西北四方,上分周天三百六十之度数,下界九州山川之分野,如果错乱、差殊而失其位,改移其上下之序,则天道变于上,地道、人事错乱于下。丹道亦同此理。四七,指周天之二十八宿。乖戾,指错乱、差殊。离,改移,失位。俯仰,他本或作“仰俯”,指上下变化之意。,他本或作“侈”。
【译文】
治理天下政事,首当依其法则、规律;炼丹与治政之理同,也要明其法则;先当牢固丹药之精,使之无走泄之虞,由此便可以展示元阳至宝于金鼎、玉室之中。丹道之成功与否,重在水、火之进退;水、火进退如众星随北斗所指而运一般,皆有其理。丹道进火、退符是否顺五星、二十八宿阴阳升降之理而动,是否与《周易》卦气之候相符、相应,这决定了鼎炉中丹药烹炼之顺逆、吉凶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运转是顺行还是错乱,则天时与气候皆与之相应而有所感;二十八宿布于天穹之东南西北四方,上分周天三百六十之度数,下界九州山川之分野,如果错乱、差殊而失其位,改移其上下之序,则天道变于上,地道、人事错乱于下。丹道亦同此理。
文昌统录章第十八
【题解】
本章说明丹道之理可与天道、治道之理相通。
自外丹言之,丹道炉火引天文星象如“文昌”等,主要为取象,因象以明其理。文昌调理阴阳众星。在丹道中,“文昌”或谓鼎炉,喻土;阴阳众星则代表水、火、木、金等药物,因水、火、木、金四者,皆可入于土灶中得到煅炼。或谓“文昌”为“北斗星”之辅星,喻炼丹之炉鼎,而“三台星”则喻为鼎脚之三足配合;旧说认为,炼丹炉鼎的形状与一般的鼎有不同之处,其上安装有斗形装置,下面方为鼎之身,再往下有三足配合,合而观之,其形状有似于北斗、文昌与三台之星,此鼎常常用于丹道文火烹炼之时,故以“文昌”主之。“文昌统录”于丹道言,则象征鼎内纳受天地万物之气,得火烹炼,生成种种变化。如果天运阴阳相乖,则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时失度,这就好比炼丹运符火之士于丹药调制、烹炼过程中,调适有过差则要有所规正,此谓诘责。因为道教修炼金液还丹,其秘在于铅、火,铅、火之用贯通于炼丹过程之始终,铅、火不真则所炼之丹难成;有如众星失其度,众星失度则阴阳相乖、四时失序。
自内丹言之,“文昌”喻为绛宫之天子,它统辖人一身之乾坤;“乾坤”喻阴阳,“文昌”有如心神,统一身阴阳之精炁,使之结而成内丹。道家有三丹田之说,其中之中丹田,有时亦称“绛宫”。后世认为,道家炼精化炁在下丹田,炼炁化神在中丹田,炼神还虚在上丹田,最后,粉碎虚空,炼虚合道。如此说来,中丹田之绛宫,乃丹道修持过程中的炼炁化神之所。绛宫亦有其主宰,谓之“绛宫天子”,此绛宫天子即为“文昌”,故“文昌”不过是对炼炁化神阶段修行人心神之功用的一种比喻说法。内丹众卦火符不失其度,则万化流通而圣胎增长,而此皆取决于修丹者一心之功。
文昌统录,诘责台辅[1]。百官有司,各典所部[2]。
【注释】
[1]文昌统录,诘责台辅:文昌乃统辖、总理之星,众星中的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、周天二十八宿、乃至三台、辅星等,悉皆为文昌所管。如果阴阳顺时,则众星受文昌之统辖而周行不息;如果阴阳过差,则文昌诘众星之过咎,使之处正。关于“文昌”,《史记·天官书》云:“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:一曰上将,二曰次将,三曰贵相,四曰司命,五曰司中,六曰司禄。在斗魁中,贵人之牢。魁下六星,两两相比者,名曰三能。”认为“北斗”之首“斗魁”上有六星如匡之形,覆于其上,此即是“文昌”或“文昌宫”。“文昌宫”六星如匡之形,成“天府”、“天宫”、“天庭”之象,为北辰天帝下面的辅弼之官居之之所,其功能为扬天之纪、执天之衡,主宰天之众星,有如人世间之丞相,上佐天子理阴阳、顺四时,下遂万物之宜,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。《史记索隐》谓:“《春秋元命苞》曰:‘上将建威武,次将正左右,贵相理文绪,司禄赏功进士,司命主老幼,司炎(疑作“司中”)主灾咎也。’”关于“文昌六星”,《汉书·天文志》与《史记·天官书》之说略有不同,其以第五星为司录、第六星为司灾。台辅,为魁下六星,因其两两相比,故曰“三台”或“三阶”。《史记集解》谓:“应劭引《黄帝泰阶六符经》曰:‘泰阶者,天子之三阶:上阶,上星为男主,下星为女主;中阶,上星为诸侯三公,下星为卿大夫;下阶,上星为士,下星为庶人。三阶平,则阴阳和,风雨时;不平,则稼穑不成,冬雷夏霜,天行暴令,好兴甲兵。”或谓“台”为三台星,“辅”则为北斗旁之辅星。统录,他本或作“总录”,大概有总辖、诘问的意思。
[2]百官有司,各典所部:其他众星,各有其职责,分掌其分内之事。例如,唐代天文书《神枢灵辖》就认为:柱史一星,主记过失;三公三星,主宣德化;九卿三星,主理万事;尚书五星,主纳言;谘谋、大理二星,主刑狱事;其余众星,各有其位。百官有司,泛指各级官吏与部门皆有其执事。典,掌管。
【译文】
文昌乃统辖、总理之星,三台、辅星等悉皆为文昌所管辖;如果阴阳顺时,则众星受文昌之统率而周行不息;如果阴阳过差,文昌则诘众星之过咎,使之处正。其他众星,各有其职责,分掌其分内之事。
日合五行精章第十九
【题解】
本章言丹道循火候之正的效果,以及坎离药物交媾不合法度、刚柔失其道、动静失其时的后果,以及改正的必要性。
自外丹言之,每月初为阳火生起之时,月底伏火,晦而为阴,一月之中,而有阴阳往返、终而复始;鼎中金、汞得火烹炼,翻覆轮转,与之相似。阴阳之道,亦可喻丹道之文、武火候,文、武火候得其时则金、汞存,文、武火候失其时则金、汞逃逸;月有晦朔弦望,进退盈缩,如不明其度数,悔吝过度,则难知丹道金、汞相合之期。例如,金得猛武之火过多则亢,不成正道;汞受刚阳之气过甚则流荡不顺循轨则;必使文、武火候恰到好处,循月之律纪、度数,金、汞方能阴阳相合。
自内丹言之,日即火,月即药,始为月朔,终为月晦,晦、朔之间,为阴将尽而犹未尽,阳将生而犹未生之时,此则为炼丹之关键点。君为神,臣为炁,作丹之时,身心寂然不动,身动则炁散,心动则神散,须是凝神聚炁,心息相依,然后灵胎可结。不然,则身中之神、炁有弦望、盈缩,而乖变凶咎生。推求其故,因心之君放肆而违道,于是身之炁亦邪佞而行不顺轨。此章以“君”喻天心,“臣”喻药物,“存”比喻片时得药,“亡”比喻顷刻丧失;受炁为吉,炁散则凶;火候得法,则还丹可成。
日合五行精,月受六律纪[1]。五六三十度,度竟复更始[2]。原始要终,存亡之绪[3]。或君骄溢,亢满违道;或臣邪佞,行不顺轨[4]。弦望盈缩,乖变凶咎[5]。执法刺讥,诘过贻主[6]。
【注释】
[1]日合五行精,月受六律纪:日、月与五星相经纬,共生万物。月与日一月一合,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,亦仿效月与日之合,因此,月与五星皆一月与日相合,故“日合五行精”,五行即指五星;律吕各六,一年共用十二律吕,而日、月共分之,故每月只受得一半律吕之气,故“月受六律纪”。《周易参同契》以此比喻丹鼎中纳受坎、离药物后,运水、火之气以炼之,以交媾日、月之精粹;在这个过程中,要升降文、武火符,始复终坤,否、泰相继,存亡相续,周而更始。或谓日主天干,天干有十,其中,甲、丙、戊、庚、壬五干阳刚,表太过;乙、丁、己、辛、癸五干阴柔,表不及;十天干分属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,故“日合五行精”。月主十二律吕,六律阳而六吕阴,一月分为六候,故“月受六律纪”。或谓“五行”即“五运”,即天干甲己所化之土,乙庚所化之金,丙辛所化之水,丁壬所化之木,戊癸所化之火;六律即六气,即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,其中,地支子午为少阴君火,丑未为太阴湿土,寅申为少阳相火,卯酉为阳明燥金,辰戌为太阳寒水,巳亥为厥阴风木。精,精华。纪,纲纪。合,他本或作“含”。
[2]五六三十度,度竟复更始:太阳一日行一度,月亮一日行十三度有余;太阳行至三十度,则太阳又与太阴也即月亮交合,周而复始,循环轮转,未尝暂停。五六三十日,五日为一候,六候为一月,五六为一月的天数。度,为计度、度数。竟,终结。天文学上,通常要计一日、一月、一年之周天度数,如太阳一天运行约一度,三百六十五日运行约三百六十度,也即一周天;月亮一日行十二度至十三度,一月则行满一周天;地球则一昼夜行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。日、月一月一合,一年十二个月,所合方位皆依周天二十八宿之度数。更始,指一月计度完日、月、五星相合之度数后,下一月又开始计算。后世或谓此段经文所说之“五”、“六”,主要阐明丹道中水、土之用,因为自甲至癸十天干,谓之十日,而五干刚五干柔,故日之数五,而土之生数亦为五;月律十二,而六律六吕,故月之数六,而水之成数亦为六。度竟复更始,指日月相互作用而成晦朔弦望之循环。
[3]原始要终,存亡之绪:推原天地万物之始,知其生生之根本,则能长存;探索天地万物之终结,知其终结之因,则能不亡;慎则转亡为存,不慎则转存为亡。或谓始为阳,终为阴,阴阳之道即文、武火候之谓,文、武以时则丹宝结,文、武不节,则丹药难合,终始存亡,在于文、武火候。或谓始为月朔,终为月晦,存亡之绪指晦、朔之间,阴将尽而犹未尽、阳将生而犹未生之时。当然,所谓晦朔乃譬喻,非真以之为月三十日之终、初一日之始。
[4]或君骄溢,亢满违道;或臣邪佞(nìng),行不顺轨:国君骄溢、凌驾于国法之上,不按照法则行事,则大臣、下属亦邪佞而不守法。推求凶咎之所以产生之故,皆由君主放肆而违道,于是大臣亦邪佞而违法,不顺行其轨则所致。在外丹中,君主骄逸、亢满,指火猛烈而致药失;臣邪行、不顺轨则,指鼎上所置之水本当平而满,但却行不顺轨而倾泄,丹道火候之用前后失序,则伤害鼎室中之药物。内丹以君为神、为志,臣为炁、为耳目之官,凝神则能聚炁,心息则能相依,身心寂然不动,然后灵胎可结。心动则神散,身动则炁散,心君倘若骄奢淫逸,妄想不除,必导致身体精耗炁散。君,丹道喻指金精、神胎、心神、火、日等。臣,丹道喻指流汞、身、精炁、耳目之官、水、月等。道,治国之道,于此则喻还丹之道。溢,他本或作“逸”、“佚”。
[5]弦望盈缩,乖变凶咎:月相有晦朔弦望,有盈有缩,而乖变凶咎由此而生起。弦,指上弦、下弦,如月八日为上弦,二十三日为下弦。望,日月相望见,十五日为望。其他,如三十日为晦,初一日为朔,皆为月相变化之关键点。就丹道言,月有盈缩,如对其度数不明,则难知金、汞相合之期。因金、汞在鼎炉中烹炼,什么时候药相熔而持平,什么时候药熬干结成砂,什么时候熄火,什么时候丹砂化而成丹宝,皆有其时候、法度,与日、月之盈昃相似,若有不顺,即有凶咎。
[6]执法刺讥,诘过贻主:国有执持正道之忠臣,见君有过,讥谏之,使君主能改正其过失。执,执持。刺讥,进谏,批评。诘,诘问。或谓执法为谏诤之官。贻,他本或作“移”,改移、修正的意思。
【译文】
丹鼎中纳受日、月即坎、离药物之后,即运文、武之火以炼之。在这个过程中,离日受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精华之炼制,坎月受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六气之熏习,通过升降文、武火符,行五运、六气,以交媾日、月之精粹。五日为一候,六候为一月,日、月相互作用而成一月三十日之晦、朔、弦、望,这个过程周而复始,循环轮转,未尝暂停。月始为阳起,月终为阴盛,阴阳之道于此即文、武火候之意。丹药存亡取决于炼丹终始之文、武火候,文、武火候得其时则丹宝结,文、武火候不节则丹药难合。铅金与汞、阳火与阴符、神与炁虽有君臣、主次之分,然其是否相得、和合,却取决于文、武火候是否相宜。如果文、武火候不相宜,则君、臣皆有所不安:好比国君骄溢,凌驾于国法之上,不按照法则行事,则大臣、下属亦邪佞而不守法。金与汞、神与炁在鼎炉中烹炼,何时药相熔而持平,何时药熬干结成砂,何时熄火,何时丹砂化而成丹宝,皆有其时候、法度,与日、月盈昃之理相似;炼丹者欲知金与汞、神与炁相合之期,当察月相晦朔弦望、盈缩之理,如对月之弦望、盈缩度数不明,即有凶咎。要使火候恰到好处,当顺其轨则,法其常道,正如国有执持正道之忠臣,见君有过而讥谏之,使君主能改正其过失;丹道火候有失,修丹者亦当改而正之,方保无虞。
辰极受正章第二十
【题解】
本章与此前三章皆以天文星象、治政之理以阐明丹道之理。丹居神室之中,犹北辰在天之极以正众星,人君布政以临万国,北辰中正而不偏则众星森罗恭顺,人君端拱而无为则天下和平。故治政之道法于天道,炼丹之道法于治政之道。
自外丹言之,北辰或北极以象铅金,明堂乃鼎器之象。铅金与汞处鼎器内,安静、寂然无所为,任鼎炉外之水、火熏蒸,只要火候合于其时且不妄意开阖扰动,则自然成其正体;有如治政,君垂拱无为则朝纲谐和。铅金等本出于矿石中,外形常暗淡;当其隐于鼎内,亦视之不见,搏之不得,然铅金、汞银得火煅炼,则如日、月之明;火气足后,汞自吐花而居铅之上,故见形骸;或者汞有花芽之后,研之成粉、入鼎,其花芽得火,日久自为灰形、露出铅骸。铅金、汞银为还丹之根,故为灵株;金、汞虽灵,不能流逸,故要固塞鼎器之口,勿使走失。铅金与流汞在鼎器之中,受日、月、众星之气,生成种种变化,虽不可得而见,然依法则炼之,则金、汞不逃逸,龙、虎得以交媾,故近而易求。
自内丹言之,心为明堂,心安而虚,道自来居;虚极静笃,元阳真炁自复。此犹人君坐明堂而布政,端拱于无为、清静,则能外却群邪、内正法纪,国泰民安;炼丹亦如之,道家内丹之法重收视返听,当隐藏其明,回光内照,无为静默,深根固蒂,使精、炁、神常存于丹田,不从耳、目、口等身体感官泄漏。倘若人能聚精、炁、神之三光,返照于其身内,则可以神不外驰而和气充周,美在其中。内丹修炼,“无为功里见神功,非有相中生实相”,虽视之不见、听之不闻,然其理昭昭,近而易求。
辰极受正,优游任下[1]。明堂布政,国无害道[2]。内以养己,安静虚无[3]。原本隐明,内照形躯[4]。闭塞其兑,筑固灵株[5]。三光陆沉,温养子珠[6]。视之不见,近而易求[7]。
【注释】
[1]辰极受正,优游任下:辰极,即“北辰”或“北极”,其为众星之主;众星围绕北极星而运转,北极星正则众星运行之轨迹亦正。关于“北辰”、“北极”,《史记·天官书》说:“中宫天极星,其一明者,太一常居也;旁三星三公,或曰子属。后句四星,末大星正妃,余三星后宫之属也。环之匡卫十二星,藩臣。皆曰紫宫。”唐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引《文耀钩》曰:“中宫大帝,其精北极星。含元出气,流精生一也。”又说:“案:《尔雅》‘北极谓之北辰’。又《春秋合诚图》云‘北辰,其星五,在紫微中’。杨泉《物理论》云‘北极,天之中,阳气之北极也。极南为太阳,极北为太阴。日、月、五星行太阴则无光,行太阳则能照,故为昏明寒暑之限极也’。”天空之中宫有天极之星,其一为太一所常居,即为“北辰”,也就是“北极星”。北极含元出气,流精生太一,其极之南为太阳、极之北为太阴,北极则居天之中,日、月、五星围绕北极而运转,当其运于极北则无光、运于极南则能照。天神中最尊贵的太一居北辰之中,北辰所在为紫微之宫,乃大帝之室。北辰之旁,有三星,代表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三公,主变出阴阳、佐理机务;北辰又有四后妃星从之,名为四辅,其中,末之大星为正宫,余三星为妃属。外环之有十二星,匡卫北辰,为藩臣之属。这是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对北极、北辰的一个描述。后世一些注本亦有以“辰极”为“文昌星”、“南极星”、“北斗”等不同理解。“北辰”在天为众星运转之枢机,在丹道中则为阴阳变化之根本。《周易参同契》将古代星斗信仰与道教丹道修持理论作了一个有机结合,它非常重视“辰极”等在丹道中的运用。后世注家或以“辰极”代表炼丹之重要药物“金”,“金”处鼎器中,任周围水火熏蒸而优游,“任下”即鼎外之炉火与水,这可以北极居中处正、众星围绕它有序运转来比喻;或谓“辰极”为炼丹之“鼎”,所谓鼎正则灵药不至于散失,药在鼎中可以有序地翻腾、运转,成就丹药;或谓“辰极”为神胎,其居中宫而不偏,则鼎室内自然金水相融;或谓“辰极”为“心神”,心神清静、无为,含光默默,绵绵若存,任其自然,不可劳其神,则精炁自然归元;或谓“辰极”喻人首之泥丸宫,“受正”指搬运坎、离之龙虎而朝纳于此,然后优游下于丹田、炁海,运火以炼之。虽然众家对于“辰极”在丹道中喻意之解释有所不同,但均以“北辰”于天文学意义上的居中处正、以斗布常、任运虚无来喻丹道修炼有其关键与枢机,枢机得正,则丹道自然不倾。优游,和顺自如之貌。受,他本或作“处”。
[2]明堂布政,国无害道:北辰居中处正,则五行之气和顺,众星自然顺行而无差忒;犹如人君处明堂之正,则臣下百官之人各负其责,朝政有条不紊。明堂,《史记·天官书》说:“东宫苍龙,房、心,心为明堂。”房星、心星、尾星等为明堂三星,属二十八宿中之东方苍龙宿;尤其“心星”,其体非常明亮,为苍龙宿中的大星,亦被称为“明堂”。在世俗政治中,“明堂”为天子布政之宫。外丹以“明堂”为鼎器之象,铅金为君之象,铅金在鼎器内,外有水火熏蒸,调均鼎器,使之坚固蒙密,即无邪害。于人体言,或谓泥丸之前一寸,即为“明堂”。宋末俞琰认为,《周易参同契》所谓“明堂”,在人则为“心君”,即所谓“洞房紫极灵门户”,其“心”中之“神”,则如《黄庭经》所说之“上清真人”,人君坐明堂而布政,有如心有神为之主宰,则神与炁相融、相抱,入于三丹田之内,熏蒸达于四肢、百骸,所谓“通道于九夷八蛮”,故身国无害道,而可保其长久。布政,他本或作“政德”。
[3]内以养己,安静虚无:丹道如政道,黄老之道的治政理念,重在无为静默,深根固蒂;丹道亦强调修丹者凝淡虚寂,不能三心二意,其心安静,则金、汞自安于鼎器之中,即能养成丹宝。尤其是内丹术强调心安而虚,道自来居,认为虚极静笃则元阳真炁自复。内,指鼎器内,或摒弃外在干扰而一心专注于内。己,指药,或指人之心性。或谓安静则身修,虚无则心修;“安静”喻指身之土,“虚无”喻指心之土。此句总括性、情之土。或谓“无劳尔形,无摇尔精,心若太虚,一物不着”,即“安静虚无”之意。
[4]原本隐明,内照形躯:推原元精为人生身之本,故回光内照,隐神不外耗,保炁以储精,外用既敛,内观以调摄,退藏于密,则返本还源。或谓心不外驰而得以虚无,即“原本隐明”之意;身知收敛而得以安静,即“内照形躯”之意。
[5]闭塞其兑,筑固灵株:既安铅、汞灵根于鼎器中,则须固济、筑塞其鼎口,使不外泄;铅金、汞为还丹之根,故称之为灵株,铅、汞虽灵,不能流逸,不闭塞鼎器之口,则难以收藏、固济,闭塞其兑则上不泄,筑固灵株则下不漏。内丹则认为,神不外驰,则人身之真炁和气充周,美在其中。兑,口之意。筑,固济。株,根本。
[6]三光陆沉,温养子珠:运三光真精而入丹田鼎器之内,哺养玄珠、灵胎。三光,指日、月、星,其中,日为阳光,星、月为阴光;亦有以三光为阳火、阴符与铅金之说;或谓三光为精、炁、神三宝,为耳、目、心等感觉器官,如有谓:“天有三光,日、月、众星;人有三光,两目一心。”陆沉,日、月、众星之光向下照于大地,谓之“陆沉”。亦有以“三光”指人之三丹田,“陆沉”为六腑,存三丹田之炁以灌溉六腑,温养精神,神令不散,则魂魄长存。温养子珠,如鸡孵卵,温温默默,不徐不疾,不燥不寒,和气渐蒸,无为功里见神功,非有相中生实相。子珠,指元精。
[7]视之不见,近而易求:金丹大道视之不可见,听之不可闻,然近而易得,只依法度求之即可。内丹因圣胎有炁而无质,故说“视之不见”;虽视之不见,然近在我身,切近心胸,人所不知,而己独知,故说“近而易求”。外丹则强调铅金、流汞在鼎器之内,变化难测,故说“视之不见”;若以天机运制、法象枢辖,则金、汞不至于逃逸,结成丹宝,故说“近而易求”。
【译文】
北极星为众星之主,北极星正则其下众星皆循自己的运行轨迹优游而行,各得其所。北极星居中不偏,犹如人君处明堂之正,君正则百官各负其责,朝政有条不紊。丹道如政道,黄老之道的治政理念重在清静无为,深根固蒂,丹道亦强调要摒除外在干扰,收心于内,安静、恬淡,炼其汞、铅。汞、铅皆由元精、元炁所化,元精、元炁为万化之本,有炁无质、隐而难见,然神而明之,存乎其人,只要保炁、储精于身内,则窈冥中有精,恍惚中有物。修丹者既安铅、汞灵根于鼎器之中,则须固济、筑塞其鼎口,使不外泄;并运三光之阳火、阴符入于鼎室之内,哺养其中的玄珠、灵胎。金丹大道虽视之不可见、听之不可闻,然若依法度求之,则近而易得。
黄中渐通理章第二十一
【题解】
本章论修丹当知其本,本立则道生。
自外丹言之,修丹之本,即金花、黄芽。金花、黄芽其色皆黄,由铅、汞作成,铅金入于流汞之中,其情通畅;得火温养,日久则化,渐渐成丹。人服丹之后,丹可滋养人之四肢及五脏,润泽并可达于肌肤。炼丹之初,火候得正,则一月、一年之火候,皆可得而知之,终始循环,更相替代。阳为干、阴为支,即铅金与流汞,铅金先唱,流汞后随,铅金与流汞相互扶持,即成真宝。一为水之数,铅、汞得火煅炼之后,即化为水;此水既含铅又含汞,铅中有汞掩蔽;此水勿妄泄,即能成丹,但世人未晓其理罢了。
自内丹言之,中宫黄庭有宝则精炁流通,润泽可达于四肢百骸、肌肤腠理。丹田既初受炁、始生萌芽,则正其枝干,而终成正果,故丹道有始有终、有本有末,但得本,不愁末,原始可以要终,即本可以该末。先天真一之炁分而为阴阳,化而为天、地、人三才,三才既立,而后变化无穷;然先天真一之炁其造端之处、发生之原理,皆隐而不显,难为人所知。
黄中渐通理,润泽达肌肤[1]。初正则终修,干立末可持[2]。一者以掩蔽,世人莫知之[3]。
【注释】
[1]黄中渐通理,润泽达肌肤:中宫黄庭有宝则神化流通,和顺积中则英华外发,人身内黄庭之中的元和真炁渐渐通畅于腠理之间,润泽达于肢体、肌肤。黄,中央之色,所谓“黄中”即黄庭,亦有以“黄中”为“黄婆”,乃炼丹人之真意;或指人之脾胃,其色配黄,脾胃能消化丹药,滋养四肢、五脏并肌肤。理,腠理,即皮肤之间的组织;或谓“理”即炁。此句源出于《周易》坤卦六五爻《文言》:“君子黄中通理,正位居体,美在其中,而畅于四肢,发于事业,美之至也。”取《易》居中、履正之辞,以发明有诸内而形诸外之理。
[2]初正则终修,干立末可持:学道以守正为要、以立志为先,守正则不入曲径旁门,立志则不致始勤终怠。心正而后身修,本立而后道生;既初受气、始生萌芽,能正其枝干,而终成正果,所谓源深则流长。初正、干立,原丹道之始;终修、末持,责丹道之终。丹道有始有终、有本有末,初始为炼己下手之功,终末为入室了手之事,但得本,不愁末,原始可以要终,即本可以该末。修,他本或作“循”。末,他本或作“未”。
[3]一者以掩蔽,世人莫知之:“一”从道而生,为万化造端之始,隐蔽而不彰显,世俗之人很难了解它的情况。《道德经》非常推崇“一”,关于“一”,其谓:“载营魄抱一,能无离乎”(十章);“视之不见名曰夷,听之不闻名曰希,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诘,故混而为一。(一者)其上不皦,其下不昧,绳绳不可名,复归于无物”(十四章);“少则得,多则惑,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”(二十二章);“昔之得一者:天得一以清,地得一以宁,神得一以灵,谷得一以盈,万物得一以生,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”(三十九章);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(四十二章)。《周易·系辞》亦说: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继之者,善也;成之者,性也。仁者见之谓之仁,知者见之谓之知,百姓日用而不知,故君子之道鲜矣。”丹道通常以“一”为先天真一之炁,其分则为阴阳,化而为天、地、人三才,三才既立,而后变化无穷;如能得其一,则万事毕。或谓“一”即道的别名,乃宇宙的本体。以,他本或作“已”。世人,他本或作“俗人”。莫知之,他本或作“莫能知”。
【译文】
人身内黄庭之中的元和真炁渐渐通畅于四肢、百骸,润泽达于肌肤、腠理之间。学道之人以守正为要、以立志为先,守正则不入曲径旁门,立志则不致始勤终怠;丹道有始有终、有本有末,但得本、不愁末,原始可以要终,即本可以该末。“得其一,万事毕”;“一”源自于道,为万化造端之始,隐蔽而不彰显,世俗之人很难了解它的情况。
上德无为章第二十二
【题解】
本章阐明炼丹法象之大纲、神药之指归。
自外丹言之,上德指铅金、流汞所化之水,下德指鼎下之炉火;金水处鼎中,湛然常静,炉下之火则炎而常动。炼丹时,上鼎当要密固,方保药不失;下炉在烹炼中,为提升炉温,亦要采取密闭措施;收宫之时,还要“封炉”,故有“上闭”、“下闭”等措施。因鼎中之金水居上而有体位,故“上闭则称有”;炉火处下而无常形,故“下闭则称无”;炉下无常形之火气炎于鼎上,鼎中之金水则凝结成还丹。在这个过程中,鼎、炉的上、下两个口子起了关键作用,鼎上面口子的开阖主要与金水是否融化、凝结等事宜相关,炉下面口子的开阖则与炉火温度的高低直接相关。上、下两个口子的功能须要配合、相应,上鼎之金水与下炉之火气才能两相调和、顺宜,如此则还丹可成。
自内丹言之,“上德”喻修性,其体本静,无为而不烦智索;“下德”喻修命,其体常动,有为而自强不息。上闭则收视返听,闭塞其兑,此乃有为之功;下闭则潜心于渊默,筑固其灵株,此乃无为之道。上闭则性火交于下,而命水得以生成,故称“有”;下闭则命水升于上,而性火不散,故称“无”。元炁居下、元神居上,元炁用下德以奉上,元神居上德以御下;下德命门之肾水交于上德性中之心火,水制火以奉上,取坎填离,精化炁而有神,故“上有神德居”。元神守于玄宫,默默无为;炁腾于丹田、紫府,绵绵不绝,虚心实腹,虚上实下,则心肾相交,神、炁相抱,故说“相须”。
上德无为,不以察求;下德为之,其用不休[1]。上闭则称有,下闭则称无[2]。无者以奉上,上有神德居[3]。此两孔穴法,金气亦相须[4]。
【注释】
[1]上德无为,不以察求;下德为之,其用不休:上德为水,下德为火;水在上湛然常静,有“无为”而“不以察求”之意;火在下则炎而常动,有“为之”而“其用不休”之意;水上火下,成水火既济,则可由后天坎、离复归先天之乾、坤。当然,历代注家对此句还有多种解释。如有谓上德之人安静虚无,法自然而无为;下德之人功不稍息,其有为之事不休止。或谓上德为修性,其体本静,无为而不烦智索;下德乃修命,其体常动,有为而自强不息。或谓“离”喻心炁而居上,其中玉液可为还丹而有益于人,故称“上德”;“坎”喻肾炁而居下,其中有金液亦可为还丹而有益于人,故称“下德”;玉液还丹,神守于玄宫而默默无为,即“上德无为,不以察求”;金液还丹,气腾于紫府而绵绵不绝,非借假炉灶而修为则不可得,故“下德为之,其用不休”。或借《周易》谦卦之《彖》“天道下济而光明,地道卑而上行”之说,认为下部坤腹、玄关之中生起元阳,从身后尾闾、夹脊、玉枕三关历阶而升,此为坤道之上德,其体本静,静则无为,听其自然,非人力能与,故“不以察求”;上部乾首之元神,注于坤腹、玄关,是为下德,乾道下济,乾体常动,动则有为,人力可以参与其中,无时可休止,故“其用不休”。处无为之时即以无为,在有为之时则用而不休。此句经文源出于《道德经》: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,下德为之而有以为。”(三十八章)“虚其心,实其腹;弱其志,强其骨。”(三章)
[2]上闭则称有,下闭则称无:炼丹有上鼎、下炉,铅金、流汞所化之水居上鼎,火居下炉。炼丹时,上鼎当要密固,方保药不失;下炉在烹炼中,为提升炉温,亦要采取密闭措施而用之;乃至在收宫时,还要采取俗称的“封炉”,故有“上闭”、“下闭”之说。因鼎中之水居上而有体位,故“上闭则称有”;炉火处下而无常形,故“下闭则称无”。或谓上闭则收视返听,闭塞其兑,此乃有为之功;下闭则潜心于渊默,筑固其灵株,此乃无为之道。上闭则性火交于下,而命水得以生成,故称“有”;下闭则命水升于上,而性火不散,故称“无”。或谓元阳升上而闭固,因坤道上行,闭之得有形之水,故称“有”;元神下注而闭固之,乃乾道下济,闭之得无形之火,故称“无”。闭,关闭。
[3]无者以奉上,上有神德居:鼎炉中有金水,得炉火烹炼,火无形而金水有形,故上有、下无;丹道火候运四时、五行之气,以资养神胎中之金水,炼成还丹至宝,此即“无者以奉上,上有神德居”。或谓元炁居下、元神居上,元炁用下德以奉上,元神居上德以御下;下德命门之肾水制上德性中之心火,水制火以奉上,取坎填离,精化炁而有神。
[4]此两孔穴法,金气亦相须:鼎、炉有上、下两个口子,鼎上面口子的开阖主要与金水是否融化、凝结等事宜相关,炉下面口子的开阖则与炉火温度的高低直接相关。鼎中金、汞得火气相蒸、历历有声,如龙吟、虎啸;铅、汞在鼎内,混融、相须,上、下两个口子的功能须要配合、相应,水火之气才能两相调和、顺宜,如此则还丹可成。穴,他本或作“窍”。金气,他本或作“吟气”、“有无”。须,他本或作“胥”。
【译文】
上德为水,下德为火;水在上,湛然常静,有“无为”而“不以察求”之意;火在下,则炎而常动,有“为之”而“其用不休”之意。炼丹有上鼎、下炉,铅金、流汞所化之水居上鼎,火居下炉,炼丹时上鼎要密固,方保药不失;下炉在烹炼中,为提升炉温,亦要采取密闭措施而用之,在收宫时还要“封炉”;鼎中之水居上而有体位,故“上闭则称有”;炉火处下而无常形,故“下闭则称无”。炉火虽无常形,却能烹炼、资养上鼎中之金水,炼之使成还丹至宝。鼎、炉有上、下两个口子,鼎上面口子的开阖与金水是否融化、凝结等事宜相关,炉下面口子的开阖则与炉火温度的高低直接相关。鼎中金、汞得炉下火气相蒸、历历有声,如龙吟、虎啸;铅、汞在鼎内,混融、相须,故上鼎、下炉两个口子的功能须要配合、相应,上鼎之金水与下炉之火气才能两相调和、顺宜,如此则还丹可成。
知白守黑章第二十三
【题解】
本章直指“水中之金”乃丹道之母。
自外丹言之,铅色黑,汞色白,铅、汞得火炼制,化而成水,中含金精、黄芽,故“神明自来”。五行之中,水数为一,水能变化,乃丹道之母,故铅、汞所化之水为道之枢机。铅、汞初交,得火而融,即是阴阳之始,所化水中有黄芽、金精,此则为“玄含黄芽”。铅为五金之主,总持鼎中金水之变化;五行中,水居北方,金水在鼎中沸腾,上下左右轮转,故为“北方河车”。铅虽外黑,内有金华之象,其未融化之前,金精混于矿石之内,以黄杂于黑,呈黄褐之色,故称“被褐”;铅质虽贱,而金精在内,故称“怀玉”;铅外貌虽黑而内藏金华,其至宝暗藏于身内,犹如人怀藏金玉于其身内,外边则穿着褐色破旧的外衣而佯装癫狂。
自内丹言之,其以“金”比喻先天真炁,“水”喻为精;白为金之色,黑为水之色;真炁化而为精,此乃五行顺生之金生水,为“顺则生人”之道;水本为金所生,乃金之子,如果能炼精化炁,以水为基础而求取水中之金精,此即为五行返生,乃“逆则成仙”之路。所以,精虽由炁而化,亦可逆而炼精化炁,此即为“知白守黑”,欲知白当守其黑,守黑则白自现;知水中有金,守其水则金自至。守之之法,即如猫之守窟以待鼠至,身不动而目不瞬,此心唯在于鼠,更无他念,如此则心虚而神凝,神凝而息定,息定则产药而神明自来。如以汉易五行生成之数论之,则天一生水,居五行之始;水一加土五,得水之成数六,土为真意,寂静而真意生,水色玄而土色黄,故有“玄含黄芽”之象;水中产铅金,铅金为五金之主,产在北方玄冥之水内,得土而生黄芽,黄芽即金华,乃铅之精英。水本居北,搬运而南,使坎水自下丹田升上,与居上之离火交媾;在人身而言,即元阳真炁即产之后,当自下丹田搬运至于上宫泥丸,元阳真炁自下载宝而上,如河边抽水灌溉的翻车之运水,故称“河车”。故铅体外黑而金华隐于其中,犹如至宝藏于褐夫之怀。
知白守黑,神明自来。白者金精,黑者水基[1]。水者道枢,其数名一[2]。阴阳之始,玄含黄芽[3]。五金之主,北方河车[4]。故铅外黑,内怀金华;被褐怀玉,外为狂夫[5]。
【注释】
[1]知白守黑,神明自来。白者金精,黑者水基:“白”喻水银,即汞,“黑”喻铅,炼水银于黑铅之中,铅与汞相守以为药基,则神精自生于鼎器之中。白为金之色,黑为水之色,白色代表金之精华,黑色代表水之根基。金精为汞,白属西方金之色,故说“白者金精”;铅金为黑,黑属北方水之色,故称“黑者水基”,此是一种解释。或谓金精是汞融入铅中后所吐黄芽之花,称为“金精”,亦名“玄黄花”,亦名“金花”,而黑铅实乃为金花之根基。中国古代五行配五色,具体为木配东方青色,火配南方赤色,金配西方白色,水配北方黑色,土配中央黄色。五行顺生为水生木、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、金生水,五行相克为水克火、火克金、金克木、木克土、土克水。道家内丹之法有“顺则生人,逆则成仙”之说,其以“金”比喻先天真炁,“水”喻为精,真炁化而为精,此乃五行顺生之金生水,为“顺则生人”之道;水本为金所生、乃金之子,如果能炼精化炁,以水为基础而求取水中之金精,此即为五行返生,乃“逆则成仙”之路。所以,知水中有金,守其水则金自至,好比“金生丽水”,若想“淘金”,须到水中去淘,方能得之,故要想“知白”,当守其“黑”,守黑则白自现。内丹“知白守黑”之法,即如猫之守窟以待鼠至,身不动而目不瞬,此心唯在于鼠,更无他念,如此则心虚而神凝,神凝而息定,息定则产药而神明自来。神明,即天机。《周易·说卦》说:“神也者,妙万物而为言者也。”物之极妙,如神降之不知来迹,欲知天机,必先虚其心。此句源出于《道德经》:“知其白,守其黑,为天下式。为天下式,常德不忒,复归于无极。”(二十八章)
[2]水者道枢,其数名一:铅、汞处鼎中,得炉下之火烹炼,融而化为水,此水含铅、汞之精华,实乃为丹道之枢纽。水之生数为一,合于经文“一者以掩蔽,世人莫知之”之意,也合于《道德经》“道生一”之旨,故“一”为五行之初,道之枢机。汉易将五行与天地之数相配,天地之数即《周易·系辞》所谓:“天一、地二;天三、地四;天五、地六;天七、地八;天九、地十。”“天数五,地数五,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天数二十有五,地数三十,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,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。”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为奇阳之天数,其数相加为二十五;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为偶阴之地数,其数相加为三十。自一加至十,得五十五,此为天地之数。五行与天地之数相配,则天一生水、地六成之;地二生火,天七成之;天三生木,地八成之;地四生金,天九成之;天五生土,地十成之。故水之生数,其数名一;五行从“天一生水”开始,水一、火二、木三、金四、土五,水数之一乃天地、阴阳、五行、万物之始,故说“水者道枢”。
[3]阴阳之始,玄含黄芽:天一生水,水居五行之首。丹道中,铅、汞初交,化而为水,即是丹道阴阳之始,乃丹道之枢纽;水色黑而金色黄,铅、汞融化为水,水又结晶成金精,丹道以之为“黄芽”,故有“玄含黄芽”之象。或谓水数一加中央土数五,得水之成数六,水其色玄黑,土其色黄,亦有“玄含黄芽”之象。
[4]五金之主,北方河车:铅为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等五金之主,凡熔五金,必得铅而后凝;五金熔则化为金水,铅入金水中,主宰金水在鼎中上下左右循环轮转、沸腾,有如在河边车水灌溉农田的翻车,故称“河车”;又五行中,水居北方,故称“北方河车”。或谓五金乃借外炼之银、铅、砂、汞、土,以喻人身中的五行之精;或谓“北方河车”即北斗,北斗为“帝车”,载北辰紫微太一之神巡游天河,因其随天河而轮转,故称“河车”,丹道借“河车”以喻金精、黄芽生于水中,得火煅炼,出而循环轮转。
[5]故铅外黑,内怀金华;被褐怀玉,外为狂夫:金华乃铅之精英,铅虽外黑,内有金华隐于其中;犹如人怀藏金玉于其身内,外边则穿着褐色破旧的外衣而佯装癫狂。《道德经》有言:“我愚人之心也哉!沌沌兮!众人昭昭,我独昏昏;众人察察,我独闷闷……众人皆有以,而我独顽似鄙。我独异于人,而贵食母。”(二十章)铅未熔化之前,其金精混于矿石之内,以黄杂于黑,为黄褐之色,故称“被褐”;铅质虽贱,而金精在内,故称“怀玉”;外貌黑而内藏金华,至宝暗藏于中,犹如被褐怀玉之狂夫。以贱护贵,以晦养明,以卑保尊,以狂养圣,虽外视好像癫狂之人,却内怀至宝,机缄不露。
【译文】
白喻水银,即汞,黑喻铅,炼水银于黑铅之中,铅与汞相守以为药基,则神精自生于鼎器之中。以五行配五色,则白为金之色,黑为水之色,白色代表金之精华,黑色代表水之根基。铅、汞处鼎中,得炉下之火烹炼,熔而化为水,此水含铅、汞之精华,实乃为丹道之枢纽。水之生数为一,合于经文“一者以掩蔽,世人莫知之”之意,也合于《道德经》“道生一”之旨,故“一”为五行之始、道之枢机。铅、汞熔化为水,水又结晶成金精,水色玄而金精色黄,故有“玄含黄芽”之象。铅为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等五金之主,凡熔五金,必得铅而后凝;五金熔则化为金水,铅入金水中,主宰金水在鼎中上下左右循环轮转、沸腾,有如河边车水灌溉农田的翻车,故称“河车”;又五行中,水居北方,故称“北方河车”。金花、黄芽乃铅之精英,铅虽外黑,内有金花、黄芽之质隐于其中,犹如人怀藏金玉于其身内,外边则穿着褐色破旧的外衣而佯装癫狂一样。
金为水母章第二十四
【题解】
本章分别阐明丹道金、水两体之用,以明金、水同源。
丹道所谓铅、砂、银、汞、土,乃外丹之事;精、神、魂、魄、意,乃内丹之事。《周易参同契》中,这两者经常交互言之,因其理相用,虽多用隐喻、玄言,如能得其要旨,则可晓其大略。
自外丹言之,铅、汞处鼎中,得火而熔化为金水,铅、汞乃此金水之母,金水中涵藏铅、汞之金精、黄芽,故“母隐子胎”。金水未产之时,常隐于铅、汞胞胎之中,此则为“子藏母胞”。金精、黄芽处铅、汞所熔化之水中,即是真人在渊内;金精、黄芽被炉下文、武之火烹炼,在铅、汞所熔化之水中,上下沉浮,翻滚不定;虽有丹之象、未成丹之形,故或现或隐,若有若无。汞入铅汁之中,分散退布于铅汁之内,为铅所拘守;铅沉汞浮,不得越出其所处之位。
自内丹言之,肾中元阳先天真一之炁为金,元阳先天真一之炁能生肾水之精,故为肾水之母,而肾水为其子;元阳先天真一之炁隐于肾水之中而为胎,肾水之中即藏有其母之胞。内丹所谓求取“水中金”,即指炼精以化其炁,也指知白以守其黑、守子以存其母。“真人”喻指“元神”,自其妙而观之,则以其为有;然其体本一无,又似为无,故“若有若无”。“仿佛大渊,乍沉乍浮”,指元神之炁虽寂然不动,却又感而遂通。元神或先天元阳真一之炁,虽至无而含至有、至虚而含至实,化而为阴阳五行之气,无不具备;存神聚炁,则精、神、魂、魄、意,各安其所守。
金为水母,母隐子胎,水者金子,子藏母胞[1]。真人至妙,若有若无。仿佛大渊,乍沉乍浮[2]。退而分布,各守境隅[3]。
【注释】
[1]金为水母,母隐子胎,水者金子,子藏母胞:铅、汞处鼎中,得火而熔化为金水,铅、汞乃此金水之母,金水中涵藏铅、汞之金精、黄芽,故“母隐子胎”。金水为铅、汞熔化而成,无铅、汞之金则不能产此金水,此则为“子藏母胞”。内丹法以肾中元阳先天真一之炁为金,元阳先天真一之炁能生肾水之精,故为肾水之母,而肾水为其子;元阳先天真一之炁隐于肾水之中而为胎,肾水之中即藏有其母之胞,内丹所谓求取“水中金”,即指炼精以化其炁,知白以守其黑、守子以存其母。五行关系中,金生水,故金乃为水母;金本生水,现在金反而隐形于水,此则为母隐于子胎;水为金之子,推原水之所来,则源于金,此乃子藏母胞。隐,他本或作“藏”。
[2]真人至妙,若有若无。仿佛大渊,乍沉乍浮:金精、黄芽处铅、汞所熔化之水中,即是真人在渊内;金精、黄芽被炉下文、武之火烹炼,在铅、汞所熔化之水中,上下沉浮,翻滚不定;虽有丹之象、未成丹之形,故或现或隐,若有若无。大渊,指鼎器之中,烊铅成汁。投汞入于铅汁,汞入铅中,沉浮不定,是炼制黄芽、金花之法。内丹法则以“真人”喻指元神或元阳先天真一之炁,自其妙而观之,则以其为有;然其体本一无,又似为无,故“若有若无”。仿佛大渊,乍沉乍浮,指元神或元阳先天真一之炁虽寂然不动,却又感而遂通。
[3]退而分布,各守境隅:汞入铅汁之中,分散退布于铅汁之内,为铅所拘守;铅沉汞浮,不得越出其所处之位。或谓鼎中之药应炉外文、武符火之进退,各守其界分,不敢越雷池半步。内丹法则认为,元神或先天元阳真一之炁,虽至无而含至有、至虚而含至实,化而为阴阳五行之气,无不具备;存神聚炁,则精、神、魂、魄、意,各安其所守。退,他本或作“进”。
【译文】
铅、汞处鼎中,得火而熔化为金水,铅、汞乃此金水之母,金水中涵藏铅、汞分子、元素,故说母隐于子胎;金水未产之时,隐藏于铅、汞的胞胎之中,此则为“子藏母胞”。鼎器之中,烊铅成汁,犹如大湖泊;投汞入于铅汁,汞入铅中,相互作用,生成金精、黄芽;金精、黄芽处铅、汞所熔化之水中,被炉下文、武之火烹炼,在鼎中上下沉浮、翻滚不定,虽有丹之象、未成丹之形,故或现或隐,若有若无。汞入铅汁之后,为铅所拘守,分散退布于铅汁之内;铅沉汞浮,各自不能越出其所处之位。
采之类白章第二十五
【题解】
本章明鼎中丹已经成象,贵在护养;并从形上学的角度,以之为丹道先天之本元。
自外丹言之,烊铅成汁、入汞造作,其色由白变而为朱赤。铅为表卫,汞入内被铅所裹,不得逃逸,故居其所正。汞入铅中,混杂相融,于鼎炉中煅造,成方圆一寸之丹。鼎在太一炉中、三台之上,铅、汞入其内,得成还丹,故鼎在丹道中非常重要,被视为丹道中至尊、至高之物。
自内丹言之,修行之人于静定之中,虚室生白,丹药凝结,此为“采之类白”;既而运心神之火以哺育、培养之,使丹基坚固,此为“造之则朱”。久之则神凝炁聚、神炁相抱,混然中处,有表有里;精、炁与神交媾于方圆径寸的丹田之中,固济绵密,如果阴阳火符纤微不差,则丹宝得以养成。丹宝乃神炁混合之灵妙真有,究其本则为先天地生的阴阳之根、造化之本,故崇高伟大!
采之类白,造之则朱[1]。炼之表卫,白里贞居[2]。方圆径寸,混而相拘[3]。先天地生,巍巍尊高[4]!
【注释】
[1]采之类白,造之则朱:煅制丹药,有不同的程序:烊铅成汁、入汞造作,于其中采取金精、黄芽,以之为大丹之基,初时其色为白,此为“采之类白”;得赫火煅制、陶冶,丹药之色渐渐变如朱赤之色,此为“造之则朱”。或谓采金于水、炼银于铅,制铅化白而成胡粉,故说“采之类白”;采铅为母、炼金为丹,造铅变赤而成黄丹,故说“造之则朱”。以内丹言之,修行之人于静定之中,虚室生白,丹药凝结,此为“采之类白”;既而运心神之火以哺育、培养之,使丹基坚固,此为“造之则朱”。采,他本或作“望”。
[2]炼之表卫,白里贞居:鼎中有丹药,须得外炉之火昼夜炼养,然后成熟;文、武之火运于外炉,此为“炼之表卫”。煅造之后,铅为表卫,汞处铅内、为铅所裹,不得飞走,其象犹如鸡蛋一般,蛋白之里有蛋黄混沌居中,此为“白里贞居”。或谓“白”喻丹药之金、居内以为贞,而离火为表卫、炼之于外;火运于外,丹药安处于鼎内,此为“白里贞居”。内丹则认为,神凝炁聚、神炁相抱,有混然中处者、亦有炼之表卫者,如俗话所说的“内练精、炁、神,外练筋、骨、皮”。炼,陶冶。表,外表之意。贞,《周易》以六爻别卦之内卦为贞、外卦为悔,故“贞”有“内”、“里”之意;或谓“贞”有“正”之意,“居贞”即“居正”,共成正道之意。炼之表卫,他本或作“铅为表卫”、“炼为表卫”。白里贞居,他本或作“帛里贞居”。
[3]方圆径寸,混而相拘:铅、汞在鼎中,得炉外文、武之火烹炼,乃混沌而相和合,变化成方圆径寸之丹,“方圆径寸”喻指金丹之法象。内丹中,或以“方圆径寸”喻人身之丹田,此句的意思是精、炁与神交媾于方圆径寸的丹田之中,固济绵密,使阴阳火符纤微不差,以养丹基;当然,还有以“方圆径寸”喻泥丸宫、喻心等多种不同解释。拘,他本或作“扶”。
[4]先天地生,巍巍尊高:丹道强调要采先天地之炁为丹药之基,聚阴阳纯粹之精为还丹之质;其既生于天地之先,故巍巍尊高不可思议!内丹以“先天地生”喻指元阳真一之炁,其为天地之根、阴阳之母;或谓泥丸穴乃一身众窍之祖窍,此窍开则众窍齐开,又泥丸宫在人之首,乃元神所居之位,道教以之上应玄都玉京万神会集之乡,故其为“先天地生,巍巍尊高”。外丹则通常以“先天地生”喻鼎器;“天、地”喻铅、汞之药,先立其鼎器,然后注入铅、汞药物,故鼎器称“先天地生”;鼎器高出于炉之上,故称“尊高”。此句源于《道德经》:“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,寂兮寥兮,独立而不改,周行而不殆,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,字之曰道,强为之名曰大。”(二十五章)巍巍,高大之貌。
【译文】
烊铅成汁、入汞造作,于其中采取金精、黄芽,以之为大丹之基,初时其色为白;得赫火煅制、陶冶,其色渐渐变如朱赤。鼎中丹药,须得外炉之火昼夜炼养,然后成熟;丹成之后,铅为表卫,汞处铅内、为铅所裹,不得飞走,其象犹如鸡蛋的蛋白裹有蛋黄一般。铅、汞在鼎中,得炉外文、武之火烹炼,乃混沌而相和合,变化成方圆一寸左右的金丹。构成此金丹的基本元素先天地而有,乃天地、阴阳造化之本元,故其巍巍尊高不可思议!
旁有垣阙章第二十六
【题解】
本章言丹鼎神室及火候之妙用。
自外丹言之,坛、灶之状犹如墙垣、门阙,炉、鼎相接有如山形,故将之比喻为蓬莱、方壶之神山。铅、汞等药安置于鼎炉中之神室,其外周匝如环、轮转相通,象楼阁之曲折。炼丹时要固塞鼎、炉之际会,务使坚完、牢密,无纤微之缝隙,则丹不走失。丹道成功与否,重在其火候,如果能识文、武火候之妙理,则无思而成;失其理,则忧愁劳苦且无益。如果鼎下炉火过盛,则药物如流汞等滑利而易于奔逸,去之无踪,寻之无所。所以,炼丹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在于燮调文、武火候,不可有须臾差忒;守此火候而不失,则丹道可成。炼丹时,反覆鼎器及进退文、武之火,其动静休息,常须有人看守,故丹道火候动静、休息,取舍虽非由人自专,亦不能离开人的具体因循、操作。
自内丹言之,泥丸宫位于人身之头顶,元神居于其中;眼、耳、鼻、目等七窍皆旁列于其外,前则有洞房、黄阙等穴,其状如海上蓬莱、方壶之仙山,周旋而四通。修行人收视返听、深根固蒂、闭塞其兑,令内者不出,则身体内元和真炁内运,周流通达。当然,也要摒除各种外在干扰,任由各种魔境相侵,而不为所动。人身之灵窍、脉络相通,本无隔碍,然必防微杜渐、固密防护,方可得神炁满室,又须调运阴阳之火交互施功,使神炁不泄而成变化。炼内丹可以无思,不可以愁劳,心无为则神炁和,神炁和则丹宝结;心有为则神炁乱,神炁乱则英华散。真功累积既久,则周身神炁太和充溢,此时,如果运火符有所差忒,纵有真宝在内,亦可能飞走而不住。正因为神炁充盈,至难保护,所以动静休息之时,常须谨守,必须时时相顾、刻刻相守,神炁常与人相伴不离,如此则形神皆妙。故炼丹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夫在于燮调文、武火候,不可有须臾差忒,守此火候而不失,则丹道可成。
旁有垣阙,状似蓬壶[1]。环匝关闭,四通踟蹰[2]。守御密固,阏绝奸邪[3]。曲阁相通,以戒不虞[4]。可以无思,难以愁劳[5]。神气满室,莫之能留[6]。守之者昌,失之者亡[7]。动静休息,常与人俱[8]。
【注释】
[1]旁有垣阙(yuán què),状似蓬壶:炼丹先要准备坛、灶、鼎、炉。垒土为坛、灶,其状如墙垣、城门之阙;鼎、炉与坛、灶上下相接,鼎炉居上、居中,而坛、灶居下,环护其四周,有如仙山蓬莱、方壶、瀛洲之形状,或如酒壶之形状,所以比喻其为“蓬壶”。垣,城墙。阙,古代皇宫大门前两边供瞭望的楼;或者神庙前竖立的石雕,或谓即门阙,明炼丹之鼎的四方上下、环护启闭,如有墙垣以护卫其外,有门阙以通达其内。一说,“垣阙”即垣墙,喻炼外丹所用的“太一炉”,其炉有四正面、四隅面,每面各开一门,故有八门,以通八方来风;其上安有十二个突与窟,象征一天之十二时辰;太一炉上下有四层,应一年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;所谓“壶”,即炼丹之鼎,形状有瓜形、方形等,但皆似酒壶之状,其鼎边安有鼎耳,方便取、拿;“蓬”则是炉,炉按五岳之形建造,形似传说中的海中仙山。内丹则认为,此句经文主要叙说上丹田,其位在人身之头顶,有时亦将之隐喻为泥丸宫,元神居于其中;泥丸宫居人身之头顶,眼、耳、鼻、目等七窍皆旁列于其外,泥丸宫前还有洞房、黄阙等穴,犹如海上有三神山,而蓬莱居三山之上,如蓬壶之状,周旋四通;内丹以此喻神室之中、金丹法象圆融,如蓬壶那样美丽,外有河车金轮环转、护卫,如墙阙之周遮。或谓“垣阙”指人肾部之宫。
[2]环匝关闭,四通踟蹰(chí chú):鼎器之外,炉灶周匝如环,如银山铁壁之坚密;鼎器之中,复有神室金胎,委曲相连,如琼楼、玉阁四通八达,铅、汞则居于内,封固深藏而踟蹰不出。内丹则认为,“环匝关闭”指收视返听、深根固蒂、闭塞其兑,令内者不出;“四通踟蹰”指元和真炁内运,周流通达。或谓“环匝”指鼎的四耳,或二耳。环,圆圈之形,圆成无缺。匝,环绕,周回,周遍。踟蹰,心里迟疑,要走不走的样子,行而不进之貌。
[3]守御密固,阏(è)绝奸邪:鼎器之外,还有各种装置、设施起固济、防护的作用,同时还要观察火候,昼夜不得倦怠,以防药物走失。守御,观察火候,昼夜不得倦怠。密固,坚固。炼丹若鼎炉不牢密,则药物将走失殆尽。阏绝奸邪,指固济牢密,药物即无败邪、亏失。内丹则认为,修丹当收视返听,摒除各种干扰、守御密固,使精神内守、神炁相依,勿使其须臾相离,如骊龙养珠,心念念不忘;又如母鸡孵卵,热气不绝。阏绝奸邪,指任由各种魔境相侵,而不为所动。阏,堵塞、止之意。奸邪,指内外魔障,以及火候进退差殊之失等炼丹事故。
[4]曲阁相通,以戒不虞(yú):炉处外而鼎处中,周匝如环,像曲曲折折的楼阁一般迂回、相通;固塞鼎、炉之际会,使无纤微之缝隙,务使坚完,贵其牢密。内丹则认为,灵窍、脉络相通,本无隔碍,然必防微杜渐、固密防护可得神炁满室,又须调运阴阳之火交互施功,使神炁不泄而成变化。或谓“曲阁”为尾闾关,与“垣阙”即人肾部之宫相通连,“以戒不虞”指防止睡梦当中而或泄之。虞,预料,忧虑,或谓“失”之意。《周易·屯》六三爻辞:“既鹿无虞,惟入于林中,君子几不如舍,往吝。”此“虞”则是古代为贵族掌管山林、鸟兽的小官,在贵族行猎时,其负责驱出鸟兽,故“虞”也可有“向导”之意。
[5]可以无思,难以愁劳:识丹道之妙理,则无为而成;不识丹道之根本,妄自为之,虽忧愁且无益。炼丹之火候,刚柔相济,一动一静,一休一息,有其常道,文、武之火运用适宜,则无须多思,故当弃有为而入于无为。内丹则认为,心无为则神炁和,神炁和则丹宝结;心有为则神炁乱,神炁乱则英华散,故炼内丹可以无思,不可以愁劳。或谓前文提及要警戒不虞,恐作丹者因此而过于畏慎、以勤劳自苦,此句则以“可以无思”慰藉之。
[6]神气满室,莫之能留:鼎下炉火过盛,则药物如流汞等滑利而易于奔逸,去之无踪,寻之无所,故须如前文所说:鼎炉要固济牢固,无穿孔、损坏。内丹则认为,神炁充盈,至难保护。真功累积既久,则周身神炁太和充溢,此时,如果运火符有所差忒,纵有真宝在内,亦可能飞走而不住。故要保持太和,动静休息之时,常须谨守,此时一念动则可能神炁随之,犹如端持盈满之器,稍有不平则可能倾覆。此句源于《道德经》:“金玉满堂,莫之能守。富贵而骄,自遗其咎。”(九章)神气,外丹指火,内丹指丹宝。满,指武火太过于盛满。室,外丹指炉,内丹指丹田神室。室,他本或作“堂”。
[7]守之者昌,失之者亡:炼丹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在于燮调文、武火候,不可有须臾差忒,火气均调,勤心不怠,守此火候而不失,则丹道可成。
[8]动静休息,常与人俱:炼丹时,反覆鼎器及进退文、武之火,其动静休息,常须有人看守。故丹道火候一动一静、一休一息,期间之取舍,虽非由人自专,然循火候进退而不失,亦不能离开人的具体因循、操作。内丹则认为,神炁处丹田之中,必须时时相顾、刻刻相守,动静休息之间,神炁常与人相伴不离,如此则形神皆妙。
【译文】
炼丹的炉、鼎之外为坛、灶,坛、灶之状犹如墙垣、门阙,而炉、鼎相接则有如蓬莱、方壶、瀛洲之神山。铅、汞等药安置于鼎炉中之神室,其外周匝如环,务使坚完、牢密;其内则四通八达,轮转迂回。炼丹时要固塞鼎、炉之际会,使之无纤微之缝隙,则丹不走失;同时谨守文、武火候,防止因火候进退差殊之失而酿成炼丹事故。丹鼎如楼阁曲折而相通,必使坛精严,以戒不虞之患。如果修丹者熟知丹道之妙理,则可无思而成;如失其理,则难上加难,虽忧愁劳苦亦且无益。神室、金胎中神炁洋溢充盈,但易于奔逸,去之无踪,寻之无所;若能谨护、持守则胎全、丹熟而昌,如若失之则炁散神飞而亡。丹道火候之动静、休息,其取舍虽非由人自专,然亦不能离开人的具体因循、操作。
是非历藏法章第二十七
【题解】
本章言金丹之道与诸旁门小法有本质之不同。通过历举主要的旁门小法,明其纵然有小成,终亦不免失败;唯金液还丹之道,方可达大道之宗元,从而使后学知有所戒。
是非历藏法,内视有所思[1];履行步斗宿,六甲以日辰[2];阴道厌九一,浊乱弄元胞[3];食气鸣肠胃,吐正吸外邪[4];昼夜不卧寐,晦朔未尝休;身体日疲倦,恍惚状若痴[5];百脉鼎沸驰,不得清澄居[6]。累土立坛宇,朝暮敬祭祠;鬼物见形象,梦寐感慨之[7]。心欢意悦喜,自谓必延期;遽以夭命死,腐露其形骸[8]。举措辄有违,悖逆失枢机[9]。诸述甚众多,千条有万余;前却违黄老,曲折戾九都[10]。
【注释】
[1]是非历藏法,内视有所思:金丹之道,乃上圣登真之梯筏,非各种旁门左道之所能及。旁门左道中,有闭目内视,存想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五脏之精光的内思小伎,其法通过内视五脏而存思其精光而得名。是,此指金丹大道。非,不是。历,遍及,一个一个依次及之之意。藏,同“脏”,指人身体内之五脏六腑。内视,内观之意。思,存想之意。
[2]履行步斗宿,六甲以日辰:行禹步而履斗、踏罡,以取星宿之气;按日辰而祭六甲之神、服六甲之符,以吞日月之光。《周易参同契》认为,此非金丹之道。履行,步、踏之意。斗宿,指北斗、二十八星宿等众星。六甲,具体指甲子、甲寅、甲辰、甲午、甲申、甲戌。古代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依次相配以计时,如天干甲与地支子相配则为甲子,天干乙与地支丑相配则为乙丑,如此依次相配,从甲子至于癸亥共有六十组,因其以甲子为其首,俗称“六十甲子”。“六十甲子”毕,则又开始下一轮天干与地支相配的循环。“六十甲子”中,一共有“六甲”。履行步斗宿,他本或作“履斗步罡宿”。六甲以日辰,他本或作“六甲次日辰”。
[3]阴道厌九一,浊乱弄元胞:至于对境接气、行房中之术者,满足于九浅一深,以之为采阴补阳之火候;或服食婴儿胞胎之衣,以之为养生之法,秽浊迷乱而不自知。厌,满足;或谓“服”之意。元胞,即婴儿胞衣、胎盘,因其多血,其色为紫,亦有“紫河车”之称。九一,他本或作“一九”。
[4]食气鸣肠胃,吐正吸外邪:忍饥食气,吐身中之正,吸身外之邪,常使肠、胃空鸣。食气,吞服外气之意。正,身中之正炁。外邪,身外之邪气。外邪,他本或作“所邪”、“新邪”。
[5]昼夜不卧寐,晦朔未尝休;身体日疲倦,恍惚状若痴:常坐不卧,昼夜不寐,晦朔无休,身体日疲,精神恍惚,故此炁乱神疲,魂伤魄瘁,若痴若呆。晦朔,他本或作“阳鸣”、“肠鸣”。日,他本或作“既”、“以”。
[6]百脉鼎沸驰,不得清澄居:周身百脉之炁散驰奔逸,无一刻能清净其心、澄澈其神。
[7]累土立坛宇,朝暮敬祭祠;鬼物见形象,梦寐感慨之:累土立坛,祭祀淫鬼;朝祠、暮祭,期于遇道。或者,感梦、祈神,致使鬼气传于精魂,邪风起于心室,精神迷乱,梦与鬼怪、妖魅相遇而见其形声,遂感慨而欢悦,不知乃妄想心成,却自以为得道。累土,他本或作“累垣”、“周回”。
[8]心欢意悦喜,自谓必延期;遽(jù)以夭命死,腐露其形骸:学人不明金丹大道,却固执旁门小术以为正道,且为此而心欢喜悦,自认为得此必定可以延年益寿;然而却中道夭亡,折其天年,不免于形骸腐坏。期,寿年,寿命。遽,于是,就。心欢意悦喜,他本或作“心欢意喜悦”。
[9]举措辄有违,悖逆失枢机:因其操持悖理、谬误,不得丹道之枢机、秘法,有违于金丹正道。举措辄有违,他本或作“举错辄有为”。
[10]诸述甚众多,千条有万余;前却违黄老,曲折戾(lì)九都:各种旁门左道之法甚多,成千上万而不可胜计。其举措乖讹,皆违背黄帝清静之旨,失却老子《道德》之意,曲折而难通大道,若执迷不悟,其获罪愆乃势所必然。前却,前,乃进之意,却,乃退之意,“前却”即进退,明旁门左道进退皆有违于黄老之旨。戾,罪愆,罪过,乖张。九都,诸注或以之为“九幽”、“丰都”;或笼统将之解释为道教的九都之府、九真之法、九教丹经等。陈撄宁先生提出,《道藏》清字号《张真人金石灵砂论》之《黑铅篇》曾引《九都丹经》语,则《九都》乃古丹经之名。
【译文】
金丹之道,非各种旁门左道之所能及。旁门左道中,有闭目内视,存想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五脏之精光的内思小伎;或者行禹步而履斗、踏罡,以取星宿之气,按日辰而祭六甲之神、服六甲之符,以吞日月之光;或者对境接气、行房中之术者,满足于九浅一深,以之为采阴补阳之火候,服食胞胎之衣,以之为养生之法,秽浊迷乱而不自知;或者忍饥食气,吐身中之正,吸身外之邪,常使肠、胃空鸣者;还有常坐不卧,昼夜不寐,晦朔无休;身体日疲,精神恍惚,炁乱神疲,魂伤魄瘁,若痴若呆者;其周身百脉之炁散驰奔逸,无一刻能清净其心、澄澈其神。至于累土立坛,祭祀淫鬼,朝祠、暮祭,期于遇道;或者感梦、祈神,精神迷乱,梦与鬼怪、妖魅相遇而见其形声,遂感慨而欢欣,不知此乃妄想心成。学人不明金丹大道,却固执各种旁门小术以为正道,且为此而心欢喜悦,自认为得此必定可以延年益寿;然而却中道夭亡,折其天年,不免于形骸腐坏。因其操持悖理、谬误,不得丹道之枢机、秘法,有违于金丹正道。各种旁门左道之法甚多,成千上万、不可胜计;其举措乖讹,皆违背黄帝“清静”之旨,失却老子《道德》之意,曲折而难通丹经所述之大道,若执迷不悟,其获罪愆乃势所必然。
明者省厥旨章第二十八
【题解】
本章言成道之事。学者能参悟《周易参同契》书中之理,用心以明之,则金丹之旨无出于此;丹成后,可以成仙,得逍遥之游。
明者省厥旨,旷然知所由[1]。勤而行之,夙夜不休[2]。服食三载,轻举远游[3]。跨火不焦,入水不濡[4]。能存能亡,长乐无忧[5]。道成德就,潜伏俟时[6]。太一乃召,移居中洲[7]。功满上升,膺箓受图[8]。
【注释】
[1]明者省厥(jué)旨,旷然知所由:好道之士如能省察、探究《周易参同契》中的金丹之旨,并能因言而会意,则自能知所以修道之由,从而豁然贯通、旷然洞晓金丹之理。厥,此处作指示代词用,为“他的”之意;另还可作副词,其意为“乃”、“才”。
[2]勤而行之,夙(sù)夜不休:既知晓金丹大道之理,则须夙夜勤修,终始勿怠。因为修金液大丹与旁门小安乐法不同,必当谢绝人事,专心致志,夜以继日,勤而行之,乃能成功。即所谓淡泊名利,撤声色,去嗜欲,投灵山,结仙友,隐密潜修,昼夜无怠,方可希望成功。夙,早。
[3]服食三载,轻举远游:丹药炼成之后,服食三年,则可轻举飞身、远游至于四面八方,变化灵通,逍遥自在。服食,他本或作“经营”、“伏食”。
[4]跨火不焦,入水不濡(rú):道成之后,法身恒存,历水、火而无碍。此句意承《庄子·逍遥游》:“大浸稽天而不溺,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热。”濡,沾湿。
[5]能存能亡,长乐无忧:聚则成形,散则成炁,存亡由己,千变万化,精神长乐无忧。
[6]道成德就,潜伏俟(sì)时:道成德就之后,不能独善其身,更当潜遁世间,暗施阴德,功济群品,以开度众迷,接引后学,积功累德,待时而仙。道门中有语:“功满三千,大罗为仙;功满八百,大罗为客。”“大罗”指“大罗天”,乃道教最高层次之仙境。
[7]太一乃召,移居中洲:天上的太一尊神将见召,从此便可以移居“中洲”等仙境。太一,乃天上之尊神。中洲,道教众仙宫、神州之一。
[8]功满上升,膺箓受图:修丹者功德既圆满,镂名于金简之上,膺受道门之图箓,方能获得升为上仙之机会。膺,他本或作“应”。
【译文】
好道之士如能省察、探究《周易参同契》中的金丹之旨,并能因言而会意,则自能知所以修道之由,从而豁然贯通、旷然洞晓金丹之理。既知晓金丹大道之理,则须夙夜勤修,终始勿怠,方可望丹药成就。丹药既成,服食三年,则可轻举飞身、远游至于四面八方,变化灵通,逍遥自在。服丹药而成道,其形上法身恒存,历水、火而无碍。聚则成形,散则成炁,存亡由己,千变万化,精神长乐无忧。此时,修丹者不能独善其身,更当潜遁世间,暗施阴德,功济群品,以开度群迷,接引后学,积功累德,待时至则天上的太一尊神将见召,从此便可以移居“中洲”等仙境。当然,修丹者只有功德圆满之后,方可以镂名于金简之上,膺受道门之图箓,从而获得升为上仙之条件。
《火记》不虚作章第二十九
【题解】
本章明丹道炉火之事实法《周易》阴阳之理而行,尤其重视以青龙、白虎等“四象”论丹道之药物。
自外丹言之,炉鼎器形如偃月之状,“白虎”喻铅金,先下铅金,后入流汞,汞以铅为枢纽。流珠本由汞作,其性质为阳之精,青龙亦是;白虎乃铅之精,熬铅化为汁,再投入青龙汞,得火烹炼以后,化而为丹。铅、汞相合,如人之魂魄相求,实即阴阳相合之意。炼丹时,以铅半斤与汞半斤相配,一两计有二十四铢,则铅半斤计一百九十二铢,汞半斤计一百九十二铢,一斤共有三百八十四铢;《周易》一卦有六爻,六十四卦计有三百八十四爻,其中阳爻一百九十二,阴爻一百九十二,而乾、坤阴阳之道由是而备,故丹道药物之铢数与《易》卦之爻数正好相应。汞为日,铅为月,日月为“易”字,故《易》道不倾。
自内丹言之,偃月炉谓“玄关一窍”,因其神、炁相抱,各占一半,犹如月相中半黑半白的偃月,故以《周易》坎卦象之。“铅金”喻人身之精、炁,偃月炉中,铅之精、炁居于其内,丹经术语则说“金、水同居”,或者说坎水中藏有铅金;“汞”喻人的心神,流珠鼎中,汞得火而化青龙,因青龙位东、五行属木,故丹经术语则说“木、火为侣”,也即南方朱汞离火之识神中,藏有东方青龙之元神。识神中现出元神,即是“火里栽莲”、“龙从火里出”;炼精化炁,即是“水中求金”、“虎向水边生”;神与精、炁相交媾,则可以喻之为东西合、南北交、龙虎斗,或坎离交媾、魂魄相制等种种譬喻。月相中,上弦阴阳各半,以《周易》的兑卦象之;经八日后成月圆之象,以《周易》的乾卦象之。下弦亦阴阳各半,以《周易》的艮卦象之;经八日后成月晦之象,以《周易》的坤卦象之。合月相之上、下两弦,则乾、坤鼎器成立,而“二八应一斤”的铅、汞药物、“三百八十四爻”的文、武火候尽在其中。当然,内丹借《易》道以论丹道之妙,不过取其阴阳两齐而配合相当之意,不能泥文执象而昧其正理。
《火记》不虚作,演《易》以明之[1]。偃月法鼎炉,白虎为熬枢,汞日为流珠,青龙与之俱,举东以合西,魂魄自相拘[2]。上弦兑数八,下弦艮亦八,两弦合其精,乾坤体乃成,二八应一斤,易道正不倾,铢有三百八十四,亦应卦爻之数[3]。
【注释】
[1]《火记》不虚作,演《易》以明之:古有丹书,述丹道火候之功用,其名为《火记》。《火记》之旨乃通过推演《周易》阴阳之理,以明丹道炉火之事,故并非虚而无据。
[2]“偃月”六句:炼丹之鼎、炉,其形状有如仰月;铅等药物处鼎中,得炉火煅炼而沸腾翻滚,其色先为白,有如白虎,乃炼丹之重要枢机;汞经火煅炼后所得之精华,喻为太阳之精,也称之为“流珠”,因其状为珠之形,光明流转,滑利如珠;当然,因为汞得火则沸腾、飞跃,故还可以腾跃之青龙喻之。炼丹时,铅、汞在鼎炉中得火煅炼,相融、相抱,《周易参同契》则喻之为“白虎”与“青龙”俱,“东”与“西”相合,“魂”与“魄”相拘。偃月,月相中的一种,外丹以之喻炼丹之鼎炉,鼎炉的形状为前下圆、后上缺,如偃月之状;或谓鼎炉因其下部得火而红,其势将由下而上进,鼎炉外形红、黑相判别,如偃月之相,遂得名“偃月炉”;或谓鼎象望月之圆,可容药物,炉象弦月之缺,可纳火符,故说“偃月法鼎炉”。内丹则以“偃月炉”喻玄关一窍,因其神、炁相抱,各占一半,犹如月相中半黑半白的偃月,故称之为“偃月炉”。因其与月亮相关,丹经或以《周易》坎卦喻之。偃,卧、仰之意。白虎,丹经以之喻铅金。中国古代以六神兽镇四方上下,其中,青龙位居东方,朱雀位居南方,白虎位居西方,玄武位居北方,另有勾陈与腾蛇,各居其所。因铅金熔化后,在某一个阶段,其色变白,而五行中金色白,位配西方,与“六神”中之白虎相应,故铅金亦可称为“白虎”。“白虎”铅金投入以《周易》坎卦表示的偃月炉中烹炼,即丹经《太白真人歌》所谓的“虎向水边生”。或谓“白虎”乃铅、汞化合所成之金花,其色玄白。熬,煎熬。枢,枢机。外丹认为,先下铅金入鼎炉中,然后下入汞,流汞以铅金为枢纽;或谓“熬枢”乃药处偃月鼎炉中,先沿鼎炉之边而下沉于底,后得火煅炼,化而为水气沿鼎炉之壁蒸润上行,鼎中之药即是“熬枢”。汞日,外丹认为,铅、汞两味药物,汞常动为阳,铅常静为阴,汞阳配日,铅阴配月,故称汞为“汞日”,丹经或以《周易》离卦喻之。流珠,汞经火煅炼后所得之精华,因其状为珠之形,光明流转,滑利如珠,故称之为“流珠”。青龙,汞得火则沸腾、飞跃,丹经中故以腾跃之青龙喻之。青龙是汞经火煅炼后所得之精华,与流珠实为一物。丹经《太白真人歌》所谓“龙从火里出”,实源出于此。或谓流汞呈液态水状,水数为一;汞得火烹炼,火数为二;以水一、火二相加则为三,三为木数,木处东方、为青龙所镇守,故流汞经火炼后所得之精华称“青龙”。举东以合西,魂魄自相拘,中国古代中医有以五行配五方和人之五脏的说法,如东方五行属木,色青,以人之肝脏与其对应,而肝中藏魂;西方五行属金,色白,以人之肺脏与其对应,而肺中藏魄;南方五行属火,色赤,以人之心脏与其对应,而心中藏神;北方五行属水,色黑,以人之肾脏与其对应,而肾中藏精;中央五行属土,色黄,以人之脾脏与其对应,而脾中藏意。铅为白虎居西,汞为青龙居东,东方属肝脏而藏魂,西方属肺脏而藏魄;炼丹中,铅、汞相融、相抱,则可以“东”“西”相合,“魂”“魄”相拘来喻之。或谓《周易》先天八卦中,离东而坎西,离为日、魂而坎为月、魄,东西合、魂魄交,实即“取坎填离”、复归纯乾之体的意思。内丹认为,龙虎、铅汞、金木、东西、魂魄、上下弦、乾坤之属,乃至坎离、日月、水火、南北、四象、五行等,都只是譬喻之言,或者互换其名,其实只是神与精、炁二物,内丹以神运精、炁,使之结而为丹。如果人能虚心静默,凝神入于气穴、丹田,则神与精、炁混融,丹经以“东西配合”、“金木交并”、“南北混融”、“水火既济”等喻之。鼎炉,他本或作“炉鼎”。拘,他本或作“求”。
[3]“上弦”八句:初八日,月生一半之明,乃上弦之时,以《周易》之兑卦象之;自八日兑卦上弦再进八日,月相乃圆,成十五之乾体,故说“上弦兑数八”。二十三日,月生一半之魄,乃下弦之时,以《周易》之艮卦象之;自二十三日艮下弦,又退八日,乃成三十之坤体,故说“下弦艮亦八”。月相中,上弦经八日后成月圆之象,以《周易》乾卦象之;下弦经八日后成月晦之象,以《周易》坤卦象之,故说“两弦合其精,乾坤体乃成”。炼丹时,以铅半斤与汞半斤相配,古代一斤为十六两,正应丹道药物一斤之数,故说“二八应一斤”。一两又计二十四铢,则一斤共有三百八十四铢,其中铅半斤计一百九十二铢,汞半斤计一百九十二铢;《周易》一卦有六爻,六十四卦计有三百八十四爻,其中,阳爻一百九十二,阴爻一百九十二,而乾、坤阴阳之道备。故丹道药物之铢数与《易》卦之爻数,其数正好相应。当然,《周易参同契》借易道以论丹道之妙,不过取其阴阳两齐、配合相当之意。铢(zhū),中国古代计量单位之一,二十四铢为一两。艮亦八,他本或作“数亦八”、“亦如之”。亦应卦爻之数,他本或作“亦应爻之计”、“亦应火候爻象之计”,另有注本则无此“铢有三百八十四,亦应卦爻之数”句。
【译文】
古有丹书名为《火记》,其旨乃通过推演《周易》阴阳之理,以明丹道炉火之事,故并非虚而无据。炼丹之鼎、炉,其形状有如仰月;于此鼎器中,先熬铅化为汁,此铅之精名为白虎,再投入流汞,汞当以铅为枢纽;汞经火煅炼后所得之精华,因其光明流转,滑利如珠,也称之为流珠;又因汞得火则沸腾、飞跃,故还可以腾跃之青龙喻之;炼丹时,铅、汞在鼎炉中得火煅炼,相融、相抱,则喻之为“东”与“西”相合,“魂”与“魄”相拘。月相中,上弦月阴阳各半,经八日后成月圆之象,以《周易》乾卦象之;下弦月亦阴阳各半,经八日后成月晦之象,以《周易》坤卦象之;上、下两弦,“二八”相合,《周易》乾、坤之体,于是乃成;丹道铅、汞药物,亦各重八两,两个八两相加,共计十六两,正应一斤之数,如此则大易乾坤阴阳之道与丹鼎铅汞炉火之道,皆中正而不倾颓;《周易》一卦有六爻,六十四卦计有三百八十四爻,其中,阳爻一百九十二,阴爻一百九十二,而乾、坤阴阳之道备于此;丹道之药,铅半斤计一百九十二铢,汞半斤计一百九十二铢,其一斤共有三百八十四铢,故丹道药物之铢数与《易》卦之爻数正好阴阳两齐、配合相应。
金入于猛火章第三十
【题解】
本章直指先天金性为丹道之基。
自外丹言之,丹药所含本来金性,虽入猛火之中煅炼,其色不变、其性不失、其重不减,与天地之间的日、月同其恒久。铅得火炼而熔成汁,成液态水状;再入汞造作,结晶形成金花。铅象月而汞象日,铅、汞受气、变化之理,与朔旦月受日光之理正同。炼丹旨在通过炼铅、汞等药物,以求复归于其所涵有的万劫不坏的本来金性。炼丹起火,以朔旦月受日光为喻;丹成伏火,则以月晦为喻。伏火时铅、汞相融、相抱,与月晦之时日、月合璧之象相似;此时,铅、汞彼此相互隐伏、潜藏于对方之中,其各自的界限已不分明;因炉下之火已伏,铅、汞熔液不再上下沸腾、翻滚,而是收缩、沉伏于鼎器的底部,鼎器一时显得旷广、空虚。金得猛火烹炼,乃能去除杂质,复其固有之金性,故鼎炉火炽,则金色愈明。
自内丹言之,“金”乃喻人先天之真炁或本来之真性,历劫不坏,与日、月同久。通过凝神入于炁穴,神与精、炁相混,昏昏默默、窈窈冥冥,时至则凝而成丹,此与日月晦朔之理正同。精、炁处坤腹丹田之中,与神相守不离,亦犹月晦之夜日、月之合璧;神与精、炁相扭,初则无形无象、无声无息,渐渐沉归于丹田、气海,如月魄之不见;然守之既久,则剖开太极,劈破天心,一阳之真金来复,顷刻之间光芒透鼎,趋此时火力炽盛,当运转河车,由会阴海底沿督脉直达头顶之昆仑峰顶,此则所谓“金复其故性,威光鼎乃熺”。
金入于猛火,色不夺精光[1]。自开辟以来,日月不亏明,金不失其重,日月形如常[2]。金本从月生,朔旦受日符[3]。金返归其母,月晦日相包,隐藏其匡郭,沉沦于洞虚[4]。金复其故性,威光鼎乃熺[5]。
【注释】
[1]金入于猛火,色不夺精光:真金入于猛火之中煅炼,其性不失,精光倍增,益愈光亮。外丹认为,丹药所含本来金性,亦万劫不坏,无有能夺其精光者。内丹则以金性为人父母未生之前的本来真性,亘古不坏。金入于猛火,他本或作“以金入猛火”、“金入猛火中”。精光,他本或作“晶光”。
[2]自开辟以来,日月不亏明,金不失其重,日月形如常:自宇宙开天辟地以来,不知道经过了几千万年,而日、月之形恒常不变,未尝亏折其光明。天地间之物,与日、月同其长久者,还有真金,其本性至为稳定、坚固,未尝变性、褪色,弥历时久,而其重量亦如其初时一般,没有缺失。世间真金尚且如此,丹道认为,丹药之金性、人之本来真性亦无欠无余,任时、空变化而常存。
[3]金本从月生,朔旦受日符:铅得火炼而熔成汁,成液态水状;再入汞造作,结晶形成金花。金花由铅汁变化而来,《周易》以坎卦象水、象月,故说“金本从月生”。月之光本生于日,月为太阴,有质而无光,以受日光之多少而定其盈亏;月自朔旦,始与日合,经过三日,而生其明,此为“朔旦受日符”;铅象月而汞象日,铅亦视汞入之多少,彼此配合、相含受而产生金花,其受气、变化之理,亦同于朔旦时月受日光之理。天地间,“悬象著明,莫大乎日月”;丹道炉火,亦莫过于铅、汞。内丹则以神为火、为日,以精、炁为水、为月,凝神入于炁穴,神与精、炁相混,结而成丹,此与日、月晦、朔之理正同。朔旦,农历每月初一日。日符,即太阳光。
[4]金返归其母,月晦日相包,隐藏其匡郭,沉沦于洞虚:炼丹不离铅、汞之金,通过炼铅、汞之金,以求复归于其所涵有的万劫不坏的本来金性,此谓“金返归其母”。或谓烧炼铅、汞使之变而成丹砂,变化丹砂使之成为金花,丹砂乃金花之母。此后,再以火煅造,使金花复又化成纯度更高的丹砂,故说“金返归其母”。炼丹之火初起,丹经以朔旦之时月受日光为喻;炼丹告一段落后,火气既足,则须伏火,以月晦为喻;此时,铅、汞相融、相抱,与月晦之时日、月合璧之象相似,此为“月晦日相包”;或谓炼丹从起火至伏火,用月朔、月晦一周天喻之;文、武火候既足,则又重开炉灶、研治丹砂,丹经则以初一朔旦日光重新包裹月亮喻之,以之为“月晦日相包”之意。丹灶伏火后,铅、汞彼此相互隐伏,潜藏于对方之中,其各自的界限已不分明,此为“隐藏其匡郭”;因炉下之火已伏,铅、汞熔液不再上下沸腾、翻滚,而是收缩、沉伏于鼎器的底部,鼎器一时显得旷广、空虚,此为“沉沦于洞虚”。《周易·说卦》认为,坤卦可以取象于人之腹部、母亲、釜、土等。丹经中,人身之精、炁常以金、月、坎喻之,神则以火、日、离喻之。内丹学认为,“金返归其母,月晦日相包”指的是精、炁处坤腹丹田之中,与神相守不离,亦犹月晦之夜日、月之合璧,坤之土为金之母,即精、炁处坤腹丹田之中而不外泄之意;或谓“坤土”喻指真意,人之妄识去则真意现,真意现则精、炁与神相扭结而金丹之丹头结,“金返”即“还丹”,还丹之所以成,当归功于坤土之真意。“隐藏其匡郭,沉沦于洞虚”,指精、炁隐藏于坤腹丹田匡郭之中,神则沉浸于空旷、虚寂之境界,神与精、炁相扭,初则无形无象、无声无息,渐渐沉归于丹田、海底,如月魄之不见。然守之既久,则一阳来复,顷刻光芒透鼎,火力炽盛,此则下文所谓的“金复其故性,威光鼎乃熺”。返,他本或作“反”。匡郭,他本或作“垣郭”。
[5]金复其故性,威光鼎乃熺:金得猛火烹炼,乃能去除杂质,复其固有之金性,故鼎炉火炽,则金色愈明,其威光炎炎而可爱。熺,炎之意。他本或作“嬉”,“嬉”则为欢喜之意,认为金、汞成形,丹乃成功,故炼丹人心欢喜悦。
【译文】
真金入于猛火之中煅炼,其性不失,精光倍增。自宇宙开天辟地以来,不知道经过了几千万年,日、月之形却恒常不变,未尝亏折其光明;天地间与日、月同其长久者,还有真金,其重量历久而不减。炼丹时,金花由铅所熔液汁变化而来,《周易》以坎卦象水、象月,故说“金本从月生”;月本无光,以受日光之多少而定其盈亏,月自朔旦始与日合,经过三日而生其明,此为“朔旦受日符”。丹药中,铅象月而汞象日,铅熔化成液汁之后,还要视所加入之汞量的多少,才能彼此配合、相含受而产生金花,其受气、变化之理,亦同于朔旦时月受日光之理。炼丹不离铅、汞之金,通过炼铅、汞之金,以求复归于其所涵有的万劫不坏的本来金性,此谓“金返归其母”;炼丹伏火,以月晦为喻,此时铅、汞相融、相抱,与月晦之时日、月合璧之象相似,此为“月晦日相包”;丹灶伏火后,铅、汞彼此相互隐伏、潜藏于对方之中,其各自的界限已不分明,此为“隐藏其匡郭”;因炉下之火已伏,铅、汞熔液不再上下沸腾、翻滚,而是收缩、沉伏于鼎器的底部,鼎器一时显得旷广、空虚,此为“沉沦于洞虚”。金得猛火烹炼,乃能去除杂质,复其固有之金性,故鼎炉火炽,则金色愈明。
子午数合三章第三十一
【题解】
本章主要阐明丹道药物交媾之道。
自外丹言之,铅水、汞火、鼎炉土三物,乃炼丹之纲纪。铅、汞水火之气,彼此相呼吸于鼎器之中,相交、合体,犹如夫妇之道。铅、汞相熔所得金花,乃于鼎炉中产出;使铅、汞液汁不飞走,皆因鼎炉土之功。至于能烹炼铅、汞者,唯火而已,然火候之进退,亦要注意调节均衡。汞虽流转不定,却终为铅所拘。汞入铅中,伏火铅汞成砂,砂如土如灰,故俱归厚土;还丹既成,铅、汞俱亡,唯鼎炉之土独存。
自内丹言之,精、炁与神可喻为水火,坎离,水数一、火数二,真意喻为土,土数为五。以真意之土为水、火之媒,在其间调停配合,使水、火即精炁与神结为夫妇,也即是丹,如此则阴阳和谐,“八石”即八方和气皆来归之。修行人虚心凝神,回光内照,存神既久、神宁息定则真意出现,如此则自然一阳来复、先天元阳之炁发生。真意“黄土”乃“金”即先天元阳之炁之父,此先天元阳之炁合汞之神与铅之炁、精而成,易于逃逸,故又可以“流珠”喻之,乃后天肾水之精之母。后天肾水之精听命于“黄土”真意,真意出则肾水之精不妄流。南方朱雀火精喻心,心之意识杂乱无主,则精炁逃逸而不暂聚,此为火炎而水涸,神敝而精炁散;心之意识空灵虚静,则精炁因无干扰而得以聚集,此为水火既济,神不敝而精炁充盈。只有调匀水火,使之进退有序,则精炁充盈而神旺。铅之精、炁与汞之神在黄婆真意的作用之下,入鼎炉即丹田中煅造,则水、火、土三性会合;精炁与神混而为一,成就丹宝,丹宝乃元始先天祖炁、具亘古不变之本来真性,精炁与神皆自此元始先天祖炁、本来真性中出,然同出而异名;经修炼之后,最后又可以复归于此元始先天祖炁、本来真性,故说“本性共宗祖”。
子午数合三,戊己号称五[1]。三五既和谐,八石正纲纪[2]。呼吸相贪欲,伫思为夫妇[3]。黄土金之父,流珠水之母[4]。水以土为鬼,土镇水不起[5]。朱雀为火精,执平调胜负[6]。水盛火消灭,俱死归厚土[7]。三性既合会,本性共宗祖[8]。
【注释】
[1]子午数合三,戊己号称五:子为水,水数一;午为火,火数二,相合成三。戊己为土,土数为五。炼丹最重要者,莫过于水、火、土三物。外丹以铅、汞为水、火,以鼎器、炉灶为土;内丹则以精、炁、神为水、火,以真意为土。《周易参同契》此说据汉易五行生成之数。汉代易学的特点之一,即以五行说解释《周易》的筮法、象数,把《周易·系辞》中的“天地之数”、“大衍之数”与五行联系起来,其内容大致为:天一生水于北,地二生火于南,天三生木于东,地四生金于西,天五生土于中;阳无偶、阴无配,不能相成,故地六成水于北,与天一并;天七成火于南,与地二并;地八成木于东,与天三并;天九成金于西,与地四并;地十成土于中,与天五并。汉易纳甲法中,又以甲乙为木、丙丁为火、戊己为土、庚申为金、壬癸为水;纳支法中,以亥子为水、寅卯为木、巳午为火、申酉为金、辰戌丑未为土。《周易参同契》此说又启后来陈抟、邵雍的河图、洛书之学。号称,他本或作“数称”。
[2]三五既和谐,八石正纲纪:子水一、午火二,子午之数合而成三;土数为五,“三”与“五”合而成“八”,此为“三五既和谐,八石正纲纪”。三五和谐,指水、火、土三者合会,其中,外丹以之指铅、汞药物入鼎炉中烹炼成丹,或者指炼丹时水火进退有据、鼎炉稳固而无泄漏之虞;内丹则指以真意之土为水、火之媒,在其间调停配合,使水、火即精炁神结为夫妇,也即是丹,如此则阴阳和谐、八方和气皆来归之。八石,泛指炼外丹所用之药。陈撄宁先生认为,“八石”有两种说法:一种说法以朱砂、雄黄、雌黄、硫黄、空青、云母、硝石、戎盐(青盐)为“八石”,另一种说法则将云母、硝石、戎盐改为硼石、胆矾、信石,其余五种不变。此句意为水、火、土之间阴阳配合得当,相为夫妇、互做君臣,有如炼外丹时,八石之间互相配伍,相为制约,共成丹宝。和谐,他本或作“谐和”。
[3]呼吸相贪欲,伫思为夫妇:铅、汞得水火之气烹炼,铅呼于汞、汞吸于铅,两者相混融于鼎器之中;铅、汞相交、合体,阴阳对待、两停,犹如夫妇之道。内丹则认为,人能虚心凝神,回光内照,随真息之升降,顺其自然而存之,久之则能达到呼吸兀然自住,神与炁精则打成一片,结为夫妇。或谓土属脾,脾主意,真意能使心神之火下而精炁之水上,水、火一上一下,水火既济、相呼吸而结为夫妇。呼吸,出气为呼,入气为吸,一呼一吸,则为一息。贪欲,他本或作“含育”。伫思,他本或作“伫息”。
[4]黄土金之父,流珠水之母:五行中,土生金、金生水、水生木、木生火、火生土;土居中央,中央之色配黄,故称“黄土”,土生金,故说“黄土金之父”;流珠乃汞升华后之结晶,以其游走不定,故称“流珠”,汞入于铅汁之中,以火烹炼,则结成流珠,此流珠中已含有铅金之性,因金能生水,故说“流珠水之母”。内丹则以“黄土”喻真意,修行人存神既久、神宁息定则真意出现,如此则自然一阳来复、先天元阳之炁发生。先天元阳之炁可以“金”喻之,故说“黄土金之父”;此“金”乃汞神入于铅炁中、神炁相合的产物,易动而流失,故又以“流珠”喻之,乃后天肾精的来源,后天肾精以“水”喻之,故说“流珠水之母”。
[5]水以土为鬼,土镇水不起:炉鼎之土能闭固铅、汞之液汁,遏之使不漏泄。汉易纳甲法以五行配六亲,六亲指父母、兄弟、妻财、子孙、官鬼。五行中,土克水、水克火、火克金、金克木、木克土;其中,土克水,土即为水的官鬼、水即为土的妻财;土生金,土即为金的父母、金即为土的子孙;五行性质相同,则为兄弟,如天干之“戊”与“己”皆属土,即为兄弟,地支亦同此理。内丹以“土”喻真意,以“水”喻精炁,真意既定则炁和脉住,即“水以土为鬼,土镇水不起”。镇,他本或作“填”。
[6]朱雀为火精,执平调胜负:朱雀为火,居南方,鼎中之药若得南方朱雀之火猛烹极煅,则铅、汞烊成液汁;铅必得火而熔,铅熔乃能止汞;汞必得铅而止,铅、汞和凝得体,则能产金花、黄芽,此则为“朱雀为火精,执平调胜负”。执平,指调整、调匀的意思。胜负,为加减铅、汞之剂量;或谓指升降炉火,升指加炭,降指减炭。内丹以朱雀南方火精喻心,乃意识之主。心之意识杂乱无主,则精炁逃逸而不暂聚,此为火炎而水涸,神敝而精炁散;心之意识空灵虚静,则精炁因无干扰而得以聚集,此为水火既济,神不敝而精炁充盈。朱雀离火为心神,坎水为肾精、先天元阳之炁,人身之神与炁、精,犹如水火,火炎则水干,水决则火灭;然水非火则冰,无以润物;火非水则炎,而焚毁万物,只有调匀水火,使之平衡,则精炁充盈而神旺。执平,他本或作“气平”。
[7]水盛火消灭,俱死归厚土:铅得火即烊成液汁,故以水喻铅;汞俗称“水银”,常闪烁有光亮,故以“火”喻汞;铅能制伏汞,使之不流逸,此则为“水盛火消灭”。汞入铅中,铅、汞伏火而成砂,砂之色如土、如灰,故说“俱死归厚土”。内丹则认为,人身精炁充盈则水盛,水盛则妄火不炎,妄火不炎则心定神和而脉住,归于冲虚无为,冲虚无为则真意呈现,真意即土。故火虽炽盛,为水消灭;水火俱息,唯土独存;还丹既成,水火消亡。
[8]三性既合会,本性共宗祖:铅水、汞火与鼎炉之土,称为“三性”;铅、汞入鼎炉中煅造,称“三性合会”;铅、汞皆奉鼎炉之土为宗祖,因为只有在鼎炉中,铅、汞方能得到烹炼,从而混而为一,成就丹宝。或谓丹宝乃元始先天祖炁,铅、汞同禀有此元始先天祖炁,故能炼之而成丹;然同出而异名,故有铅、汞之异。铅、汞同出于元始先天祖炁,最后又复归于元始先天祖炁,故说“本性共宗祖”。既,他本或作“以”、“已”。合会,他本或作“会合”。
【译文】
子为水、水数一,午为火、火数二,相合成三;戊己为土,土数为五。炼丹最重要者,莫过于水、火、土三物。外丹以铅、汞为水、火,以鼎器、炉灶为土;内丹则以精、炁与神为水、火,以真意为土。铅、汞药物入鼎炉中烹炼,炼丹时水火进退有据、鼎炉稳固而无泄漏之虞,如此则八石等丹药皆可阴阳谐和。铅、汞得水火之气烹炼,铅呼于汞、汞吸于铅,两者相混融于鼎器之中,相交、合体,阴阳对待、两停,犹如夫妇之道。五行中,土居中央,中央之色配黄,故称“黄土”;土生金,故说“黄土金之父”;汞入铅汁中,得火烹炼,结成流珠,此流珠中已含有铅金之性,因金能生水,故说“流珠水之母”。炉鼎之土能闭固铅、汞之液汁,遏之使不漏泄,以五行之理证之,则为土能克水、土镇则水不能起;汉易纳甲法有“六亲”之说,其以土为水之“官鬼”。南方朱雀喻火,火烹则铅、汞烊成液汁,此时要注意铅、汞之比例是否协调,进火、退火是否及时。铅得火即烊成液汁,故以水喻铅;汞俗称水银,常闪烁有光亮,故以火喻汞;铅能制伏汞,使之不流逸,以五行之理证之,则为水能克火、“水盛”则“火消灭”;汞入铅中,铅、汞伏火而成砂,砂之色如土、如灰,砂成则铅、汞俱失其原来的存在状态,故说“俱死归厚土”。铅水、汞火与鼎炉之土,称为“三性”;铅、汞入鼎炉中煅造,称“三性合会”;铅、汞得火烹炼,混而为一,成就丹宝,丹宝乃元始先天祖炁,铅、汞虽同禀有此元始先天祖炁,然同出而异名;炼成丹宝后,铅、汞又复归于元始先天祖炁,故说“本性共宗祖”。
巨胜尚延年章第三十二
【题解】
本章论服食金丹之效果。
巨胜尚延年,还丹可入口[1]。金性不败朽,故为万物宝;术士服食之,寿命得长久[2]。土游于四季,守界定规矩[3]。金砂入五内,雾散若风雨[4]。薰蒸达四肢,颜色悦泽好;发白皆变黑,齿落生旧所;老翁复丁壮,耆妪成姹女;改形免世厄,号之曰真人[5]。
【注释】
[1]巨胜尚延年,还丹可入口:“巨胜”即胡麻,人食之尚能延年益寿;况金液还丹,为至贵之宝,如得服之,其功效远胜胡麻等凡药。或谓“巨”乃“大”之意,“巨胜”即其功效大大胜于诸丹,故称“巨胜”;后世亦有谓巨胜、胡麻乃两种不同的药物。内丹常以“巨胜”喻真种子,即内丹之药物,以其为炼己、持心之根柢。
[2]金性不败朽,故为万物宝;术士服食之,寿命得长久:金之性坚刚,经久而不腐朽,故为万物中之至宝,炼丹之术士服之,乃得长生。当然,此“金”非通常金银之“金”,乃是还丹之真金,乃天地元炁之祖。天地之先,一炁为初,而生万象,即此为万物之母。
[3]土游于四季,守界定规矩:土分旺于春季之辰月(三月)、夏季之未月(六月)、秋季之戌月(九月)、冬季之丑月(十二月),于四季中各旺十八天,故土之气游走于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,土居每季之末,故为四季之分野,此则为“土游于四季,守界定规矩”。炼丹时,以黄土筑为鼎灶;或炉之四面,以黄土涂之;或者铁鼎内涂抹以黄土,故说土能守铅、汞之界,为其定出活动的范围、规矩。或谓土能竭水藏火、生金养木,其守于水则水不流,守于火则火不焰;土中能生金、藏金,木亦从土而出、为土所养,故金、木、水、火皆资土而立。
[4]金砂入五内,雾散若风雨:丹之神妙不同凡药,金丹入口之后,在人体中涣然如云雾之四散,飒然如风雨之迭至,径入于五脏、六腑。金砂,指大还丹。五内,五脏;或谓五脏、六腑。
[5]“薰蒸”八句:服丹之后,真炁在体内游走,如水得火烹而变成水蒸气,而在体内熏蒸、流布,达至于四肢、百骸。此时,人自然神清气爽、颜色光鲜、精神欢悦,并且能发白返黑,齿落再生,老翁变为壮汉,老妪又成少女,从此回颜换骨、返老还童,避开世俗种种灾难、厄运,跳出樊笼、逍遥物外,号称得道之“真人”。中国古代以七十岁以上者为老人,以六十岁以上者为“耆”(qí),“耄”(mào)则指七十至八十岁的年龄,“耋”(dié)指八十至九十岁的年龄,九十岁为“颐”;一说六十岁为老,七十岁为耆。妪(yù),老女则称“妪”。丁壮,汉朝法制,男子二十岁为丁。姹(chà)女,美丽的女子,尤指美丽的少女、处女之意。“发白皆变黑,齿落生旧所”二句,他本或作“鬓发皆变黑,更生易牙齿”。
【译文】
巨胜即胡麻,人食之尚能延年益寿;况金液还丹,如得服之,其功效远胜胡麻等凡药。尤其还丹中所涵之金,其性坚刚,经久而不腐朽,故为万物中之至宝;炼丹之术士服之,乃可以得长生。炼丹时,炉鼎之四面以黄土涂之,这样就可以限定铅、汞等药物活动之范围,使其不能渗透出于鼎炉之外,而超出其应处之所。丹之神妙不同凡药,人服食之后,丹在人体中涣然如云雾之四散,飒然如风雨之迭至。径入于五脏、六腑,其所化之真炁在人体内游走,犹如水之蒸气,熏蒸而流布,达至于人的四肢、百骸,此时,人自然神清气爽、颜色光鲜、精神欢悦;并且能发白返黑,齿落再生;老翁变为壮汉,老妪又成少女;从此回颜换骨、返老还童,避开世俗种种灾难、厄运,跳出樊笼、逍遥物外,号称得道之真人。
胡粉投火中章第三十三
【题解】
本章明炼丹当以同类之物相互作用、变化成宝为原则,又以异类不能相成反复阐明此道理。
自外丹言之,胡粉本是炒铅和醋盐做成,如果放于火上去炒,必复变还为铅;丹经以此来比喻炼丹所用水银本含金之性,对水银加热,能使之复还其本有之金性,以此金性为基础,加入其他药物,变化成金丹。因为种类相生、终始相因乃自然之道,故《周易参同契》认为,想要服食丹药成仙,应该服以同类型之物;性质相类同之物,对人有所助益;如果服用性质不相同之物,则对人有害。
自内丹言之,“金”喻元阳祖炁,“砂”为“朱砂”,喻人之心神,“水银”喻人的元阳之精,三者为同类互生之真种,精在神的作用之下可以化炁,结成内丹。如果以《周易》坎卦喻人的元阳之精,坎卦虽然象水,然坎卦二阴爻夹有一阳爻,此阳爻乃是生命之火,一阳藏于二阴之中,犹如水中藏火,喻人之肾水固则命火安,命火存则肾水温而不冷;如果以《周易》离卦喻人之神明,离卦虽然象火,然离卦二阳爻夹有一阴爻,犹如心以血为用、烛膏能燃火,心劳则精耗、火炽而膏消,心静则精神内充而不耗散。故坎之一阳来自于乾天,离之一阴来自于坤地;阳与阳同类,故坎阳有升之理;阴与阴同类,故离阴有降之势,水升火降则既济而交媾,本于自然之理,此合于《周易·文言》所说:“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。水流湿,火就燥。”“本乎天者亲上,本乎地者亲下,则各从其类也。”
胡粉投火中,色坏还为铅[1]。冰雪得温汤,解释成太玄[2]。金以砂为主,禀和于水银[3]。变化由其真,终始自相因[4]。欲作服食仙,宜以同类者。植禾当以黍,覆鸡用其子;以类辅自然,物成易陶冶。鱼目岂为珠,蓬蒿不成槚;类同者相从,事乖不成宝!是以燕雀不生凤,狐兔不乳马;水流不炎上,火动不润下[5]。
【注释】
[1]胡粉投火中,色坏还为铅:胡粉本由黑铅烧炼而成,若投之火中,则其色变坏,复还为铅之体。物类相感,有不期然而至不容不然之理,炼铅可为胡粉,炼胡粉又可以复为铅,如此则归其本。一说,胡粉本是炒铅和醋盐做成,如果放于火上去炒,必复变还为铅;丹经以此来比喻炼丹所用水银本含金之性,对水银加热,能使之复还其本有之金性,以此金性为基础,加入其他药物,变化成金砂,则成金砂还丹。火,他本或作“炭”。另他本“胡粉”前或多一“若”字。
[2]冰雪得温汤,解释成太玄:冰雪乃由水冻结而成,若把冰投于热水中,则冰于热水中慢慢溶解,还会复化为水。水凝而冰,冰消为水,是为归其本根;炼丹亦取此返本还元之理。太玄,此喻水,因五行中水居北方,水深则幽暗玄黑,故称“太玄”。玄,乃幽暗、黑暗不明之意。
[3]金以砂为主,禀和于水银:炼铅金之目的,乃在于求得金砂、黄芽;在这个过程中,须和入水银也即是汞,铅、汞相配得其理,方能成就金砂。砂,指金砂,将铅久炼,熔铅化为汁,和入水银一起烧,可以炼成金花,名为“金砂”,或名“黄芽”;以金砂为本根,变化而产铅、汞,炼铅与汞,则可复得金砂。或谓古代炼金术以金出于金砂,而金砂之所以能炼出黄金,实由金砂中所含之水银;炼金之法,以金砂、水银同入灰池之中,以火煅之,则金浮而水银沉,所以,金之生成皆禀于水银。内丹则以“金”喻元阳祖炁;“砂”为“朱砂”,喻人之心神,故有“神砂”之称,朱砂亦可以《周易》离卦喻之;“水银”可以喻人的元阳之精,因其呈液态流动之状且有光亮,故有“水银”之称,“水银”亦可以《周易》坎卦喻之。金、砂、水银即神、炁、精,内丹不离神与炁、精,研和此二物,则可以成就内丹。故修炼之士,不可以外神与炁、精而别用其心。
[4]变化由其真,终始自相因:铅金与汞为真种子,铅、汞相合,自有变化之理,可以结成丹宝。水银与砂为同类之物,所以终始相因而成变化。犹如以金做金戒指则必成,种豆望豆则豆必生,因种类相生、终始相因,乃自然之道。
[5]“欲作”十四句:《周易参同契》认为,想要服食丹药成仙,应该服以同类型之物;性质相类同之物,对人有所助益;如果服用性质不相同之物,则对人有害。譬如种植禾黍当以黍子为种,孵小鸡必须用授精后的鸡蛋,因其种类相同,则不劳于人力而自然生成变化,犹如烧土为陶、铸金为器一般易于陶冶。如果炼丹、服食舍其同类而别求他物,则犹如鱼之目不可为珍珠,蓬蒿之草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一样,药物性质既不相同,怎么可能变化生成金丹!亦犹燕子只能孵出小燕子、鸟雀只能生同类型的鸟雀,如果要想使它们生出凤凰,则不可能;狐狸妈妈只能哺乳小狐狸,兔子妈妈只能哺乳小兔子,如果要想使它们去哺乳马,则不可能;火的性质是炎上,使之润下则不可能;水之性质为润下,使之炎上亦不可能。炼丹亦同此理。真汞得其铅,则一阴一阳,气类相感,是为同类,故知同类即成,非类不可,铅、汞相合,事须谐和,方能结成金丹。黍(shǔ),一年生草本植物,叶子线形,籽实淡黄色,去皮后叫黄米,比小米稍大,煮孰后有黏性。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,籽实可以酿酒、做糕等。槚(jiǎ),古书上指楸树或茶树。他本或夺“鱼目岂为珠,蓬蒿不成槚”十字。服,他本或作“伏”。辅,他本或作“转”。“类同者相从,事乖不成宝”二句,他本或作“同类易施功,非种难为宝”。火动,他本或作“熏动”。
【译文】
胡粉本由黑铅烧炼而成,若投之火中,则其色变坏、复还为铅之体。冰雪乃由水冻结而成,若把冰投于热水中,则冰于热水中慢慢溶解,还会复化为水。炼铅金之目的,乃在于求得金砂、黄芽;在这个过程中,须和入水银也即是汞,铅、汞相配得其理,方能成就金砂。铅金与汞为真种子,铅、汞相合,可以结成丹宝,因其为性质相同之物,所以才可以种类相生、终始相因而成变化,此乃自然之道。人想要服食丹药成仙,亦应该采用同类性质之物,性质相同之物,对人有所助益;如果服用性质不相同之物,则对人有害。譬如种植禾黍当以黍子为种,孵小鸡要用授精后的鸡蛋,因其种类相同,则不劳于人力而自然生成变化,好比烧土为陶、铸金为器,如此则易于陶冶。如果炼丹、服食舍其同类而别求他物,则犹如鱼之目不可把它当作珍珠,蓬蒿之草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一样;只有同类性质的药物,方能相互作用而成丹,药物性质不相同,怎么可能变化生成金丹!故燕子只能孵出小燕子、鸟雀只能生同类型的鸟雀,如果要想使它们生出凤凰,则是不可能的;狐狸妈妈只能哺乳小狐狸,兔子妈妈只能哺乳小兔子,如果要想使它们去哺乳小马,也是不可能的;又好比火的性质是炎上,使之润下则不可能;水之性质为润下,使之炎上亦不可能。炼丹之理与此相同。真汞得真铅,则一阴一阳同类相感,炼就成丹,故非其类则不能结成丹。
世间多学士章第三十四
【题解】
本章叹世上之人不悟还丹之道,广求石药,虽至白首而无成,因其所用炼丹之药杂性不同类,不可能炼就丹宝。
世间多学士,高妙负良才;邂逅不遭遇,耗火亡货财[1]。据案依文说,妄以意为之;端绪无因缘,度量失操持[2]。捣治羌石胆,云母及礜磁;硫黄烧豫章,泥相炼飞;鼓下五石铜,以之为辅枢;杂性不同类,安有合体居!千举必万败,欲黠反成痴[3]。侥幸讫不遇,圣人独知之[4]。稚年至白首,中道生狐疑[5]。背道守迷路,出正入邪蹊;管窥不广见,难以揆方来[6]!
【注释】
[1]世间多学士,高妙负良才;邂逅(xiè hòu)不遭遇,耗火亡货财:世上才高、好学之士很多,虽志慕炉火,然不遇明师示其真诀,不识何者为真铅汞,往往浪费炉火、虚损货财,不能成功。邂逅,偶然遇见,不期而遇。负,他本或作“美”。遭,他本或作“相”。遇,他本或作“值”。
[2]据案依文说,妄以意为之;端绪无因缘,度量失操持:这些人只是根据某些书本所说,妄意为之,反认为道即在于此,没有机缘获知丹法修炼首尾、始末之理,丹法火候之度数长短、丹药剂量之轻重,亦不能如实把握。文说,他本或作“托文”、“说文”。失,他本或作“可”、“何”。
[3]“捣治”十句:只是烧炼胆矾、云母、砒石、磁石、硫黄、朱砂、六一泥、水银、五色石、金属铜等五金、八石之药,以世间有形有质之物作为烧炼丹药之根本或者辅助物。然这些物品其种类各不相同,其性质亦相差甚远,怎么可能结合在一起、形成丹宝!故凡以此术为炼丹之法者,莫不千举万败,虽自认为聪明才智超出于他人之上,反而弄巧成拙,为识者哂为愚痴。羌(qiāng)石胆,即胆矾,含水硫酸盐的金属或由两种金属硫酸盐结合成的含水复盐,盛产于西羌;羌自古即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,于地理位置而言,西羌大约位于今青海、甘肃、四川北部等地。云母,矿物,主要成分为铝硅酸盐。礜(yù),即砒(pī)石之类的矿物;“砒”乃“砷”的旧称,非金属元素,有灰、黄、黑褐三种同素异形体,有毒;砒霜则是一种无机化合物,是不纯的三氧化二砷,为白色粉末,有时略带黄色或红色,有剧毒,也叫“信石”、“红矾”。磁,即磁石之类的矿物,也即是磁铁矿的矿石,具有吸引铁、镍等金属的性能。硫黄,“硫”的通称,硫有多种同素异形体,黄色,能与氧、氢、卤素(除碘外)和大多数金属化合。豫章,古代江西南昌一带地区的称呼,南昌出产香樟木,炼丹者用以烧火炼药;或谓豫章指用洪州、豫章之土为炼丹之鼎炉,捣云母、礜石、磁石、硫黄、石胆为药,于此鼎炉中煅炼;或谓经文所说豫章实指湖南的道州、永州,道州等古属饶州豫章县,出产朱砂、水银;或谓豫章即樟木脑,与硫同性。泥(gǒng),“泥”大概指“六一泥”之类的矿物,“”即朱砂中炼出之水银,乃水银之别名,泥即用泥包裹水银于其内。五石铜,即以五色石和入铜内,铸成各种器具;或谓五金矿物皆出石中,故以“五石铜”代称之;还有谓五石铜可能是某种与道教外丹五石散相似的化合物质。辅,辅助物。枢,枢纽,关键,根本。黠(xiá),聪明而狡猾。痴,愚笨。他本或夺“欲黠反成痴”五字。羌,他本或作“差”。礜,他本或作“矾”。泥相炼飞,他本或作“铅相炼治”、“铅鸿合扣治”。杂,他本或作“异”。类,他本或作“种”。有,他本或作“肯”。
[4]侥幸讫(qì)不遇,圣人独知之:炼丹不明其理,只是妄想以偶然的原因而得到成功或免去灾害,终究是不可能的;金丹之理,暗合天机,只有圣人才有资格了解。侥幸,以偶然的原因而得到成功或免去灾害。讫,始终,一直。他本或夺去此二句,或夺去后一句。
[5]稚年至白首,中道生狐疑:金丹之理,非上述所说这些方法中所能涵盖;某些人运用这些方法去炼还丹,虽自童稚之时即始,至于白发苍苍的老年,蹉跎岁月,不能有所成功;或有始无终,狐疑中道,心生怅望。中道生狐疑,他本或作“用索怅狐疑”。
[6]背道守迷路,出正入邪蹊(xī);管窥不广见,难以揆(kuí)方来:甚至有人得金丹正传却背弃之,出正而入于邪径,背离大道而执守迷路;或执一法、一经、一诀以自足,以偏概全,此犹如以管窥天,其见既不广阔,何足与论方来无穷之玄奥妙理呢!蹊,小路,蹊径。揆,推测揣度。出正入邪蹊,他本或作“履径入曲邪”。不,他本或作“非”。
【译文】
世上才高、好学之士很多,虽志慕丹道炉火,却存侥幸心理,企图无师自通;然不得金丹真诀,不识何者为真铅汞,往往浪费炉火、虚损货财,不能成功。这些人只是根据某些书本所说妄意为之;没有机缘获知丹法修炼首尾、始末之理,丹法火候之度数长短、丹药剂量之轻重,亦不能如实把握。只是烧炼胆矾、云母、砒石、磁石、硫黄、朱砂、六一泥、水银、五色石、金属铜等五金、八石之药,以世间有形有质之物作为烧炼丹药之根本或者辅助物;然而这些物品其种类各不相同,其性质亦相差甚远,怎么可能结合在一起、形成丹宝!故凡以此术为炼丹之法者,莫不千举万败,虽自认为聪明才智超出于他人之上,反而弄巧成拙、为识者哂为愚痴。炼丹不明其理,只是妄想以偶然的原因而得到成功或免去灾害,终究是不可能的。金丹之理非上述所说这些小术所能涵盖,其与天机暗合,只有圣人才有资格了解;某些人运用上述所说小术去炼还丹,虽自童稚之时即始,至于白发苍苍的老年,蹉跎岁月,也不能有所成功。或者炼丹有始无终,狐疑中道,心生怅望。乃至于得到金丹正传却背弃之,出正而入于邪径,背离大道而执守迷路;或执一法、一经、一诀以自足,以偏概全,此犹如以管窥天,其识见既不宽广,何足于与之论方来无穷之玄奥妙理呢!
若夫至圣章第三十五
【题解】
本章明天道微妙隐奥,非《易》象、《易》理不足以明之,非圣人迭起不足以阐述之;金丹之理法于《易》理,金丹之道无形难思,如果不示之以言,则后世无所取法,此乃所以作《周易参同契》的原因。
若夫至圣,不过伏牺,始画八卦,效法天地;文王帝之宗,结体演爻辞;夫子庶圣雄,《十翼》以辅之。三君天所挺,迭兴更御时[1]。优劣有步骤,功德不相殊;制作有所踵,推度审分铢;有形易忖量,无兆难虑谋;作事令可法,为世定诗书[2]。素无前识资,因师各悟之;皓若褰帷帐,瞋目登高台[3]。
【注释】
[1]“若夫”十句:伏牺效法天地变易之理,始画八卦,乃《易》之祖;周文王法伏牺所画八卦,重八卦之象而演成《周易》六十四卦并作卦爻之辞,于《易》而言,其功仅次于伏牺,实可以为《易》之宗;孔子踵伏牺、周文王而阐发《易》之理,遂作《十翼》,乃出身于庶民、百姓中的圣人、英雄,在当时虽无帝王之位,然而却成万世之师表。伏牺生于邃古,文王生于商末,孔子生于晚周,三位君子相继而兴起,演《易》以通天地万物之情,德配天地,为天地所推崇。因为天地虽大,难缄否泰之机;阴阳至虚无,涵藏动静之数,圣人因《易》明道,以之驾驭天地阴阳变化之机。结体,此处意指周文王将伏牺八经卦重叠为六十四卦。《十翼》,指《易传》,共七种十篇,计为《彖》上下篇、《象》上下篇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上下篇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,“翼”本意为鸟之羽翼,无羽翼则鸟不能飞翔,无《易传》之辅则《易》之经义不明;旧时认为,《易传》为孔子所作。结体,他本或作“修而”、“循而”。
[2]“优劣”八句:若论古今炼丹之法,其内容、方法、步骤各异,乃至于有优与劣、精致与简陋之分,然以济世之功德论之,则前圣与后圣并无差别。《周易参同契》之作,必假借《周易》之卦爻象和卦理以发明其说,亦可谓有所踵继,而不是凭空捏造,其推理、校度丹道之理极为详审,乃至于分、铢之细微亦必计较之。事之有形有兆者,可以忖量,可以虑谋;金丹大道乃无形无兆之理,不可忖量,不可虑谋。如果不示之以言,则后世无所取法,此乃之所以作《周易参同契》的原因。踵,接续之意。铢,计量单位,一斤药有三百八十四铢。忖(cǔn),揣度,思量,细想。兆,预兆。谋,计策。法,法则。诗,此处指记载炼丹法诀之古歌。书,此处指《周易参同契》。《周易参同契》详载丹道之理,乃推详古歌而作,非自出其意,犹如孔子删《诗》定《礼》。诗书,他本或作“此书”。经文中篇有“定录斯文”句,与此同意,则“诗书”或为“斯书”。量,他本或作“度”。
[3]素无前识资,因师各悟之;皓若褰(qiān)帷帐,瞋(chēn)目登高台:并非作《周易参同契》之人素有前识、预见之明,实乃因明师指点而觉悟大丹之理;一旦得其口诀,则群疑尽释,皓然明白若撩起帷帐而撤其掩蔽,豁然开朗如登高台而极目眺望旷远,心智为之开明,岂不大快!褰,撩起、揭起(衣服、账子等)。帷帐,用布、纱或绸子等做成的张挂在床上或屋子里防蚊、蝇和各种虫子的用具。各,他本或作“觉”、“学”。皓,他本或作“浩”。瞋,他本或作“瞑”。
【译文】
如果说到人中至圣,当首推伏牺,伏牺效法天地变易之理,始画八卦,乃《易》之祖;周文王虽身为帝王,他法则伏牺所画八卦,重八卦之象而演成《周易》六十四卦并作卦爻之辞,于《易》而言,其功仅次于伏牺,实可以为《易》之宗;孔子踵继伏牺、周文王的事业而阐发《易》之理,遂作《十翼》,乃出身于庶民、百姓中的圣人、英雄,虽在当时无帝王之位,然而却成万世之师表。伏牺生于邃古,文王生于商末,孔子生于晚周,三位君子相继而兴起,演《易》以通天地万物之情,德配天地,为天地所推崇。因为天地虽大,难缄否泰之机;阴阳至虚无,涵藏动静之数,圣人因《易》明道,以之驾驭天地阴阳变化之理。丹道炉火亦循此理,若论古今炼丹之法,其内容、方法、步骤各异,乃至于有优与劣、精致与简陋之分,然以济世之功德论之,则前圣与后圣并无差别;《周易参同契》之作,必假借《周易》之卦爻象和卦理以发明其说,对前圣之学可谓有所踵继而并非凭空捏造,其推理、校度丹道之理极为详审,乃至于分、铢之细微亦必计较之;因事之有形有兆者,可以忖量,可以虑谋,金丹大道乃无形无兆之理,不可忖量,不可虑谋;如果不示之以言,则后世无所取法,此乃之所以作《周易参同契》的原因。当然,这并非作《周易参同契》之人素有前识、预见之明,实乃因明师指点而觉悟大丹之道;炼丹之人一旦得其真诀,则群疑尽释,心智为之开明,皓然明白若撩起帷帐而撤其掩蔽,豁然开朗如登高台而极目眺望旷远。
《火记》六百篇章第三十六
【题解】
本章言著者撰述《周易参同契》的原因。
金丹大药虽有多方、旨趣各殊,终归一理,恐世人不能深思熟虑之,故文字郑重而说;然又怕泄漏天机,故举其宏纲,撮其机要,略述丹道之枝条,旨在使后人因言而会意,则不至于使丹道之理泯其所传。
《火记》六百篇,所趣等不殊[1]。文字郑重说,世人不熟思;寻度其源流,幽明本共居;窃为贤者谈,曷敢轻为书!若遂结舌瘖,绝道获罪诛;写情著竹帛,又恐泄天符[2]。犹豫增叹息,俯仰缀斯愚[3]。陶冶有法度,未忍悉陈敷。略述其纲纪,枝条见扶疏[4]。
【注释】
[1]《火记》六百篇,所趣等不殊:讲述炼丹时进退文、武火候功用的《火记》有六百篇,然其言语虽殊,而本旨却同;或谓《火记》是古之丹经,记载炼金丹大药的药方六百余条,然虽有多方、旨趣各殊,却终归一理;亦有谓《火记》六百篇,即前文所说《周易》除乾、坤、坎、离四卦之外的六十卦;六十卦表达一月火候之功,十个月则有六百篇。一月以六十卦喻火候之文、武,其所言之理皆同;十个月则有六百篇,篇篇亦相似,故其阐述的炼丹火候之旨趣皆相同而不殊异。
[2]“文字”十句:古仙、丹经对炼丹之理郑重阐述,无论鼎器之出处、产药之川原、火候之法度,言言彻底,字字着实,倾肝沥胆以告世人,世人却无暇熟思;然而探寻、校度丹道之理,穷其源而循其流,其所说皆不过一阴一阳之理而已;无论是幽深的天地之道,还是显明的人之道,皆循此理而行;当然,丹经所述丹道之理皆为世之贤者所备,著者岂肯轻为著述以钓私名、沽私誉!著者撰述此经时,态度亦很矛盾!如果结舌而噤无一语,则恐道脉不得承传而获罪;若将炼丹之实情尽著之于竹帛之中,则又恐所传非贤、轻易泄漏天机而受到天的谴责。幽明,“幽”喻指天地之道,“明”喻指人道。他本或脱“寻度其源流,幽明本共居”十字。瘖(yīn),缄默不作声。天符,天机、天道之理。轻为书,他本或作“诈为辞”、“诈伪词”。若遂结舌瘖,他本或作“结舌欲不语”。著,他本或作“寄”。又恐泄天符,他本或作“恐泄天之符”、“又恐泄天机”。
[3]犹豫增叹息,俯仰缀斯愚:于是,著者犹豫、叹息不已,俯仰思虑再三,缀撰此文,述丹道药物、火候之大略以告学者,旨在使后人因言而会意,则不至于使丹道之理泯其所传。缀,组合字句篇章,此处为作文之意。斯愚,他本或作“思虑”。
[4]陶冶有法度,未忍悉陈敷。略述其纲纪,枝条见扶疏:丹道有其陶冶的具体法度,著者既不敢明言,又不忍秘默不语,故于此经中举其宏纲,撮其机要,略述炼丹之纲纪,稍稍透露丹法之枝条,以备贤者参究之。
【译文】
讲述炼丹时进退文、武火候功用的《火记》有六百篇,然其言语虽殊,而本旨却同。古仙、丹经对炼丹之理郑重阐述,世人却无暇熟思;然而探寻、校度丹道之理,穷其源而循其流,其与幽深的天地之道和显明的人之道皆同;当然,丹经所述丹道之理皆为世之贤者所备,著者岂肯轻为著述以钓私名、沽私誉!著者撰述此经时,心理亦很纠结!如果闭口不谈,噤无一语,则恐道脉不得承传而获罪;若将炼丹之实情尽著之于竹帛经中,则又恐所传非贤、轻易泄漏天机而受到谴责。于是,著者犹豫、叹息不已,俯仰思虑再三,缀撰此文,述丹道药物、火候之大略以告学者,旨在使后人因言而会意,不至于使丹道之理泯其所传。丹道自有其陶冶的具体法度,著者于此既不敢明言,又不忍秘默不语,故举其宏纲,撮其机要,略述炼丹之纲纪,稍稍透露丹法之枝条,以备贤者参究。
以金为堤防章第三十七
【题解】
炼丹开始之发端、药物之铢两、临炉采取之妙、伏火之功,皆备载于此章。
自外丹言之,炼丹之初,要先下铅金入鼎炉中煅炼,后再投入流汞,铅金的功能犹如堤坝,能防止流汞渗漏、飞走、散失;但所用铅与汞之铢两、轻重应该平衡,一般情况下,铅金、流汞当各用一半。铅金、流汞二味为炼丹之真药,二者结合而产金砂,金砂产后,铅、汞所含药性并无所损。炼丹除用铅、汞两味药物之外,尚要有炉灶生火以烹炼之,炉灶以土垒成,鼎器内壁亦要涂上土,但炼丹只用铅金、流汞,而土则不入于丹。铅金之金、流汞之水外加炉火为三物,三物之性合会,则铅、汞二味相拘,发生神妙之变化。具体说来,鼎器中之药得火煅炼,先化为液体,然后变成蒸气熏蒸上腾,发出的声音犹如大车行于黄土之道上,故名之为“黄舆”。鼎中之汞、铅经过煅造,于鼎盖处结晶而成丹粉,其色如灰土,其状如明窗所附之尘。此时,当如下章所说,收取其药之粉末,更入鼎中以火炼之,其药色则渐变而为黄褐色,再变为红紫之色,如此则丹宝炼成。还丹既成,铅净、汞干,铅、汞原来之形态发生颠覆,此即本章经文所说“毁性伤寿年”和下章经文所说的“气索命将绝,休死亡魄魂”之意。
自内丹言之,炼丹必须先立堤防、牢镇六门,使精、炁、神不外泄,从而凝结成丹。于此章,“金”喻指人所具先天真一之精炁,以《周易》坎卦中之阳爻象之;“水”则喻指人心神的静定状态,以《周易》离卦中之阴爻象之;以先天真一之炁为堤防,人之心神得先天真一之炁相拘,就不能飞扬跋扈而流逸,从而神不外驰、神与炁相抱不离;以丹经术语言之,此则为“以金为堤防,水入乃优游”。先天真一之炁与心神静定之程度乃一一对应的关系,炁愈足则心神之静定程度愈深,而心神愈静定则先天真一之炁愈旺,《周易参同契》于此以一月变化之数喻之,如上半月十五天为阳长,喻先天真一之炁旺盛;下半月十五天阴长,喻神随炁旺而愈澄静,此即为“金计有十五,水数亦如之”。神与炁阴阳相配的关系,亦可以金、水五行成数喻之,金五行成数为九、水五行成数为六,金九、水六合计为十五;十五分中,水得六分,故说其五分有余;虽金九、水六数目不对等,但于此表达的却是金、水之平衡,喻神与炁相应而长。内丹以神与炁、精二者为真药,故说“二者以为真”;真药乃炼凡药而成,好比炁乃由精生,但炁虽蕴藏在精中,其真性并未因形态有异而改变,此则为“金重如本初”。内丹强调性命双修,由精可以炼炁,此通常谓之“修命”;炁又可以制伏神,神逐渐趋于虚无,此则谓之“炼性”;炁与神、命与性相合,又不能离开真意;三者之间作用、变化成神丹;五行中,木五行生数为三,火五行生数为二,内丹以“木”喻性,以“金”喻炁,以“火”喻神,神与炁初交,性尚隐而不显,故“其三遂不入”;神与炁相抱后,真性方能逐渐明朗,呈现出来,神不离炁,此则为“火二与之俱”。夜半子时,太阳在北方,虽隐而不见,然阳气开始节节增添;“太阳气”于内丹喻静定之后所产生的一阳来复现象,丹经亦谓之为“活子时”;此时人身之炁运行到下部尾闾之关,亦开始节节上升。一阳来复之时,阳炁在下,水火交媾,神、炁在真意的作用下氤氲相交,化而成液,蒸蒸而上,则金光满室,腾腾若车舆行于黄道之上,故号之“黄舆”;又因真意配脾土、其色为黄,真意摄载神、炁而升,亦可称“黄舆”;神、炁凝则结而成丹。真炁在体内周转,涤荡群阴之邪,内丹则用大小周天之说、河车运转之法以喻之,以此与天运相配。人身自有一周天,与天地无异,天运有始有终,人身真炁之运亦如此;至于息停脉住,则炼神还虚、炼虚合道,形下之寿年等事岂能萦于心怀、入于胸襟!内丹药物有清浊之分,真炁为清,化而为生殖之精则浊;丹法强调要取清弃浊,清者浮而在上,其状若明窗之尘;浊者沉而在下,其形体乃为灰土。
以金为堤防,水入乃优游[1]。金计有十五,水数亦如之[2]。临炉定铢两,五分水有余[3]。二者以为真,金重如本初[4]。其三遂不入,火二与之俱[5]。三物相合受,变化状若神[6]。下有太阳气,伏蒸须臾间[7]。先液而后凝,号曰黄舆焉[8]。岁月将欲讫,毁性伤寿年[9]。形体为灰土,状若明窗尘[10]。
【注释】
[1]以金为堤防,水入乃优游:先下铅金入鼎炉中煅炼,筑成金胎神室,后再投入流汞,流汞于铅金所界定的范围内优游;铅金的功能犹如堤坝,能防止流汞渗漏、飞走、散失。或谓“金”指九炼铅精所得之金花牙,以此为堤防能制汞;因金花芽能勾留汞,故称其为“堤防”;汞得金花相伴入,则相谐而无流失,故称“优游”,“优游”有舒缓不迫之意。或谓“水”本为“木”字,丹药以曾青有木之性。自内丹言之,炼丹必须先立堤防、牢镇六门,使精、炁、神不外泄,从而凝结成丹。“金”喻指人所具先天真一之精炁,以《周易》坎卦中之阳爻象之;坎乃乾之中爻入坤中而成,此阳爻来于乾金,坎为水、坎之中爻即“水中金”。“水”则喻指人心神的静定状态,以《周易》离卦中之阴爻象之,离乃坤之中爻入乾中而成,此阴爻来自于坤,坤有安静之意,因离汞虽喻心神之火,然心神之火亦有静定之性,此亦可喻为心所产之阴液,也即是“水”。坎之阳升则离之阴降,以先天真一之炁为堤防,则心神不外驰而得定;人之心神得先天真一之炁相拘,就不能飞扬跋扈而流逸,从而神与炁相抱不离。以丹经术语明之,则是“以金为堤防,水入乃优游”。入,他本或作“火”。
[2]金计有十五,水数亦如之:炼丹所用药物,其属性、质量应该阴阳平衡。如果用铅金之花十五两,则流汞、水银亦当用十五两之数,因流汞之性燥而难制,当以铅金止之,以阴制阳。十五,即指药物之重量为十五两;旧制一斤为十六两,十五两虽不足一斤之数,然两个十五两,合而为三十,却可以象一月三十日阴阳平衡之数。或谓“十五”,指十分中取其五的意思,喻药物当阴阳相配而平衡;又有谓水之成数六,金之成数九,六、九相加共成十五,亦明其阴阳相配之意,并非斤两之数。自内丹言之,先天真一之炁与心神静定之程度乃一一对应的关系。首先,炁愈足则心神之定愈深,而心神愈静定则先天真一之炁愈长;一月三十日中,十五日阳长阴消、十五日阴长阳消,神与炁亦如此,先天真一之炁愈旺,则心神愈静,心神愈静而炁愈壮。
[3]临炉定铢两,五分水有余:临炉炼丹之时,要确定药物的铢两、轻重。一般情况下,铅金、流汞各用一半,如果药物用铅金五分,其余则要配以流汞五分,此即经文所说“五分水有余”。或谓金九、水六,共十五数,十五数中,水得六数,为五分有余。铢,古代的重量单位,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为一铢。两,为古代的质量或重量单位,旧制十六两等于一斤,古代度量衡以三两为一分,五分即是十五两;如果用一斤十六两流汞与一斤铅相配,则也可以说其“五分有余”。神与炁阴阳相配的关系,亦可以金、水五行成数喻之,金五行成数为九、水五行成数为六,金九、水六合计为十五;十五分中,水得六分,故说其“五分有余”;虽金九、水六数目不对等,但于此表达的却是金、水之平衡,喻神与炁相应而长。
[4]二者以为真,金重如本初:铅金、流汞二者为炼丹之真药,二者结合而产金砂;铅金与流汞乃金砂之母,金砂产后,其与初时所用铅金、流汞药物之质量正相当,并无所损,所以说“金重如本初”。金、水二者为真药,故说“二者以为真”。内丹以神、炁二者为真药,故说“二者以为真”;真药乃炼凡药而成,好比炁乃由精生、识神中乃蕴有元神,但真药虽蕴藏在凡药中,其真性并未有所改变,此则为“金重如本初”。
[5]其三遂不入,火二与之俱:炼丹除用铅、汞两味药物之外,尚要有炉灶生火以烹炼之;炉灶以土垒成,鼎器内壁亦要涂上土,土所垒成之炉灶虽周回于鼎器之间,但鼎器内只存铅金、流汞,而土则不入于丹药的成分之中,此为“其三遂不入”;然炉灶之土虽不入鼎器,炉灶所生之火却时时煅烧鼎器,以促使药物发生变化而结成丹宝;五行生成之数,火之生数为二,故说“火二与之俱”。或谓“其三”,指五行生成之数中木的生数,其数为三,木生火以温鼎器,故木不入鼎;而木所生之火力则透入鼎器中,以烹炼丹药,火的生数为二,故火二与之俱。五行中,木五行生数为三,火五行生数为二,内丹以“木”喻性,以“金”喻炁,以“火”喻神,神与炁初交,性尚隐而不显,故“其三遂不入”;神与炁相抱后,真性方能逐渐明朗,呈现出来,神不离炁,此则为“火二与之俱”。三,他本或作“土”。入,他本或作“离”。
[6]三物相合受,变化状若神:铅金、流汞得火气烹炼、煅造,变化而成丹宝。其中,铅金之金、流汞之水,外加炉火为三物,三物之性合会,则铅、汞二味相拘,发生神妙之变化。内丹强调性命双修,由精可以炼炁,此通常谓之“修命”;炁又可以制伏神,神逐渐趋于虚无,此则谓之“炼性”;炁与神、命与性相合,又不能离开真意;三者之间作用、变化成神丹。三物相合受,他本或作“三物相含受”、“二物相含受”、“三物既合度”等。
[7]下有太阳气,伏蒸须臾(yú)间:鼎中有铅、汞之药,以鼎盖覆之;鼎下则以炉火炼之,药得火炼,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熏蒸上腾,发生变化。“太阳气”喻火,此言鼎下有火,火煅药成丹。合丹成败关键在火,火急则药可能走失、逃逸,火微则药亦不能化合而成丹。须臾,极短的时间,片刻。夜半子时,太阳在北方,虽隐而不见,然阳气开始节节增添。“太阳气”于内丹喻静定之后所产生的一阳来复现象,丹经亦谓之为“活子时”;此时人身之炁运行到下部尾闾之关,亦开始节节上升。
[8]先液而后凝,号曰黄舆焉:鼎中铅、汞药物得火煅烧,先化为液体,逼出金华,名为真铅;伏火之后,其液渐渐凝结,其色微带青黄,如黄金紫色;又炼丹起火之后,炉火于鼎器之下燃烧,鼎中铅、汞相熔化而成液,再由液体化而成蒸气,其气腾腾上升,发出的声音犹如大车行于黄道之上,故名之为“黄舆”。舆,大车。一阳来复之时,阳炁在下,水火交媾,神、炁在真意的作用下氤氲相交,化而成液,蒸蒸而上,则金光满室,腾腾若车舆行于黄道之上,故号之“黄舆”;又因真意配脾土、其色为黄,真意载神、炁而升,亦可称“黄舆”;神、炁凝则结而成丹。
[9]岁月将欲讫,毁性伤寿年:炼丹有其时序,到了一定的时候,便要伏火收丹;还丹既成,铅金、流汞原来之形态发生改变,亦即铅、汞之形态、寿年伤毁;或谓人服食丹宝后,岁月将讫,则消毁凡胎气性及有限寿年之阴质,体变纯阳,寿同天永,故说“岁月将欲讫,毁性伤寿年”。讫,事情完结,截止。真炁在体内周转、涤荡群阴之邪,内丹则用大小周天之说、河车运转之法以喻之,以此与天运相配。人身自有一周天,与天地无异,天运有始有终,人身真炁之运亦如此,此则为“岁月将欲讫”;至于息停脉住,则炼神还虚、炼虚合道,形下之寿年等事岂能萦于心怀、入于胸襟!此则为“毁性伤寿年”。或谓“下有太阳气,伏蒸须臾间”为丹道之进阳火,真炁于下丹田炁海发动,沿身后之督脉由尾闾、夹脊、玉枕节节升入于泥丸脑海;“先液而后凝,号曰黄舆焉”,为丹道之退阴符,真炁沿身前之任脉下降,经十二玉楼即喉管、膻中,入于下腹;《周易》中,坤卦可取象腹,大舆,也即大车,又取象黄色,故为“黄舆”。
[10]形体为灰土,状若明窗尘:在某一个阶段,鼎中之汞在铅的作用下,失其流汞之体,化而成粉,黑如死炭灰,轻如尘土,故药状如明窗上之尘灰;此时不能见黑便休,因其火气未足,当收取其药之粉末,更入鼎中以火炼之,以年、月长久之火养之,其药色渐变而为黄褐色,后又变为红紫之色,即变而成丹宝。内丹药物有清浊之分,真炁为清,化而为生殖之精则浊;丹法强调要取清弃浊,清者浮而在上,其状若明窗之尘;浊者沉而在下,其形体乃为灰土。或谓真炁在体内生成,感觉恍恍惚惚、窈窈冥冥,犹如《庄子》中的“野马”、“尘埃”之喻,故形容其貌为灰土,状若附于明窗上之尘埃。
【译文】
先下铅金入鼎炉中煅炼,后再投入流汞;铅金的功能犹如堤坝,流汞则于铅金所界定的范围内游走。如果用铅金之花十五两,则流汞、水银亦当用十五两;临炉炼丹之时,要确定药物的铢两、轻重,一般情况下,铅金、流汞各用一半,如果药物用铅金五分,其余则要配以流汞五分。铅金、流汞二者为炼丹之真药,二者结合而产金砂;金砂产后,与初时所用铅金、流汞药物之质量正相当,并无所损。五行中,木五行生数为三,火五行生数为二;炼丹时,以木生火、烹炼丹药,但以三为喻的木之质不能混入丹内,以二为喻的火之气则可以透入丹中。铅金、流汞得火气烹炼、煅造,变化而成丹宝;其中,铅金之金、流汞之液,外加炉火为三物,三物之性合会,则铅、汞二味相拘,发生神妙之变化。合丹成败关键在火,鼎下炉火适宜,药得火炼,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相熔化而成液体,再熏蒸成蒸气,蒸气腾腾上升,发出的声音犹如大车行于黄道之上,故名之为“黄舆”。炼丹有其时序,到了一定的时候,便要伏火收丹;还丹既成,铅金、流汞原来之状貌、形态发生颠覆性改变,其原有体状受到毁伤。具体说来,鼎中之汞在铅的作用下,失其流汞之体,化而成粉,黑如死炭灰,轻如明窗上所附之尘土。此时,不能见黑即止,当收取其药之粉末,更入鼎中以火炼之,其药色则渐变而为黄褐色,后又变为红紫之色,即化而成丹宝。
捣治并合之章第三十八
【题解】
本章承上章坎离相交之意,接着阐述乾坤交媾大还丹之法象。
自外丹言之,众药经初次煅造后,将之合聚于一处,细捣为末,按比例适度调配,再投入鼎中,以炉火煅炼之,鼎之色亦为之变而为赤红。金砂入鼎,当固济谨密,闭塞完坚,勿令有漏;炉下之火要常炎而不息,鼎中之药得炉火煅炼,历历作声,犹如婴儿之啼。运火以烹丹,需要视丹之老、嫩,调停火力,审察紧缓,谨慎调节鼎炉之寒温,不可有所轻慢。丹道进火,开始试用文火;作丹终竟之时,则须用武火收关;进退火候,应与天道十二辰阴阳升降之理同。火候经一周天之期,铅、汞之气索然消失,铅飞汞干,炉火伏灭,此时,大丹经过炉火煅造后,颜色变化成为紫金之色。还丹既成,服之一丸,量不须多,只要刀头、圭角一些子,其功效神妙不可思议!
自内丹言之,神与炁扭结在一团,相吞相咽,此为“捣治并合之”;金丹大药产在下丹田之坤腹,煅炼精纯则须升而至于乾首,乾首居上为鼎,坤腹居下为炉,通过猛烹极煅,则大药出于坤炉,倒行逆旋而升于乾鼎;药自坤升乾《周易·说卦》以乾卦象大赤之色,故说“持入赤色门”。内丹修炼,亦应塞兑闭门,固闭密护,真炁方不泄漏。炼药之初,凝神聚炁,调匀鼻息,惟使其绵绵续续,勿令间断,其息当深之又深,其意当静之又静,神久自凝,息久自定,虚极静笃,则神炁归元,此则为文火;至于一阳来复、运转河车,吸、舐、撮、闭,乾坤颠倒、龙虎交争,则当用武火烹之。运火以烹丹,需要视丹之老、嫩,调停火力,审察紧缓,谨慎调节鼎炉之寒温,不可有所轻慢,故文、武火候,于不同阶段当有所甄别。修至百脉归源,脉住气停,则大丹始结,此时,神、炁归根复命,神凝精结,八脉俱住,口鼻呼吸亦止,其气索然如绝。大丹既成,体化紫金之光,时时呈露,处处现前,其化为玉浆流入口中,则香甜清爽遍于舌端;吞之、服之入于五内,则脏腑通畅、身体康安,变化不测,神妙不可思议!
捣治并合之,持入赤色门[1]。固塞其际会,务令致完坚[2]。炎火张于下,昼夜声正勤[3]。始文使可修,终竟武乃陈[4]。候视加谨慎,审察调寒温[5]。周旋十二节,节尽更须亲[6]。气索命将绝,休死亡魄魂[7]。色转更为紫,赫然成还丹[8]。粉提以一丸,刀圭最为神[9]!
【注释】
[1]捣治并合之,持入赤色门:众药皆合聚于一处,经捣为末,调配之后,投入鼎中,以炉火煅炼之,鼎之色变而为赤红。“赤色门”指鼎;或谓此鼎以铅金之花涂之,则变而为赤;或将黄土捣为泥涂于鼎,或用赤盐覆鼎,鼎色变赤,故称之为“赤色门”。自内丹言之,神与炁扭结在一团,相吞相咽,捣治相合;金丹大药产在下丹田之坤腹,煅炼精纯则须升而至于乾首;乾首居上为鼎,坤腹居下为炉,通过猛烹极煅,则大药出于坤炉,倒行逆旋而升于乾鼎;药自坤升乾,《周易·说卦》以乾卦象大赤之色,故说“持入赤色门”。
[2]固塞其际会,务令致完坚:金砂入鼎,当固济谨密,闭塞完坚,勿令有漏。因鼎器有上下两釜,其上、下交接之处,皆当密闭之。自内丹言之,塞兑闭门、无思无为,方可以固济药物,使真炁不泄。固,封固。塞,窒塞。际会,鼎器上下之间。致,达至。
[3]炎火张于下,昼夜声正勤:炉下之火常炎,鼎中之药得炉火煅炼,历历作声,犹如婴儿之啼,啼声若停则火熄,火熄则丹药不成,故其火昼夜不得停熄。自内丹言之,神、炁相吞相咽,喻为龙虎相斗、龙虎交争;身体内发生种种变化,喻为龙吟虎啸之声;真意时时关照神、炁而不离,以昼夜不息之功喻之。昼夜,他本或作“龙虎”。
[4]始文使可修,终竟武乃陈:丹道中,文火乃发生之火,武火乃结实之火;丹道进火,开始试用文火,终竟之时,则须用武火收关。或谓修丹火候不能冒进,大药初生,先用文火调适之、含育之,使其刚柔不相抗,升腾而出炉;大药既生,则进武火以烹炼之,其火候共分三节,始则发武火以煅之,称之为“野战”;中则文火以养之,名之为“灌溉”;终则以烈火以成之,名之为“烹煎”。自内丹言之,炼药之初,凝神聚炁,调匀鼻息,使神炁归元,此时惟使其绵绵续续,勿令间断,然后神久自凝,息久自定,此则为文火;至于一阳来复,运转河车,吸、舐、撮、闭等采取之功,则当用武火。文、武火候,于不同阶段当有所甄别。
[5]候视加谨慎,审察调寒温:运火以烹丹,需要视丹之老、嫩,调停火力,审察紧缓,谨慎调节鼎炉之寒温,不可有所轻慢。寒温,指文、武火候。
[6]周旋十二节,节尽更须亲:十二节乃周天十二辰,天道阴阳进退,自子时而阳升,至午时而阴降,至于十二节尽,则天罡复指于子;丹道进退火候与之相应,犹如天道历十二辰而升降阴阳,故说“周旋十二节,节尽更须亲”。或谓十二节,即前文所说十二卦节,汉易卦气说以十二辟卦表征一年十二月阴阳二气升降之理,即自复卦一阳生,历临、泰、大壮、夬、乾为阳长阴消,阳至于极;自姤卦一阴生,历遁、否、观、剥、坤为阴长阳消,阴至于极;炼丹火候亦同此理,自复而乾、自姤而坤,阴极阳生、阳极阴生,六阴六阳,循环往复,终而复始。自内丹言之,十二节喻人身火候之方位。如火之发动,喻为一阳来复,或谓此为“冬至子之半”之时、发生方位则谓之“天根”,邵雍有“地逢雷处看天根”之诗;自尾闾、夹脊、玉枕,升而上之,或者自泥丸乾顶经十二重楼降而下之,于其间炁有停顿、积聚力量之时,喻之为卯、酉沐浴,或谓“春分之卯阳之中”“秋分之酉阴之中”;升入乾鼎,喻为“夏至之午”“阳之极”;阳极则阴生,以《周易》的姤卦象之,邵雍将之喻为“乾遇巽时观月窟”;至于降下黄庭、入于坤腹,则喻为“冬至之子”“阴之极”。须亲,他本或作“始元”、“亲观”。
[7]气索命将绝,休死亡魄魂:火候经一周天之期,铅、汞之气索然消失,炉火伏灭;铅、汞可分阴阳,阴为魄,阳为魂,魂日是汞,魄月为铅,铅飞汞干则阴阳俱废,魂消魄散,化而为大丹。气,此处指火。索,尽、灭之意。自内丹言之,修至百脉归源,脉住气停,则丹始结。此时,神、炁归根复命,神凝精结,八脉俱住,口鼻呼吸亦止,其气索然如绝。
[8]色转更为紫,赫然成还丹:经炉火煅造,丹药之颜色发生改变,变化成为紫金之色,此时,丹药赫然化成金丹。自内丹言之,丹要成熟,当通过运转河车、涤除杂质,九转火候数足,则还丹赫然光明,变化紫金之色。赫然,明盛之貌。还,还其本性之意。人禀道炁而生,服金丹则可复归于道,故名之为“还丹”。或谓“丹”乃赤色之意,“还”为返归之意。《道藏》容字号无名氏注本此句之后,“粉提以一丸,刀圭最为神”句前,尚有“阴阳相饮食,交感道自然”句。
[9]粉提以一丸,刀圭最为神:还丹既成,其色转而为紫赤;服之一丸,量不须多,只要刀头、圭角一些子,其功效神妙不可思议!粉,粉红之色;因还丹之正色为紫赤色,丹之色若不转紫赤,则不能称为大还丹;丹之色为黄赤,还不能称为还丹,只是小伏火之汞药,当要以火再炼,使丹之色转为紫赤。或谓“粉”乃细而微之物,“丸”乃圆而小之物;此处“粉”指金丹药粉,“提”是以指甲撮物,即从药粉中提取一些,和成药丸,故说“粉提以一丸”。刀圭,为刀头、圭角一些子之意,大约为十分之一方寸匕,喻丹药量不须多,只一些子而已。自内丹言之,金丹既成,色身之金光转紫,丹之状如紫粉,一刀圭许,时时呈露,处处现前,变化不测,神妙不可思议!其化为玉浆流入口中,则香甜清爽遍于舌端;吞之、服之入于五内,则脏腑通畅、身体康安。其解“刀圭”,亦颇有特色,坎、离药物皆因戊、己二土,方得和合而成纯乾之体,戊、己二土喻真意,坎、离药物喻神、炁,神、炁得真意调节方能和合成丹,故“圭”字从二土;“刀”则喻为金,“刀圭”则喻金、土两物,以真意炼药方能使之化为金丹。粉提以一丸,他本或作“粉提一刀圭”、“提粉以一元”、“服之以一丸”。刀圭,他本或作“九鼎”。
【译文】
将众药合聚于一处,细捣为末,按比例适度调配,投入鼎中,以炉火煅炼之,鼎之色亦为之变而为赤红。药物入鼎,当固济谨密,闭塞完坚,勿令有漏。炉下之火要常炎而不熄,鼎中之药得炉火煅炼,发生化合反应,历历作声,犹如婴儿之啼。丹道进火,开始试用文火;作丹终竟之时,则须用武火收关。烹炼时,需要视丹之老、嫩,调停火力,审察紧缓,谨慎调节鼎炉之寒温,不可有所轻慢。丹道进退火候,应与天道十二辰阴阳升降之理同,一个周期结束后,下一个周期再循环用之。丹道火候之功完毕,则铅飞汞干,铅魄、汞魂之气索然消失,炉火伏灭。此时,大丹经过炉火煅造,变化成紫金光明之色。还丹既成,从其粉末中撮取少量,和成一丸,量不须多,只要刀头、圭角一些子,其功效神妙不可思议!
推演五行数章第三十九
【题解】
本章言丹道药物相交感,虽变而不失其自然之理。
自外丹言之,丹药之性质可用五行的属性区分之,如果能推导、演绎五行之理,就可以知道炼丹之道其实简约而不复杂、繁难。外丹以“水”喻铅金之花,以“火”喻真汞,以金入汞,是以水激火;汞得铅制,伏而不动,其光明流转之性灭,故灭其光明。外丹又以“月”喻铅,以“日”喻汞,自然界中,日、月相互掩冒、蚀食,常于晦朔之间、阴阳交会之时;外丹铅、汞相交结,其理亦同于此,汞魂常起于月朔之晨,铅魄常终于月晦之暮,故铅汞相融、阴阳相禅、互相摄取之理,与天地阴阳交感之道相同。
自内丹言之,道自虚无生一气,此一气分而为阴阳,化而为三才、五行乃至于万物。人身之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五脏,可以对应精、神、魂、魄、意五炁;通过修炼,人身中五炁归于一炁、一炁归于道之本体,五炁朝元之理与五行相生、相克之理正同。如内丹常用“举水激火”“灭光明”喻人之识神得先天真一精、炁相制,不再心猿意马、纷扰杂乱而归于宁静;日、月食阴阳相掩,则喻神与炁、精相合;日、月交食常在晦朔之间,内丹所谓晦朔之间,乃意静神寂之时;故内丹神、炁相交,彼此相为制伏,其理与天地阴阳交感之道正同。
推演五行数,较约而不繁[1]。举水以激火,奄然灭光明[2]。日月相激薄,常在晦朔间[3]。水盛坎侵阳,火衰离昼昏[4]。阴阳相饮食,交感道自然[5]。
【注释】
[1]推演五行数,较约而不繁:如果能推导、演绎五行之理,就可以知道炼丹之道其实简约而不复杂、繁难。外丹认为,炼丹药物之性质可用五行的属性分之,如汞属水,朱砂属火,铅银属金,曾青属木,雄黄属土。但是,炼大丹唯用二物即铅金和汞,此二味丹药又自可以分五行,如铅之黑属水,银之白属金,如此等等。内丹常以“五行”为虚无之气,并以《周易·系辞》天地之数变化法则准之。《系辞》说:“天一、地二,天三、地四,天五、地六,天七、地八,天九、地十。”后世易学将其演为五行生成之数,即以“五”为土数,位居中央,合北方水一则成六,合南方火二则成七,合东方木三则成八,合西方金四则成九,以“九”为数之极,五居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之中,实为中数。至于土之成数十,乃北方之一、南方之二、东方之三、西方之四聚于中央而成。故中央之五散于四方则成水之六数、火之七数、木之八数、金之九数,所以水、火、木、金皆赖土而成;若以四方之一、二、三、四归于中央而成十,则水、火、木、金皆返本还元而会于土中。道教易学对此有颇多运用,如北宋张伯端《悟真篇》所说:“二物总因儿产母,五行全要入中央。”即发明此义。
[2]举水以激火,奄然灭光明:水喻铅金之花,火喻真汞,以金入汞,是以水激火;汞得铅制,伏而不动,其光明流转之性灭,故灭其光明。鼎内药物五行相克、相生,火兴则水退,水激则火衰。激,灌之意。灭光明,因水阴而火阳,以水灌火,阴盛灭阳,故说“灭光明”,内丹常用“举水激火”“灭光明”喻人之识神得先天真一精、炁相制,不再心猿意马、纷扰杂乱而归于宁静。五行数,他本或作“诠五行”。灭光明,他本或作“灭光荣”。
[3]日月相激薄,常在晦朔间:日掩月则月食,月掩日则日食,日、月食常发生在月末或月初。晦,月之尽。朔,月之初。外丹以“月”喻铅,以“日”喻汞,日月相互掩冒、蚀食,常于晦朔之间、阴阳交会之时。外丹铅、汞相交结,其理亦同于此。汞魂常起于月朔之晨,铅魄常终于月晦之暮。内丹药物只坎、离二味,精、炁与神而已;坎月而离日,日望月则月食,月掩日则日食,日、月食阴阳相掩,喻神与炁、精相合;日、月交食常在晦朔之间,此时,光明为黑暗所遮蔽,内丹所谓晦朔之间,乃意静神寂之时,此时坎阳已孕于其中。激薄,他本或作“薄蚀”。
[4]水盛坎侵阳,火衰离昼昏:坎为水、为月,离为火、为日。水盛则月掩日光,水能克火;火受水克,则火衰而当昼昏暗。此于外丹言之,当为铅、汞相融、阴阳相禅,互相摄取之意;于内丹言之,则为神、炁相交,彼此相为制伏之意。
[5]阴阳相饮食,交感道自然:阴阳相交感,乃天地自然之理;丹道铅、汞相感,其理亦如之。饮食,他本或作“吞食”、“啖食”。
【译文】
如果能推导、演绎五行之理,则知炼丹之道其实简约而不复杂、繁难。铅金之花为水,真汞为火,以铅金入汞,是以水激火;汞得铅制,伏而不动,其光明流转之火性灭,故失其光明。自然界中,日、月常于晦朔之间、阴阳交会之时相互掩冒、蚀食,发生日、月食现象。坎为水、为月,离为火、为日;水盛则月掩日光,水能克火;火受水克,则太阳之光衰而当昼昏暗;铅、汞相交结,其理与之相通。故铅汞相融、阴阳相禅、互相摄取之理,与天地阴阳交感之道相同。
名者以定情章第四十
【题解】
本章言《周易参同契》全书之要旨在于阐明“还丹”之义;认为此书非凿空浪说,所述乃古圣、先贤之意;嘱咐毋轻传非人,学人对之深思精审,则其理可昭然自得。
名者以定情,字者缘性言[1]。金来归性初,乃得称还丹[2]。吾不敢虚说,仿效圣人文[3]。古记题龙虎,黄帝美金华;淮南炼秋石,王阳加黄芽;贤者能持行,不肖毋与俱[4]。古今道犹一,对谈吐所谋[5]。学者加勉力,留连深思惟[6]。至要言甚露,昭昭不我欺[7]。
【注释】
[1]名者以定情,字者缘性言:名辞可以用来描述、确定事物之情状,字句可以用来仿效、表述事物之性质。《周易参同契》的概念、字词主要用来表述丹道铅、汞化合反应之情状、原理。于外丹言,“情”喻铅金,“性”喻流汞。内丹认为,人禀先天自然之道性、冲和之元炁而生,天赋予其性,化而为情,天赋予其炁,化而为精,内丹修炼要令之返还,通过炼精以化炁、灭情以复性,使情性合、神炁混而归元。内丹之上药,共有三品,即神与炁、精,性为元神之至静,情为元炁之至阳,《周易参同契》之字词、名言,不过就是阐明神与炁合一之旨,以丹道术语明之,就是明金情、木性之义以及如何合情、性为一;情复于性,则坎、离交媾,结成大丹。或谓寂然不动为性,感而遂通为情,名属情而字属性,名者定情为离求于坎,字者缘性为坎求于离;一说则谓古人缔结婚约有纳彩问名之礼,女子许嫁,则笄而加字,名者以定情,男求婚于女,丹道以之喻性摄情;字者缘性,女作配于男,丹道以之喻情来合性。《周易参同契》借男女婚姻之事,以喻丹道阴阳交感之义。
[2]金来归性初,乃得称还丹:铅金、流汞得火烹炼,伏火成丹,返还其原本所具之不灭金性,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“还丹”之义。或谓以铅伏汞,丹成,色转为朱,故名“还丹”;“丹”乃赤色之名,“还”有返归之义。亦有谓此乃为外还丹,尚有内还丹与之配合,即道教中所谓的还精补脑之术,后归到内丹术中。内丹以“情”喻金,即元炁,又称“金精”,或谓其为有、为魄、为坎中元炁,其本则为太阳真火,乃乾之阳爻降入坤阴之中而成;以“性”喻木,即元神,又称“木液”,或谓其为无、为魂、为离中元精,其本则为太阴真水,乃坤之阴爻融入乾阳之中而成,故内丹之道以坎水、离火为体,以金情、木性为用。张伯端《悟真篇》所谓:“金公本是东家子,送在西邻寄体生;认得唤来归舍养,配将姹女结亲情。”即是对《周易参同契》此说的发挥,陈抟、邵雍图书易学先天卦离东而坎西,亦与此相关。
[3]吾不敢虚说,仿效圣人文:《周易参同契》之理,非作者凿空驾虚以肆其臆说,乃是仿效圣人之著述,则其文而为之。
[4]“古记”六句:此“还丹”之名,古今名称皆有所不同。古书有称还丹为“龙虎”的说法,黄帝又美称其为“金花”,淮南王则以炼“秋石”为说,王阳则又名之为“黄芽”。但古记之龙虎、黄帝之金花、淮南之秋石、王阳之黄芽,无非托号以寓“还丹”之微意而已,其实无论古今,还丹之道皆共此一门径,只不过这些先真、圣人皆能持守其法而践行之,不肖者则不可以使之及于此道。古记,泛指古丹经。龙虎,一些丹经以其为铅金、流汞;或谓“虎”指铅金之花、“龙”是汞;或谓水银、朱砂有龙、虎之号,朱砂称“赤龙”,水银为“白虎”,如此名目甚多;也有注家以“龙虎”为古之丹经《龙虎上经》。金华,炼铅为汁、入汞所成之金花,其花五色,丹经或名之为“天地之符”,亦名“流珠”,因其能吸住流汞,勾制、相留,变化为丹,故黄帝唯重视此金花在炼丹中的作用。或谓其为矾石粉。淮南,指汉代的刘安,其为厉王之子,封于淮南,因以“淮南”为号。据说,刘安好道,感八公授其道法。秋石,将金花加入铅砂,一百日后,名为“秋石”;或谓金花属性为金,五行金配西方,西方为秋,故号为“秋石”。王阳,据说为汉代益州某刺史之名,生性好道,常炼金丹,并以黄白之法救人;其以金花、秋石难作,故烧黄丹,其效与金花同,王阳贵此黄丹,立其号为“黄芽”。黄芽,有注家认为即用错铅及黄丹、亦名“京丹”一斤,汞四两,入寿州瓷中,以猛火烧之,不久,化成液体,其平如镜,待其冷凝后,其色如黄金,将之打破后,其状如马牙,因号“黄芽”。古记,他本或作“先圣”。题,他本或作“提”、“显”。金华,他本或作“金花”。王阳,他本或作“玉阳”。黄芽,他本或作“黄牙”。
[5]古今道犹一,对谈吐所谋:年代虽殊,道并无二,自古及今,千经万论之源、千变万化之述,皆出于一道。《周易参同契》将炼丹之道和盘托出,后人读之,犹如与作者现场对话、谈论一般,可尽得其妙理。古今道犹一,他本或作“古今道由一”。吐所,他本或作“咄耳”、“咄所”。
[6]学者加勉力,留连深思惟:有志于学习炼丹之道者,要勤勉努力,留心于《周易参同契》之说,深思其理,反复玩味此书,一旦心领神会,则自能明白其中的炼丹要旨。
[7]至要言甚露,昭昭不我欺:《周易参同契》所述,皆炼丹的至要之言,其理昭然显露,无一毫之欺隐。昭,明白。不我欺,“不欺我”之倒装句。
【译文】
名辞、概念可以用来描述、确定事物之情状,字句可以用来仿效、表述事物之性质;《周易参同契》一书,其概念、字词主要用来表述还丹之情状、阐明其原理。铅金、流汞得火烹炼,伏火成丹,返还其原本所具之不灭金性,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“还丹”之义。我于《周易参同契》中所述还丹之理,非凿空驾虚以肆其臆说,乃是仿效圣人之著述,则其文意而为之。此“还丹”之道,古往今来,其称呼皆有所不同:古丹经有以“还丹”为“龙虎”的说法,黄帝又美称其为“金花”,淮南王以炼“秋石”为说,王阳则名之为“黄芽”,这些先真、贤达皆能持守其法而践行之,至于不肖者则不能使其及于此道。自古及今,千经万论之源、千变万化之述皆出于一道,《周易参同契》将此道和盘托出,后人读之,犹如与作者现场对话、谈论一般,可尽得其妙理。有志于学习炼丹之道者,要勤勉努力,留心于《周易参同契》之说,反复玩味此书,深思其理。当知此书所述,皆是涉于丹理的至要之言,其道昭然显露,并无一毫之欺隐。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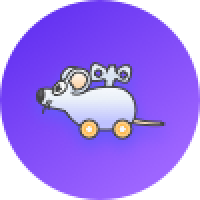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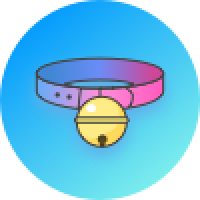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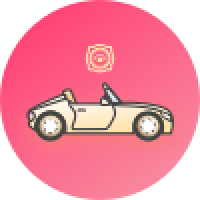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