惟昔圣贤章第七十九
【题解】
本章阐明《周易参同契》作者著作此书的目的:因忧虑、怜悯后学者不明丹道之蕴,故著此书以释其理,意在使后学者能循之而入于正道。
惟昔圣贤,怀玄抱真;服炼九鼎,化迹隐沦;含精养神,通德三光;津液腠理,筋骨致坚;众邪辟除,正气常存;累积长久,变形而仙[1]。忧悯后生,好道之伦;随傍风采,指画古文;著为图籍,开示后昆;露见枝条,隐藏本根;托号诸石,覆谬众文[2]。学者得之,韫椟终身;子继父业,孙踵祖先;传世迷惑,竟无见闻[3]。遂使宦者不仕,农夫失耘,商人弃货,志士家贫[4]。吾甚伤之!定录此文,字约易思,事省不繁,披列其条,核实可观,分两有数,因而相循;故为乱辞,孔窍其门,智者审思,用意参焉[5]。
【注释】
[1]“惟昔”十二句:过去的前贤、先圣,心怀丹道玄妙之理,抱负求真、去伪之志,烧炼、服食九鼎神丹,韬光养晦,隐居藏迹;收敛、涵养精神,聚丹药之精华、合丹药神妙之性,与日、月、星三光运转之法则相通达;故能达到使津液充盈于自己的五脏六腑、皮肤腠理之间的良好效果,使筋骨坚强,身上所存的各种阴邪之气都辟除干净,正气常存于身。如此积累的时间久长之后,就可以变化凡质,成为神仙。圣贤,或谓此圣贤指“三皇”,或谓即黄帝,相传黄帝铸九鼎于荆山而得道。还有谓指广成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列子等不同说法。此处之“圣贤”,应泛指历史上修丹的圣贤之人。怀玄抱真,心怀丹道具玄妙之理,抱负求真、去伪之志。内丹则以之为抱中守一、归根复命的养性之功;与下文“服炼九鼎”的养命之功相应。九鼎,相传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,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,铸造九鼎,将九州的名山大川、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,此鼎夏、商、周三代相继而传,后遗失不传,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谓:“禹收九牧之金,铸九鼎……周德衰,宋之社亡,鼎乃沦没,伏而不见。”《左传》则认为九鼎乃大禹的儿子启令人所铸。后人附会九鼎为:冀州鼎、兖州鼎、青州鼎、徐州鼎、扬州鼎、荆州鼎、豫州鼎、梁州鼎、雍州鼎,也有谓九鼎实则只有一鼎,此九鼎乃国家政权之象征,当不是《周易参同契》所说之“九鼎”。或谓炼丹之九鼎指天光鼎、地光鼎、人光鼎、日光鼎、月光鼎、星光鼎、风光鼎、音光鼎、灵光鼎;也有谓炼丹之九鼎,喻指火候之九转、方竟内丹之全功;或谓“九鼎”即金鼎,因为“九”在五行生成之数中为金之成数,而修炼外丹,鼎为金丹之室;或谓“九”为阳之终,“九鼎”喻纯阳之意。三光,字面意思指日、月、星三者所发之光,合而言之,应喻指日、月、星运行之法则。他本“三光”或作“三元”,认为“三元”指上、中、下三丹田;或上药三品的元精、元炁、元神;或谓仙分九品、丹列三元,“三元”指天元、地元、人元三品丹法,其中,“天元”谓之神丹,亦称“神符”,于丹鼎神室之中,追摄宇宙虚空元阳之炁的精华所得,无质而生质,其功效神妙莫测;“地元”谓之灵丹,通过炉火烧炼、点化而成的丹丸,服之可以助道;“人元”谓之大丹,通过阴阳得类、盗机逆用、含精养神,然后十月胎圆、婴儿显相,成就人元之丹,最后出神入化、复归虚无大道。腠(còu)理,皮肤、肌肉的纹理。服炼九鼎,他本或作“服食九鼎”、“伏炼九鼎”。化迹隐沦,他本或作“化洽无形”。通德三光,他本或作“通德三元”。津液腠理,他本或作“精液腠理”、“精溢腠理”。变形而仙,他本或作“化形而仙”。
[2]“忧悯”十句:前贤、往圣忧虑、怜悯后世修丹、学道之人趋入旁门、不得正道,于是随傍他们前辈的风采,依其所传之古文、丹经而指点、图解之,著成图书、典籍,以发明其理,开示、启发后学之人;在这个过程中,又不敢直言敷陈,于是便于所著述的图书、典籍中微微披露丹道的一些细枝末节,至于丹道之根本,则隐藏起来而未明言,并假托于五金、八石诸名词、术语,前后颠倒、错乱众章之节序、掩藏文本之真意。或谓此句意指作者忧心、可怜那些后生好道之人依傍古文、旁采经诀,对仙经妄行笺注,所谈皆细枝末节,不能突现丹道之根本,且通过假托金石之名,谬乱真经之意。伦,同类。随傍,依随,依傍。指画,“指”即指点,“画”即图解。图籍,“图”即图书,“籍”即典籍。后昆,子孙,后嗣。覆谬,“覆”有颠倒、掩盖之意,“谬”有错乱之意。由此也能解释何以《周易参同契》经文前后颠倒、重复、错乱之因。托号诸石,他本或作“托号诸名”。
[3]学者得之,韫(yùn)椟终身;子继父业,孙踵(zhǒng)祖先;传世迷惑,竟无见闻:后学者得到这些图书、典籍后,因不明其真意,便将之束之高阁、存于书匣之中,终身不能读之;如此而子继父、孙继子,子子孙孙世世迷惑,对于还丹妙理,竟不能有所闻见,更谈不上理解。韫椟,“韫”有包含、蕴藏之意,“椟”即匣子。踵,本意指脚后跟,引而申之,有跟随、效法之意。
[4]遂使宦者不仕,农夫失耘,商人弃货,志士家贫:导致有人读此书而不得其理,以假为真,徒竭精神,乃至做官之人放弃官职而不仕;农夫荒废田地而不耕耘;商人放弃财货而不求取;有志于炼丹者空竭货财,最后家贫如洗。
[5]“吾甚伤之”十二句:对于出现的这种种情况,我感到非常痛心!因此著录此书,字词尽管简约、容易理解,使炼丹之事简单而不繁难;因此,不仅于此书中披露、罗列炼丹之节次,也将丹道的基本内核、最真实的内容展示出来,丹道药物分、两之数亦有揭示,使后学者能因循此法而取得成功。故在此作总结性的概括,将丹道之法门略示其孔、窍,有智慧的人当审慎思考、用心参悟其理。乱辞,篇末总括全篇要旨的话,如《论语》有“关雎之乱”;《离骚》有所谓“乱曰”等等。或谓“乱辞”即谬乱之辞,作者之所以要错乱其辞,因不敢成篇漏泄丹道之理。定录此文,他本或作“定录此篇”。事省不繁,他本或作“事省不烦”。披列其条,他本或作“披列枝条”。核实可观,他本或作“实核可观”。
【译文】
过去的前贤、先圣,心怀丹道玄妙之理,抱负求真、去伪之志,烧炼、服食九鼎神丹,韬光养晦,隐居藏迹;收敛、涵养精神,聚丹药之精华、合丹药神妙之性,与日、月、星三光运转之法则相通达;故能达到使津液充盈于自己五脏六腑、皮肤腠理之间的良好效果,使自己筋骨坚强、身上所存各种阴邪之气都辟除干净,正气常存于身,如此积累的时间久长之后,他们就可以变化凡躯,成为神仙。这些往圣、前贤忧虑、怜悯后世修丹、学道之人趋入旁门、不得正道,于是随傍他们前辈的风采,依其所传之古文、丹经而指点、图解之,著成图书、典籍,以发明其理,开示、启发后学之人;在这个过程中,又不敢直言敷陈,于是便于所著述的图书、典籍中微微披露丹道的一些细枝末节,至于丹道之根本,则隐藏起来而未明言,并假托于五金、八石诸名词、术语,前后颠倒、错乱众章之节序、掩藏文本之真意。后学之人得到这些图书、典籍后,因不明其真意,便将之束之高阁,存于书匣之中,终身不能读之;如此而子继父、孙继子,子子孙孙世世迷惑,对于还丹妙理,竟不能有所闻见,更谈不上理解;甚至有人读此书而不得其理,以假为真,徒竭精神,乃至做官之人放弃官职而不仕;农夫荒废田地而不耕耘;商人放弃财货而不求取;导致有志于炼丹者最后空竭货财、家贫如洗。对于出现的这种种情况,我感到非常痛心!因此著录此书,字词尽管简约、容易理解,使炼丹之事简单而不繁难;故不仅于此书中披露、罗列炼丹之节次,亦将丹道的基本内核、最真实的内容展示出来,丹道药物分、两之数也有揭示,使后学者能因循此法而取得成功。所以,在此作总结性的概括,将丹道之法门略示其孔、窍,有智慧的人当审慎思考、用心参悟其理。
法象天地章第八十
【题解】
本章详论丹道火候运用之法度。
自外丹言之,炼丹时,火候之进退,不能有毫发差殊,如此则还丹九转,可保无咎;反之,火候进退失节,则鼎内铅、汞等金水失其性,如此就可能带来灾祸、凶咎。如果火候失调,鼎中铅、汞等金水逃逸,则需要以土来制止金水之流失;金水得土制之,改其过而归于正位,不敢逃逸。丹道以鼎、炉为关键,鼎炉固济不坚、不密,此为关楗未固,如此则鼎器泄漏;反之,则药物归鼎,如江淮之水自然东流入海,贼害乖戾之气自然远去。丹道之阳火以“寅”喻之,阴符以“申”喻之;阳火、阴符交替运用,如天地间阴阳之气迭为消长循环;炼丹当循北斗之转以定文、武火候。
自内丹言之,子时喻一阳生;一阳初动后,由子至于丑,阳炁达于尾闾,此以“河鼓临星纪”之象喻之;修行之人于此时用功,则要驱动阳炁、冲破尾闾之关,向上直奔,过夹脊、玉枕,入于头顶泥丸宫,因火候处于斩关寻找出路之时,为丹道中武火的运用,故行此武火之候,则一身中的精、炁激荡而流动,犹如人民被兵事而无不竦然惊骇。“晷影”喻火候,火候之进退,不能有毫发差殊,如此则还丹九转、可保无咎;反之,就可能带来灾祸、凶咎。“皇上”在内丹中喻神,其为君,“王者”喻精、炁,为臣;精、炁运行不循正轨,须由元神巡责其过,则精、炁自然退而改正。人身与天地相似,天关在上为首,心神居之;地轴在下为腹,精、炁居之;修行人若能上下相应,使居上之心神往下,居下之精、炁往上,则一低一昂,神与精、炁交媾,如火候合其法度,则周身害气奔走、灾祸自消。内丹之阳火虽胎在子,至寅方生;阴符虽胎在午,至申方生。天以北斗为机,人以心为机;斗居天之中,犹心居人身之中;内丹以心运火候,犹天以北斗运众星。
法象莫大乎天地兮,玄沟数万里[1]。河鼓临星纪兮,人民皆惊骇[2]。晷影妄前却兮,九年被凶咎[3]。皇上览视之兮,王者退自改[4]。关楗有低昂兮,害气遂奔走[5]。江淮之枯竭兮,水流注于海[6]。天地之雌雄兮,徘徊子与午[7]。寅申阴阳祖兮,出入复终始[8]。循斗而招摇兮,执衡定元纪[9]。
【注释】
[1]法象莫大乎天地兮,玄沟数万里:世间事物,最大者莫过于宇宙天地;宇宙天地间,有数万里的银河也即天河、玄沟的存在;然虽有天河、玄沟相隔,天地之间却仍然可以彼此相感、相通。丹道之理亦如此。自外丹言之,鼎器与炉灶,乃至炼丹的阴阳药物之间,皆可以取法天地之象;它们之间虽有界限,然天地之遥尚可以相感,何况鼎器交互相接、阴阳药物彼此相融,更加能够相互感通。或谓鼎炉法象天地,鼎与炉之间的缝隙犹如玄沟、天河,如果缝隙固济不密,则可能使药物渗漏、逃逸,如此则很细密的缝隙也犹如几万里的天河、玄沟一般宽阔。自内丹言之,人身以乾为首、以坤为腹,故头象天、腹象地,神居首而精、炁藏腹;使精、炁与神沿任、督二脉周天运转,则自然神入炁中,炁与神合;故人身之任、督二脉犹如天地之玄沟、天河,人能通此二脉,则真炁升降、上下灌注,百脉流通,无有壅滞之患;然欲使任、督二脉打通,须以修持功夫为其基础,犹如玄沟“数万里”而难渡过。法象,取法之对象。源自《周易·系辞》:“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,变通莫大乎四时,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。”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”玄沟,一作“互沟”,指天空中的银河。中国地处北半球,中国古代天文学认为,夏季的时候,银河从二十八宿中东方苍龙七宿的尾、箕,也即从天空的东北方向,至南方朱雀七宿的柳、星,也即天空的西南方向,划出一条分界线,将整个天空分作两半,犹如一条河流将两岸隔开。“银河”也称“云汉”、“天河”、“天汉”、“星河”、“银汉”等,是横跨星空的一条乳白色群星亮带,只在晴天夜晚可见,它由无数恒星的光引起,在天球上勾画出一条宽窄不一的束带。或谓“玄”有幽深、黑暗之意,“沟”即沟渎,《周易·说卦》“坎、陷也……坎为水,为沟渎,为隐伏”,故“玄沟”即坎卦之喻。玄沟数万里,他本或作“互沟数万里”。
[2]河鼓临星纪兮,人民皆惊骇:“河鼓”有三星,位于银河边上,星之位在二十八宿之斗、牛间,而“星纪”处黄道十二宫之丑位,位于北斗旁边;中国古代占星术认为,“河鼓”三星主兵事,“河鼓临星纪”意味着河鼓临北斗,则天下兵起、主有兵威,因此人民皆惊骇。因为兵有肃杀之意,与五行中金的属性相似,故此句于外丹言,可以喻鼎器之内的铅金等药物为火猛烈烹炼,有熔烁鼎器、药物倾覆、四散逃逸之凶险;“人民”喻药物,药物四散流失,以人民为兵之凶事所迫、四散奔逃比喻之。《周易·说卦》“离为火……为甲胄,为戈兵”,故“河鼓”或即离卦之喻,“河鼓临星纪兮,人民皆惊骇”,谓离当居下,“临星纪”则近北斗而居上,离火炎上、坎水润下,水火未济,如此则火候不合法度,导致鼎中药物散失。或谓“河鼓临星纪”,即传说中的牛郎与织女鹊桥相会,《岁时纪》说:“天河之东有织女,天帝怜其独处,许嫁河西牵牛郎,嫁后遂废织纴。天帝怒,责令归河东,使其一年一度相会。”于丹道言,此喻药物阴阳相交媾;“人民皆惊骇”,则喻指药物交媾时沸腾、翻滚的激烈状态。自内丹言之,子时喻一阳生;一阳初动后,由子至于丑,阳炁达于尾闾,此以“河鼓临星纪”之象喻之;修行之人于此时用功,则要驱动阳炁、冲破尾闾之关,向上直奔,过夹脊、玉枕,入于头顶泥丸宫。因火候处于斩关寻找出路之时,为丹道中武火的运用,故行此武火之候,则一身中的精、炁激荡而流动,犹如人民被兵事而无不竦然惊骇,故说“人民皆惊骇”;内丹常以“身”喻国家,以“心”喻君主,以“精、炁”喻人民。或谓“河鼓”在人则喻坎之精、炁,精、炁运转,犹如“河车”;“星纪”为北斗之分野,在人喻玉枕,“河鼓临星纪”,在人则喻运转河车、飞金晶,精、炁由下部之尾闾直逼玉枕,以达泥丸;“人民”譬喻一身精、炁,行周天之运转,精、炁必震动于身内,故以“惊骇”喻之。河鼓,星宿之名,一般认为河鼓有三星,在牵牛星之北,其中之大星为上将,左、右小星则为左、右将,主兵事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云:“河鼓大星,上将;左右,左右将。”唐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云:“河鼓三星,在牵牛北,主军鼓。盖天子三将军,中央大星大将军,其南左星左将军,其北右星右将军,所以备关梁而拒难也。”一种观点认为,“河鼓”即牵牛星,如唐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谓:“《尔雅》云:‘河鼓谓之牵牛。’”星纪,我国古代天文学为了量度日、月、行星的位置和运动,把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称之为“黄道”,黄道带可分成十二个部分,周围皆有星宿、星座,叫做“十二星次”,每个“星次”有若干星宿作为其标志;而“星纪”即“十二星次”之一,与十二辰相配为丑,与二十八宿相配为斗、牛、女三宿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八年》:“岁在星纪,而淫于玄枵。”杜预注:“岁,岁星也;星纪在丑,斗、牛之次;玄枵在子,虚、危之次。”《尔雅·释天》:“星纪,斗、牵牛也。”郭璞注:“牵牛、斗者,日、月、五星之所终始,故谓之星纪。”《晋书·天文志》:“自南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,于辰在丑,吴越之分野,属扬州。”如此则“星纪”所隶属之星有三,即“斗”、“牵牛”、“女”,而无“河鼓”;“河鼓临星纪”指河鼓越其次而至于“星纪”,如此,则河汉之内星宿错乱,中国古代占星术认为,此为水灾将兴之兆,故人民为之惊骇。星纪,他本或作“天纪”。
[3]晷(guǐ)影妄前却兮,九年被凶咎:如果晷影的进、退不合于法则,则表明天行失度、有可能导致灾难,如尧在位时的九年水灾之祸。丹道则以“晷影”喻火候,火候之进退,不能有毫发差殊,如此则还丹九转、可保无咎;反之,火候进退失节,不当前而妄前,不当却而妄却,则鼎内铅、汞等金水失其性,如此就可能带来灾祸、凶咎。晷影,或作“晷景”,即晷表所投射的日影,古人按照日影来测定时间,如《史记·天官书》说:“冬至短极……兰根出,泉水跃,略以知日至,要决晷景。”古人的计时仪器主要为圭表和日晷等,根据太阳在圭表、日晷仪等上面投射的日影长短的度数、投影的方位,即可以计时;如一年之中夏至日的日影最短、白昼最长,冬至日的日影最长、白昼最短;一日之内则正午时刻日影最短,如此等等。古人还认为,晷度变化与人事的吉凶休咎亦相联系。于丹道言,则“晷影”可喻进火、退火之时刻。前却,“前”即进,“却”即退,“前却”即进、退之意。或谓“前却”乃阻止使不前行之意。九年被凶咎,相传帝尧之时,有九年的洪水之灾。《尚书·尧典》亦说:“尧之时,洪水为患为甚。”丹道则以“九年”喻丹之九转,以“晷影”喻火候;晷影进退不合法度,喻丹道不循火候,则九转还丹不成,有凶险之事发生。晷影妄前却兮,他本或作“晷景忘前郤兮”、“晷景妄前却兮”。
[4]皇上览视之兮,王者退自改:相传帝尧命鲧治洪水之灾,九年而无成,帝尧知其任人有误,退而自改其过。或谓尧命鲧治水,鲧治水失败;后其子禹临危受命,自改其过而功成。外丹则以“皇上”喻土,“王”喻鼎中铅汞等金水,火候失调,鼎中铅、汞等金水逃逸,则需要以土来制止金水之流失;土镇则水不起,故鼎中金水得土制之,自改其过,归于正位而不逃逸。或谓“皇上”喻铅,“王者”喻汞,以铅制汞,亦合于君御其臣之道。自内丹言之,“皇上览视之”喻指修炼者运心神之火照入坎水精、炁之中,以逼出坎中之真阳,也即先天元阳之炁,此为进阳火。王者退自改,“王者”喻心神,“退自改”喻丹道之退阴符;一阴初萌为姤,此时宜闭关以自养,“系柅”以防履霜之渐,行此关闭之道不可不谨。或谓皇上为君喻神,王者为臣喻精、炁,精、炁运行不循正轨,须由元神巡责其过,则精、炁自然退而改正。或谓“皇上”喻指道心,“王者”喻指人心。皇上览视之兮,他本或作“皇上亲览视兮”。王者退自改,他本或作“王者退自后”。
[5]关楗有低昂兮,害气遂奔走:地球有南北二极、一高一下,旧时称为天关、地轴;地球昼夜运转不息,即所谓“回天关”、“转地轴”,故其南北两端乃为地球运转的关键之所;地球运转合于常轨,则各种因失常轨所带来的灾害就会消除。丹道以鼎、炉为关键,鼎炉或高、或低,固济不坚、不密,此为关楗未固,如此则鼎器泄漏,鼎中铅、汞等金水将随火气而奔走、逃逸。如果鼎炉高低、上下固济严密,则药物归鼎,如江淮之水自然东流入于海,贼害乖戾之气自然奔走远去。自内丹言之,人身与天地亦相似。天关在上为首,心神居之;地轴在下为腹,精、炁居之。修行人若能上下相应,使居上之心神往下,居下之精、炁往上,则一低一昂,神与精、炁交媾,火候合其法度,则害气奔走,灾祸自消。或谓火候失调,其低、昂或不定,则邪气得乘而害丹,导致丹鼎倾覆。关,要塞之门。楗,插门的木棍子;或作“键”,乃使门轴与门框固定的金属器件。害气,灾害之气。如以人身取譬而言,则为火水未济之象。关楗有低昂兮,他本或作“关键有低昂兮”。害气遂奔走,他本或作“同气而奔走”、“周天遂奔走”、“云气遂奔走”。
[6]江淮之枯竭兮,水流注于海:海乃百川所归之地,长江、淮河之水枯竭,因其水皆流注于大海。丹道则以之喻炼丹循其火候,合于法度,而丹药自然可以归元,生成金丹。或谓此句“之枯竭”当为“无枯竭”,“江淮”亦作“江河”,江河之水流注于海,不会枯竭,因名山、大川与洋、海相通,水气可以往来循环不已。内丹认为,人身亦同此理,元炁周流于全身,皆归于丹田炁海之中,结成金丹。江淮之枯竭兮,他本或作“江河无枯竭兮”。
[7]天地之雌雄兮,徘徊子与午: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,在子与午之间循环往复。因为子为六阳之首、阳气生于子,为冬至之时;午为六阴之首、阴气生于午,为夏至之时;阴阳二气由子至午、由午至子,循环往复。丹道以雌雄、阴阳二气喻药物,药物在鼎器中规范运转,此以“徘徊子午”喻之;或谓“雌雄”喻药物的真阴、真阳,此真阳产于子、真阴产于午,因子、午二时方能产成真药,故说“徘徊子与午”。自内丹言之,则子时一阳初复,此时阳气尚微,宜闭关以养此微阳;午时一阴初萌,此时当“系金柅”以防履霜、坚冰。或谓子午为阴阳相交、相会之地,日月至此而徘徊;以丹道言之,神与炁、精或上升、或下降,一起一伏,亦徘徊于乾首与坤腹的子、午之间,与天地造化同此原理。雌雄,指阴阳二气,丹道以之喻药物。徘徊,在某个范围内来回波动、起伏,或在某个地方来回走动,此即为徘徊。古人称太阳处中天的正午为“停午”,“停”亦有徘徊之意。天地之雌雄兮,他本或作“天地之雄雌兮”。
[8]寅申阴阳祖兮,出入复终始:以地球北半球而言,北斗斗杓指东方寅位而天下为春,阳气自此而发生,畅万物以出;斗杓指西方申位而天下为秋,阴气自此而肃杀,敛万物以入,故寅、申实为阴阳二气之祖、万物出入之门。以丹道言之,“寅申阴阳祖”,则阳火以“寅”喻之,阴符以“申”喻之;阳火、阴符交替运用,如天地间阴阳之气迭为消长循环,故说“出入复终始”。或谓阳火虽胎在子,至寅方生,阴符虽胎在午,至申方生;太阳为阳之精,故出于东方寅位而没于西方申位,月亮为阴之精,故出于西方申位而没于东北之方、与寅位相近之处。又《周易参同契》论月体纳甲,因月出西南庚方,象震之一阳初动,故丹道以之喻阳火发生之象;月始消于西南辛方,象巽之一阴初起,故丹道以之喻阴符发生之象。如以先天卦位论之,则震居东方寅位,巽居西南申位,如此则寅、申为阴阳二气之始;月出寅而入申,入而复出,故说“出入复终始”。寅申阴阳祖兮,他本或作“寅申阴阳之祖兮”。出入复终始,他本或作“出入终复始”。
[9]循斗而招摇兮,执衡定元纪:循北斗七星之斗柄,执持斗杓之玉衡,运转众星,定其轨则。以外丹言之,铅、汞之金水得火气烹炼,在鼎中沸腾运转,其状如众星随斗而旋转一般;在这个过程中,以铅金执汞,可定丹之纲纪。或谓炼丹当循斗以用文、武火候,循斗极运转,以定丹道纳甲之火候,故说“执衡定元纪”。以内丹言之,天以斗为机,人以心为机;斗居天之中,犹心居人身之中;丹法以心运火候,犹天以斗运十二辰。人身之天罡所指起于子时一阳初动,然后,运转河车,精、炁周流于一身,如北斗斗柄所指,遍历十二辰。斗,即北斗。在天文学上,北斗有七星,第一星名天枢,第二星名璇,第三星名玑,第四星名权,第五星名衡,第六星名开阳,第七星名瑶(摇)光,其中,第一至第四星组合为“魁”,第五至第七星组合为“标”(杓),合魁、杓而为北斗,“魁”为“斗”之首,“杓”为“斗”之尾。北斗之杓,与二十八宿之东方苍龙宿的龙角相连;北斗之中为衡,与南斗相对,南斗有六星;北斗之首为“魁”,枕于西方参宿之首。如《史记·天官书》说:“北斗七星,所谓旋、玑、玉衡以齐七政。杓携龙角,衡殷南斗,魁枕参首;用昏建者杓,杓自华以西南;夜半建者衡,衡殷中州河济之间;平旦建者魁,魁海岱似东北也。”又说:“斗为帝车,运于中央,临制四乡。分阴阳,建四时,均五行,移节度,定诸纪,皆系于斗。”《史记索隐》曰:“《春秋运斗枢》云:斗,第一天枢,第二旋,第三玑,第四权,第五衡,第六开阳,第七摇光。第一至第四为魁,第五至第七为標,合而为斗。”中国古代占星术认为,北斗七星可以使一年四季春、夏、秋、冬顺时而更迭,不仅如此,还可以使天文、地理、人道皆合于其序而运转。招摇,乃北斗之斗柄,即北斗第五至第七星。衡,即北斗之第五星,北斗斗柄起于第五星衡。元纪,北斗为众星之纲纪,故称之为“元纪”。或谓“元纪”乃“元星君”、“纪星君”,为北斗中之星名,具体所指则不详。
【译文】
世间事物最大者莫过于宇宙天地;宇宙天地间,有数万里的银河也即天河、玄沟的存在;然虽有天河、玄沟相隔,遥远的天地之间却仍然可以彼此相感、相通。丹道之理亦如此,鼎器与炉灶,乃至炼丹的阴阳药物之间虽有界限,也能够相互感通。“河鼓”三星位于银河边上,“星纪”处黄道十二宫之丑位、近北斗;河鼓接近星纪则天下兵起,兵有肃杀之意,因此人民皆惊骇;“人民”喻药物,鼎器之内的铅金等药物为火猛烈烹炼,有熔烁鼎器、药物倾覆、四散逃逸之凶险,犹如人民为兵之凶事所迫、四散奔逃。如果晷影的进、退不合于法则,则表明天行失度,有可能导致灾难,如尧在位时的九年水灾之祸;丹道火候进退失节,不当前而妄前,不当却而妄却,则鼎内铅、汞等金水失其性,如此也可能带来炼丹的灾祸、凶咎。相传帝尧命鲧治洪水之灾而无成,帝尧知其任人有误,故退而自改其过;丹道则以“皇上”喻土,“王”喻鼎中铅、汞等金水,火候失调,鼎中铅、汞等金水逃逸,若得土制之,则能自改其过、归于正位而不逃逸。地球南北二极即所谓天关、地轴,天关、地轴一高一低,乃地球运转的关键之所,地球运转合于常轨,则各种因失常轨所带来的灾害就会消除;丹道以鼎、炉为关键,鼎炉或高、或低,固济不坚、不密,此为关楗未固,如此则鼎器泄漏,鼎中铅、汞等金水将随火气而奔走、逃逸。海乃百川所归之地,长江、淮河之水枯竭,因其水皆流注于大海;丹道则以之喻炼丹循其火候,合于法度,而丹药自然可以归元、生成金丹。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由子至午、由午至子,循环往复,药物在鼎器中往返运转,亦同于此理。在地球的北半球,北斗斗杓指东方寅位而天下为春,阳气自此而发生、畅万物以出;斗杓指西方申位而天下为秋,阴气自此而肃杀、敛万物以入,故寅、申实为阴阳二气之祖、万物出入之门;丹道之阳火以寅喻之,阴符以申喻之,阳火、阴符交替运用,亦如天地间阴阳二气迭为消长循环。北斗七星之斗柄斡旋,能够运转众星、定其轨则;鼎中铅、汞之金水得火气烹炼、沸腾运转,其状亦如众星随北斗而旋转一般;在这个过程中,以铅金执汞,可定丹之纲纪。
升熬于甑山章第八十一
【题解】
本章主要阐明丹道药物交媾之景象。
自外丹言之,此章内容主要揭示鼎中铅、汞等金水变化之状,尽显其形仪,以示金丹成象之状貌。炼丹的鼎与炉灶接连,犹如炊事所用的甑子一般;炎炎炉火在下面发起,鼎中铅金得火烹炼,化为液体,将丹砂注入鼎中,与铅液相调和,汞得铅伏,犹如朱雀之鸟为“罗网”所罩。铅、汞在鼎器中发生化学反应,发出如婴儿恋母而啼哭一般的声音。经过不到半个刻漏时间的火符,鼎中药物开始发生种种变化,就形状而言,或呈鱼鳞之状,或如动物颈背上的长毛或长鳍那般密集杂陈、重叠相接;就颜色而言,药物也发生着丰富多彩的变化;就形态而言,因得炉火烹炼,药物先化为液态,在鼎中如水、云般急速涌沸、翻冒,上下滚动而不止息;慢慢地,药物开始凝结,相交、相结,重叠、累积,如犬牙相交错的样子;又如严冬所结之坚冰,还似溶洞中悬在洞顶上纵横交叉、参差错落的钟乳石;或如巍巍耸起、高低错落有致的土石之山,交相累积在一起,支柱于鼎器之中。
自内丹言之,“甑山”喻头顶昆仑、藏神之所,“熬”即前文所说“白虎熬枢”,喻先天阳炁,先天阳炁发动,如虎长啸,神与炁相抱、如龙之吟。朱雀之火喻人的心识;人的心识常易向外发散、不易集中,故以“飞扬”“翱翔”的“朱雀”喻之。修行人要制伏自己的散乱神识,即所谓制心一念,这要以精、炁摄引之,使向外发散的神识逆而向内,这就好比是飞扬、翱翔于天空的朱雀为罗网所罩、所压,而不得飞走一般;神与炁、精相扭结,本性炎上的神识之火颠倒向下,本性润下的精、炁之水运而向上,在丹田、炁海相聚,则精、炁与神在丹田中交媾、身内震动,此以婴儿恋母的啼哭声以喻之。“漏刻未过半”喻一阳初动后,真炁至尾闾,即将运转河车之时;“鱼鳞”为水生动物所有,喻坎之真精,“狎鬣起”喻指坎之真精将循后背之夹脊、脑后之玉枕进而上升。人的心识幻化之象可以朱雀五彩羽毛之色比喻,心遇外物牵引,易于散乱,故谓其“变化无常主”;然得充盈精、炁之水以制心识之火,则火为水制,炁定而神闭。神与炁于昆仑、泥丸头顶交媾即毕,降落于中宫黄庭,先液而后凝,渐凝渐结,无质生质,犹如犬牙之相错,又如严冬之坚冰,还如交错杂陈之钟乳,变化结成丹宝。
升熬于甑山兮,炎火张设下;白虎唱导前兮,苍液和于后[1]。朱雀翱翔戏兮,飞扬色五彩;遭遇罗网施兮,压之不得举;嗷嗷声甚悲兮,婴儿之慕母;颠倒就汤镬兮,摧折伤毛羽[2]。漏刻未过半兮,鱼鳞狎鬣起;五色象炫燿兮,变化无常主;潏潏鼎沸驰兮,暴涌不休止;接连重叠累兮,犬牙相错距;形如仲冬冰兮,阑干吐钟乳;崔嵬而杂厕兮,交积相支拄[3]。
【注释】
[1]升熬于甑(zèng)山兮,炎火张设下;白虎唱导前兮,苍液和于后:将炼丹的鼎器升举起来,安放在炉灶之上;鼎与炉灶接连,犹如炊事所用的甑子一般,高高耸立如山;炎炎炉火在下面的灶穴中生起,鼎中的铅金得火烹炼,先化为液体,然后将丹砂注入鼎中,与铅液相调和。自内丹言之,“甑山”喻头顶昆仑、藏神之所,“熬”即前文所说“白虎熬枢”,喻先天阳炁,因先天阳炁在下丹田培养、积聚久之,方能发生,故谓之“熬”。先天阳炁先发动,如虎长啸,神与炁相抱,如龙之吟;当此之时,当急发武火、集中精神,驾动河车、运转周天,自尾闾穴将其逆运入泥丸头顶,此即“炎火张设”、“升熬甑山”;其升上之时,修炼者腹部下丹田如金炉火炽,头项玉鼎如沸汤相煎。熬,为了提取有效成分或去掉杂质,将丹药放在鼎器里熬煮。或谓此句中的“熬”喻炼丹之鼎,如前文所说之“熬枢”。甑山,甑,也称“甑子”,是古代的一种炊具,略像木桶,底部有许多小孔,放在鬲(lì)上蒸食物,鬲的样子像鼎,合鬲与甑即为甗(yǎn),甗的功能略似现在的蒸锅。在此句中,“甑山”即炼丹之鼎炉。或谓“熬”喻炼丹之鼎,“甑山”则喻炉灶;鼎居炉灶之上,炉坛与鼎相接连,高耸若山之形,故以“甑山”喻之。炎火,熊熊大火。丹道以之喻武火,与绵绵若存之文火相对应。白虎,四象之一,居西方,五行配金。外丹以之喻铅金,内丹则以之喻精、炁。或谓“白虎”喻指肺液。朱熹曾谓“虎”一作“礜”、一作“矾”,然下文有朱鸟,则此当为“虎”。苍液,或谓即“苍龙”,四象之一,居东方,五行配木。外丹以之喻丹砂,因五行中,木的方位属东,木生火,丹砂色赤,故其也被称为“东方木精”。内丹以之喻心神。或谓“苍液”喻指肝液。炎火张设下,他本或作“炎火张于下”。白虎唱导前兮,他本或作“白虎倡导前兮”。苍液和于后,他本或作“苍龙和于后”。
[2]“朱雀”八句:汞出自丹砂,丹道以“朱雀”喻汞;汞之色闪闪发亮,性最易飞走、逃逸,故以“朱雀翱翔戏兮,飞扬色五彩”形容之;炼丹要伏汞,通常以铅液制之,汞得铅伏,犹如朱雀之鸟为“罗网”所罩,不能自由翱翔;因汞易飞走、蒸发,且汞之蒸汽对人体有毒副作用,故伏汞时,要将汞、铅置于密封的鼎器中,此亦有“罗网”之意,故经文说“遭遇罗网施兮,压之不得举”;以炉火烹炼汞、铅,使它们在鼎器中发生化学反应,在这个过程中,会发出如婴儿恋母而啼哭一般的声音,此即“嗷嗷声甚悲兮,婴儿之慕母”;汞性本飞扬,然其为铅所制,则安处于鼎器之内,不再逃逸,在与铅发生化学反应的过程中,汞闪闪发光的颜色亦发生变更,此犹如朱雀“颠倒就汤镬兮,摧折伤毛羽”。或谓汞处鼎器之内,鼎器四周设四神以镇伏之;鼎器内壁涂抹有土,合四神与土成五行,共为罗网,镇压汞于炉器之内,令其不得飞走。汞为火所烹,于鼎器内变化无常,或作婴儿恋母而啼之声,其色发生变化,又像鸟儿摧折其毛羽。还有谓朱雀于丹道可喻炉火,风鼓炉中之火,炎炎燃烧,如朱雀的羽毛,呈五彩之色。炉火炎上,聚其热量于鼎下,鼎炉固济紧密,阴阳药物处其中,如鸟为网罗所罩;阴阳药物相互之间发生化学反应,时有如婴儿恋母般的嗷嗷悲声发出;最终,药物相互结合,又如婴儿之依依恋母;“摧折伤毛羽”则喻鼎中药物因化学反应而色变。自内丹言之,朱雀之火喻人的心识;人的心识常易向外发散,不易集中,故以“飞扬”“翱翔”的“朱雀”喻之。修行人要制伏自己的散乱心识,即所谓制心一念,这要以精、炁吸引之,使向外发散的心识逆而向内,这就好比是飞扬、翱翔于天空的朱雀为罗网所罩、所压,而不得飞走一般;神与炁、精相扭结,本性炎上的心识之火颠倒向下,本性润下的精、炁之水运而向上,在丹田、炁海相聚,则精、炁与神在丹田中交媾、身内震动,此以婴儿恋母的啼哭声喻之。神被炁、精所招摄,不再向外发散,犹如朱雀被网罗压止而不得飞举,只能敛身束羽伏于鼎中,从而修炼人达到制心一念、恢复清静本性的效果。或谓“朱雀”乃喻指心识,心识五花八门,故以“五彩”象之,心识属离火,火得精、炁之坎水制之,如朱雀之遇罗网,故离火之心识只得与苍液木母之真性相恋,而安处在身内。如以五行生克论之,则白虎属金,苍液属木,朱雀属火。人之清静本性生心之意识,心识易散乱、昏沉,此以木生火、火性炎上喻之。木之性情生神识之火,心识之火其性炎上、飞走;然炁足则精满,精、炁充盈则有利于心性澄清,炁足精满以“金生水”喻之,精、炁足则性澄以“金克木”喻之。故丹经以金克木、金生水以制朱雀之火,喻以精、炁摄制心神;朱雀遇罗网不得飞举,火既不得生,复归于木,心识自然复归清静本性。或谓人之心识易妄动,故以“朱雀翱翔戏兮,飞扬色五彩”喻之;修内丹要尽克己之功,惩忿窒欲,不使心识妄动,故以“遭遇罗网施兮,压之不得举”喻之;心识之火不妄动,燥性消去,自然情复于性,情性如母子般相依不离,故以“嗷嗷声甚悲兮,婴儿之慕母”喻之;炼己至于无己之时,自然心神之火下降、精炁之真水升上,神不外驰而炁自定,故以“颠倒就汤镬兮,摧折伤毛羽”喻之。朱雀,四象之一,居南方,五行配火。外丹以之喻汞,内丹以之喻心识。翱翔,形容鸟儿在空中展翅、回旋飞翔的样子。五彩,木之青、火之赤、金之白、水之黑居四方,土之黄居中央,此即“五彩”之色。内丹以“五彩”喻心神之识散乱、复杂,心识之幻化如朱雀羽毛的五彩之色。罗网,捕鸟的大网。外丹以之喻铅,因铅能制汞;汞性飞扬,常以朱雀、朱鸟来比喻。内丹以之喻精、炁,因精、炁充盈,利于摄住心识,故修炼者常以真一之精、炁,以养虚灵之神。嗷嗷(áo),哀号,喊叫。颠倒,铅、汞之液得火相烹,上下翻滚。内丹则认为神火向下,精、炁升上为水上火下、坎离颠倒。汤镬(huò),“镬”为大锅;“汤镬”乃古代的一种残酷刑具,即将犯人投入沸腾、滚烫的大锅中。朱雀翱翔戏兮,《道藏》彭晓本此句作“朱雀翱翔亏兮”,《四库全书》彭本则作“朱雀翱翔戏兮”,现据四库本改;另外,他本此句或作“朱鸟翱翔戏兮”。遭遇罗网施兮,他本或作“遭遇网罗施兮”。压之不得举,他本或作“压止不得举”。嗷嗷声甚悲兮,他本或作“谑谑声甚悲兮”。
[3]“漏刻”十二句:经过不到半个刻漏时间的火符,鼎中药物开始发生种种变化,就形状而言,或呈鱼鳞之状,或如动物颈背上的长毛或长鳍那般密集杂陈、重叠相接;就颜色而言,药物也发生着丰富多彩的变化,五颜六色、鲜艳夺目,无不变之常色。就形态而言,因得炉火烹炼,药物化为液态,在鼎中如水、云般急速涌沸、翻冒,上下滚动而不止息;慢慢地,药物开始凝结,相交、相结,重叠、累积,如犬牙相交错的样子;又如严冬所结之坚冰,还似溶洞中悬在洞顶上纵横交叉、参差错落的钟乳石;或如巍巍耸起、高低错落有致的土石之山,交相累积在一起,支柱于鼎器之中。丹道以此来揭示鼎中铅、汞等金水变化之状,尽显其形仪,以示金丹成象之状貌。自内丹言之,“漏刻未过半”喻一阳初动后,真炁至尾闾,即将运转河车之时;“鱼鳞”为水生动物所有,喻坎之真精;“狎鬣起”喻指坎之真精将循后背之夹脊、脑后之玉枕进而上升。人的心识幻化之象可以朱雀的五彩羽毛之色喻之,心遇外物牵引,易于散乱,故谓其“变化无常主”;然得充盈精、炁之水以制心神之火,则火为水制,炁定而神闭,故说“潏潏鼎沸驰兮,暴涌不休止”。神与炁于昆仑、泥丸头顶交媾即毕,降落于中宫黄庭,先液而后凝,渐凝渐结,无质生质,犹如犬牙之相错,又如严冬之坚冰,还如交错杂陈之钟乳,变化结成丹宝。漏刻,即漏壶,乃古代计时之器具,用铜制成,分播水壶、受水壶两部分。播水壶分为二至四层,底部均有小孔可以滴水,水最后流入受水壶。受水壶里有立箭,箭上有刻度,刻度在标示蓄水量的同时,即可以用来计算时间。漏壶也有不用水而用沙的,也称之为“漏刻”,简称“漏”。狎鬣(liè),“狎”乃亲近之意,“鬣”指某些动物颈背上的长毛或长鳍;“狎鬣”意指如某些动物颈背上的长毛或长鳍那样密集杂陈、重叠相接。潏潏(jué),液态物涌流之状。暴涌,指水、云或与之相类似者急骤冒出,向上翻滚、升腾的样子。《道藏》彭晓本“涌”作“勇”错距,交叉罗列之意。阑干,形容纵横交叉、参差错落的样子;或谓指美石而次于玉者。钟乳,溶洞中悬在洞顶上的像冰锥的物体,与石笋上下相对,由碳酸钙逐渐从水溶液中析出、积聚而成。崔嵬(cuī wéi),有石头的土山,或形容某物高大、高峻、高耸。杂厕,“厕”即杂之意,“杂厕”指长短参差、错落有致之意。支拄,支撑之意。漏刻未过半兮,他本或作“刻漏未过半兮”。鱼鳞狎鬣起,他本或作“鱼鳞狎獵起”、“龙鳞狎獵起”、“龙鳞甲鬣起”。五色象炫燿兮,他本或作“五色象玄耀兮”。接连重叠累兮,他本或作“杂还重叠累兮”。犬牙相错距,他本或作“犬牙相错拒”。崔嵬而杂厕兮,他本或作“崔嵬以杂厕兮”。交积相支拄,他本或作“累积相支拄”、“交精相支拄”。
【译文】
将炼丹鼎器升举起来,安放在炉灶之上,鼎与炉灶接连,犹如炊事所用的甑子一般,高耸如山;炎炎炉火在下面灶穴中生起,鼎中铅金得火烹炼,先化为液体;此后,将丹砂注入鼎中,与铅液相调和。从丹砂中可以析出流汞,丹道以朱雀喻之;流汞能反射各色之光,其性最易飞走、逃逸,故以“朱雀翱翔戏兮,飞扬色五彩”形容之。汞得铅伏,犹如朱雀之鸟为“罗网”所罩、所压,不能自由翱翔。铅、汞在鼎器中相互吸引,如婴儿之恋母;其发生化学反应的过程中,会发出如婴儿啼哭一般的声音。汞性本飞扬,然其为铅所制,只能安处于鼎器之内不再逃逸;在与铅发生化学反应的过程中,其反射各色之光的性能亦发生变更。大概经过不到半个刻漏时间的火符,鼎中药物形状或呈鱼鳞之状,或如动物颈背上的长毛或长鳍那般密集杂陈、重叠相接;药物颜色也发生着丰富多彩的变化,五颜六色、鲜艳夺目,而无不变之常色。因得炉火烹炼,药物化为液态,在鼎中如水、云般急速涌沸、翻冒,上下滚动而不止息;慢慢地,药物开始凝结,相交、相结,重叠、累积,如犬牙相交错的样子;又如严冬所结之坚冰,还似溶洞中悬在洞顶上纵横交叉、参差错落的钟乳石;或如巍巍耸起、高低错落有致的土石之山,交相累积在一起,支柱于鼎器之中。
阴阳得其配章第八十二
【题解】
本章阐明炼丹时药物交媾之景象、火候之法度以及炼丹循理而操作的重要性。
自外丹言之,鼎中铅、汞等药物阴阳得以恰当配合,故能各自安守其相配合之法、居于鼎器之中。炼丹过程中,将丹砂木汞运入鼎中,其得阳火烹炼,于鼎中生华、吐秀;阳火旺盛之后,则当退阴符,候鼎中铅金、流汞自相凝结。铅、汞与火三者常相配合,同为伴侣,犹家属之相亲、相恋;但作为丹药之基的一般只有铅、汞二物,炉火只是起催化铅、汞于鼎器内发生化学反应的作用。铅、汞与火为“三”,再加上后得的铅中之汞、汞中之铅,则为“五”,它们之间相互作用,在“二所”即鼎、炉内发生化学反应,此后则合而为一,结成金丹。经文所说丹药陶冶之法如科条之不可违;至于炼丹所用时日及炉火之文、武火候,亦当取法于前文所说律历所纪之日数。
自内丹言之,修行人令己之真息绵绵,勿使间断,则精、炁与神阴阳相交感,自能得其配合;因其虚心凝神、纯一不杂,则其身内神与炁、精阴阳安然相守。修炼过程中,通过进阳火以炼精化炁,阳炁日盛则升而上、至于泥丸头顶;此后,通过退阴符之火得药并使之归炉。“青龙”喻性、魂,“白虎”喻命、魄,“朱雀”喻心之神火,性与命、魂与魄在心神之火的调节下,相亲、相配而不离,此即魂魄相合、性命双修。东三木之性、南二火之神,合而为五;西四金之炁、北一水之精,合而为五,中宫脾土之真意,其数亦为五,故为“三五”;“一”喻炼丹之真种,也即先天真一之炁。因为丹药皆要集归于鼎、炉之中加以烹炼方能成丹,所谓“二所”即玄、牝之门,修炼金液还丹有法度、科条可依,迎一阳之候以进火,其妙用则始于一阳初动之时;丹成虽须久远之时日,但仍然要以最初一点真种也即先天真一之炁为其根基。
阴阳得其配兮,淡泊而相守[1]。青龙处房六兮,春华震东卯[2]。白虎在昴七兮,秋芒兑西酉[3]。朱雀在张二兮,正阳离南午[4]。三者俱来朝兮,家属为亲侣[5]。本之但二物兮,末而为三五;三五并与一兮,都集归二所[6]。治之如上科兮,日数亦取甫[7]。
【注释】
[1]阴阳得其配兮,淡泊而相守:鼎中铅、汞等药物阴阳得以恰当配合,故能各自安守其相配合之道、居于鼎器之中。自内丹言之,欲使精、炁与神阴阳相交感,修行人当令真息绵绵,勿使间断,则药物阴阳自能得其配合;因其虚心凝神、纯一不杂,则其身内神与炁、精阴阳自然相守。配,相配,配偶;言铅、汞等药物阴阳相配,犹如配偶。淡泊,自然、平静之意。淡泊而相守,他本或作“淡薄而相守”、“淡泊自相守”。或谓其意即如前文所说之“各守境隅”,各自独居。
[2]青龙处房六兮,春华震东卯:青龙,指二十八宿中的东方七宿,二月春分时节,青龙七宿之房宿于黄昏后出现在天空的东方,其时属仲春,万物生华、吐秀,以卦言之则为震,于方位言之则属东,于辰言之则为卯月。于外丹言,此喻指将丹砂木汞运入鼎中,得阳火烹炼,于鼎中生华、吐秀之时;内丹则以之喻通过进阳火,炼精以化炁;阳炁日盛,将升而上、至于泥丸头顶。青龙,中国古代天文学指周天二十八宿中的东方七宿。二十八宿将周天划分为四部分,其中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这七个星宿组成一条龙的形象,春分时节出现在东部的天空,故称“东方青龙七宿”。中国古代天文学用四象、二十八星宿中每象、每宿的出没和到达中天的时刻来判定季节。房六,指东方青龙七宿中的房宿。一说“房”为天驷,本有四星,其旁有两星:钩、衿,合起来则为六星,故说“房六”,它们属东方苍龙之宿,于时代表春季二月之卯,五行属木,于丹道言,此所说为炼丹火动之时。或谓周天二十八宿,可分为十二分野,也即十二次,其中,东方苍龙、南方朱雀、西方白虎、北方玄武每方各三次。东方苍龙三次为:“析木”寅,包括箕、尾二宿;“大火”卯,包括心、房、氐三宿;“寿星”辰,包括角、亢二宿;房宿属“大火”卯,为“三次”之中,其左、右分别为角、亢、氐三宿与心、尾、箕三宿,因周围有“六宿”而房宿居其中,故说“房六”。或谓“房六”指房宿的度数。二十八宿的每一宿皆表示一个星空区域,于其中选出一颗星作为“距度星”,或称“距星”。距星的距度,也即相邻距星的度数之差代表各宿星区的广度。宋代鲍云龙《天原发微》认为,周天二十八宿:“星龙之度七十五,星武之度九十八四分度之一,星虎之度八十,星雀之度百二十,合之而为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。”东方苍龙七宿共计七十五度,其中,角十二度、亢九度、氐十五度、房五度、心五度、尾十八度、箕十一度,房宿的度数为五度,接近六度。当然,天体运行本无所谓“度”,推算历法者为了计算方便,按太阳每年所行经一个周期的轨道,划分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度;在这个过程中,因需要有参照物作为标记,故以在黄道附近的二十八宿作为分度界点;二十八宿所分之度数,多则三十三度、少则只有一度,这是因为在太阳所行经的黄道带上,可以作为分度标志的星体其远近距离并不相同,故其度数也有差异。或谓“六”指水之成数,在中国古代占星术中,房宿主雨水,青龙属木,“青龙处房六”,木居水旺之地而有养,表明春旺行阳气。春华,春天到了,百花齐放、万紫千红,万物皆欣欣向荣,谓之“春华”。丹道则以之喻鼎中药物得阳火烹炼,在鼎中沸腾、震动,蒸发、生华之象。震,“八经卦”之一。“震”可以用来象征东方、春天、春雷、龙、花等,《周易·说卦》:“帝出乎震。”“万物出乎震,震东方也。”“震为雷,为龙,为玄黄,为旉。”卯,十二辰之一,代表东方,于月为仲春之二月,于时辰为早晨五点至七点,此时阳气趋于盛。或谓氐、房、心三宿为火,于辰在卯,“卯”喻丹道之阳火沐浴火候。
[3]白虎在昴七兮,秋芒兑西酉:白虎,指二十八宿中的西方七宿,昴宿,居西方七宿之中,星度为七,于时代表秋季,草本科与禾本科植物此时成熟,茎项生穗或结籽;《周易》以兑卦的欢悦之意喻之,兑于后天八卦方位在西,于时为八月秋分之酉,五行属金。于外丹言,此喻阳火旺盛之后当退阴符,以阴用事,候鼎中铅金、流汞自相凝结。内丹则以之喻通过退阴符之火,得药以归炉。白虎,中国古代天文学指周天二十八宿中的西方七宿。二十八宿将周天划分为四部分,其中奎、娄、胃、昴、毕、觜、参这七个星宿形成一只虎的形象,春分时节在西部的天空,故称“西方白虎七宿”。昴七,一说“昴”有七星,为西方白虎之宿的组成部分,于时代表秋季八月之酉,五行属金,以兑卦象之;于丹道言,火旺之后,不再进阳火,以阴用事,候其金水自凝结,所谓“白虎在昴七”即有此义。或谓西方三次的中间一次为大梁,昴星属之,其度数为七,故云“昴七”;还有谓“七”乃火之成数,白虎所喻之铅金得火煅而熟成。秋芒,“芒”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,生在山地或田野间,叶子条形,秋天茎项生穗,黄褐色,果实多毛,即所谓“秋芒”;或谓“芒”即某些禾本植物籽实外壳上长的针状物。兑,“八经卦”之一。兑可以用来象征西方、秋天、泽水、欢悦等,《周易·说卦》:“兑,正秋也。”“兑为泽,为少女。”酉,十二辰之一,代表西方,于月为仲秋之八月,于时辰为傍晚5点至7点,此时阴气趋于盛。丹道以“酉”喻退阴符之沐浴火候。
[4]朱雀在张二兮,正阳离南午:朱雀指二十八宿中的南方七宿,“张宿”即南方七宿之一,因南方张宿二度与北方危宿初度将天盘一分为二,故有“张二”之说;于时代表夏季,此时阳火之气达到极盛状态,故称之为“正阳”,《周易》以离卦的火、光明之意喻之,离于后天八卦方位在南,于时为五月夏至,五行属火。于丹道言,此喻进阳火达到旺盛状态。朱雀,中国古代天文学指周天二十八宿中的南方七宿。二十八宿将周天划分为四部分,其中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张、翼、轸这七个星宿形成一只鸟的形象,春分时节在南部天空,故称“南方朱雀七宿”。张二,“张”即张宿,“张宿”乃南方七宿的重要组成部分;张宿有十八度,经文何以只言其二,对此有不同解释。一种观点认为:因周天共三百六十五度有余,中国古代天文学自北方七宿的虚、危之间,与南方七宿的张宿之间平分天盘为两部分,而危初度正与南方张二度相对,故称“张二”。或谓张宿六星,均为四、五等小星,其中较亮的是张宿二,故称“张二”。或谓朱雀七宿居南,为火之精,而五行生、成数中,火之生数为二,天文学中以张星代表火宿,故可云“张二”;结合上文,则“房六”、“昴七”应水、火之成数,“张二”、“危一”又应水、火之生数,水、火生成之数合,犹如家属之相亲。丹道则以之喻铅、汞药物相配。正阳,阳火之气的极盛状态,故称之为“正阳”。离,“八经卦”之一。离可以用来象征南方、火、光明、燥等,《周易·说卦》:“离也者,明也,万物皆相见,南方之卦也。”“离为火,为日,为电。”午,十二辰之一,代表南方,于月为夏之五月,于时辰为中午11点至13点,此时阳气鼎盛,丹道则以“午”喻进阳火至于极则阴生。朱雀在张二兮,他本或作“朱鸟在张二兮”。正阳离南午,他本或作“正阳杂南午”、“正阴离南午”。
[5]三者俱来朝兮,家属为亲侣:“三者”指青龙、白虎、朱雀,“来朝”指三者皆来朝于北极之宫;在外丹言,“青龙”喻指丹砂木精或流汞,“白虎”喻指铅金,“朱雀”喻火,铅、汞处鼎器中,再以火烹鼎,此为三者“来朝”;铅、汞与火三者常相配合,同为伴侣,犹家属之相亲、相恋,共居于一宅之中,如此则可以使炼丹有成。自内丹言之,“青龙”喻性、魂,“白虎”喻命、魄,“朱雀”喻心之神火,性与命、魂与魄在心神之火的调节下相亲、相配而不离,此即魂魄相合、性命双修。
[6]本之但二物兮,末而为三五;三五并与一兮,都集归二所:作为丹药之基的一般只有铅、汞二物,此乃真阴、真阳,炉火只是起催化铅、汞于鼎器内发生化学反应的作用。在炼丹过程中,铅、汞得火烹炼,相融于鼎中;铅、汞与火为“三”,再加上后得的铅中之汞、汞中之铅,则为“五”,故说“末而为三五”。它们之间相互作用,在鼎、炉内发生化学反应,熔成如水一样的液态之状;最后合而为一,结成金丹。本,根本,与后文之“末”相对。二物,即阴阳。外丹指铅金与流汞;内丹指精、炁与神。三五,一说“三”即前所谓青龙、白虎、朱雀,“三五”即青龙房六、白虎昴七再加朱雀张二,共十五之数,号称“三五”;一说“三五”之“三”指木、金、火,木、金、火皆禀土气,而土之五行生数为五,故说“三五”。或谓炼丹用水、火、土三物;水之生数一,火之生数二,合火之二与水之一为三,再加土之生数五,即是“三五”。外丹通常以铅、汞与火为三,鼎内壁涂有土,土五行生数为五,故说“三五”。内丹则认为,东三木之性、南二火之神,合而为五;西四金之炁、北一水之精,合而为五,中宫脾土之真意,其数亦为五,故为“三五”。一,或谓“一”指炼丹之鼎器;或谓“一”喻水之生数,喻与“张二”相对的“危一”,危宿乃北方玄武七宿的重要组成部分,天文学上,由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这七个星宿形成一组龟蛇互缠的形象,春分时节出现在北部的天空,称之为“北方玄武七宿”;青龙之房六喻水之成数,白虎之昴七喻火之成数;朱雀之张二喻火之生数,与张二所对峙的“危一”可应水之生数。内丹以“一”喻炼丹之真种,或谓即先天真一之炁。二所,即炼丹之鼎与炉,因为丹药皆要集归于鼎、炉之中加以烹炼,方能成丹。或谓“二所”即铅、汞。从内丹的角度,亦有谓“二所”为玄、牝之门者。有多家注本则认为“二所”应当作“一所”,“所”指中央正位,即中宫黄庭。末而为三五,他本或作“末之为三五”。三五并与一兮,他本或作“三五之与一兮”、“三五并为一兮”、“三五并危一兮”。都集归二所,他本或作“都集应二所”、“都集归一所”。
[7]治之如上科兮,日数亦取甫:丹药陶冶之法,一如上面经文所说,如科条之不可违;至于炼丹所用时日,及炉火之文、武火候,亦取法于前文所说律历所纪之日数。自内丹言之,大药既得之后,当从事温养之功,其法与前文所说筑基、固命之功法相同;但此过程非一日之功,当日积月累,方可能有所成,这也与筑基、固命的功夫无异。或谓此句意指:修炼金液还丹当依前面经文所说法度而行,迎一阳之候以进火,其妙用则始于虚、危的一阳初动之时;丹成虽须久远之时日,但仍然要以最初一点真种也即先天真一之炁为其根基。治,陶冶,炼制。上科,“科”即科条,于此喻炼丹的法度,“上科”即上文所提及的炼丹法度。或谓“上科”指将丹药放入鼎中之谓;此后,当按日数而行文、武之火,尤其不可以不谨慎。日数,指炼丹所用之时日,或谓指炼丹所用之文、武火候。取,资取,效法。甫,始之意。或谓“甫”即“辅”,有辅助之意。
【译文】
鼎中铅、汞等药物阴阳得以恰当配合,故能各自安守其相化合之道,居于鼎器之中。青龙指二十八宿中的东方七宿,二月春分时节,青龙七宿之房宿于黄昏后出现在天空的东方,其时属仲春,万物生长、开花,以卦言之则为震,于方位言之则属东,于辰言之则为卯月;丹道以之喻丹砂木汞居鼎中,其得阳火烹炼,在鼎中生华、吐秀。白虎指二十八宿中的西方七宿,昴宿居西方七宿之中,星度为七,其出现在合适的位置,于时代表秋季,草本科与禾本科植物此时成熟,茎项生穗或结籽;以卦言之则为兑,兑于后天八卦方位在西,于时为八月秋分之酉;丹道以之喻阳火旺盛之后,当退阴符,以阴用事,候鼎中铅金、流汞自相凝结。朱雀指二十八宿中的南方七宿,张宿即南方七宿之一,南方张宿二度与北方危宿初度将天球一分为二,其出现在特定的位置,于时代表夏季,此时阳气达到极盛状态,故称之为“正阳”;于卦言之则为离,离于后天八卦方位在南,此于丹道言,则喻进阳火达到旺盛状态、阴将要萌生之时。青龙喻指丹砂木精或流汞,白虎喻指铅金,朱雀喻火,铅、汞处鼎器中,再以火烹鼎,此为三者“来朝”;铅、汞与火三者常相配合,同为伴侣,犹家属之相亲、相恋,如此则可以使炼丹有成。作为丹药之基的一般只有铅、汞二物,此乃真阴、真阳,炉火只是起催化铅、汞于鼎器内发生化学反应的作用。在炼丹过程中,铅、汞得火烹炼,相融于鼎中;铅、汞与火为“三”,铅、汞共处鼎中相融,又有铅中之汞、汞中之铅,合则为“五”,故说“末而为三五”。它们之间相互作用,在鼎、炉这两个场所即“二所”之内发生化学反应,熔成如水一样的液态之状;最后合而为一,结成金丹。丹药陶冶之法,一如上面经文所说,如科条之不可违;至于炼丹所用时日,及炉火之文、武火候,亦取法于前文所说律历所纪之日数。
先白而后黄章第八十三
【题解】
本章言火足丹成之象。
自外丹言之,流汞在常温下呈现银白色闪亮的色泽,故说“先白”;其与铅金化合之后,颜色开始转为黄色,故说“后黄”;又继续以火煅烧,则变为红色,火足丹成,红色转变为紫色,此即所谓“赤黑”,如此所得金液还丹,称为“第一鼎之丹”;每日服食如黍米般大小的一粒金丹,时至则能道成。炼金丹皆要禀自然之法而为,如行邪伪之道则不能有所成。炼丹当以同类之物为原料,如以汞投铅,黄芽自出;以芽投汞,还丹自成,因其种类相同;若非其类,徒施功巧,终无所成。
自内丹言之,修炼先要求取先天元阳真一之炁,以丹经术语来说,即要求取“水中金”,以为丹头;丹头初结,尚须精炼,故要运转河车,使之升于头顶,最后送归于坤腹也即土釜之中含养;在这整个过程中,不离心神离火的作用,火赤、水黑、金白,土之色则黄,故说“先白后黄”与“赤黑”。精、炁与神渐凝渐结,则玄珠成象,如黍米之状,名“第一鼎之丹”;送归丹田含育,名为“服食”。当然,在这个过程中,又有烹炼、进火、退符等诀,此皆合于自然、无为的法则。精、炁与神同类自相匹配,自然结成丹宝。
先白而后黄兮,赤黑达表里[1]。名曰第一鼎兮,食如大黍米[2]。自然之所为兮,非有邪伪道[3]。若山泽气相蒸兮,兴云而为雨;泥竭遂成尘兮,火灭化为土[4]。若檗染为黄兮,似蓝成绿组;皮革煮成胶兮,麹糵化为酒;同类易施功兮,非种难为巧[5]。惟斯之妙术兮,审谛不诳语;传于亿世后兮,昭然自可考;焕若星经汉兮,昺如水宗海[6]。思之务令熟兮,反复视上下;千周灿彬彬兮,万遍将可睹;神明或告人兮,心灵乍自悟;探端索其绪兮,必得其门户;天道无适莫兮,常传与贤者[7]。
【注释】
[1]先白而后黄兮,赤黑达表里:此句阐明鼎中铅、汞变化之状。流汞在常温下呈现银白色闪亮的色泽,故说“先白”;其与铅金化合之后,颜色开始转为黄色,故说“后黄”;又继续以火煅烧,则变为红色,火足丹成,红色转变为紫色,此即所谓“赤黑”。自内丹言之,修炼先要求取先天元阳真一之炁,以丹经术语来说,即要由坎中取阳。坎属水、其色黑;《周易·说卦》乾坤父母说认为,坎中之阳由乾而来,乾为金、其色白;炼丹要从黑中取白,即求取“水中金”,以为丹头。丹头初结,尚须精炼,故要运转河车,使之升于头顶,又降落于中宫黄庭,最后送归于坤腹也即土釜之中含养,土之色黄,故说“先白后黄”。在这整个过程中,都离不开神识离火的作用,离火之色赤;神识离火能烹坎水之精、炼精以化炁,精、炁亦丹的基本成分,精属水,水之色黑,故说“赤黑”。“表”代表丹头初结,“里”代表丹之成熟,始而炼己,既而得药,终而温养,始终内外,全赖神与炁、精,故说“赤黑达表里”;也就是说,无论丹头初结还是丹之成熟,皆不离神与炁、精的相互作用。或谓肺属金,其色白;脾属土,其色黄;心属火,其色赤;肾属水,其色黑。炼丹时,肺炁降而下,脾炁自黄庭中宫升而上,此二者常相会合;赤为心炁,黑为肾气,心、肾相交媾,二者亦常相为表里。赤黑达表里,《道藏》彭晓本此句作“食黑达表里”,《四库全书》彭晓本作“赤黑达表里”,现据四库本改;他本此句或作“赤色通表里”。
[2]名曰第一鼎兮,食如大黍米:如此所得金液还丹,称为“第一鼎之丹”;每日服食如黍米般大小的一粒金丹,时至则能道成。自内丹言之,精、炁与神渐凝渐结,则玄珠成象,如黍米之状,名“第一鼎之丹”;送归丹田含育,名为“服食”。或谓精、炁与神汇于头顶泥丸宫,即所谓“第一鼎”;及其成丹,则大如黍米,送归于丹田之内,名为“服食”。第一鼎,通常丹分品类,有所谓上品、中品、下品,或者二十四品等等,第一鼎即初成之丹;如以火候言之,炼丹火候亦有九转、九鼎,则第一鼎为九转火候起初的第一转。内丹则以第一鼎为先天元阳真一之炁。黍米,一年生草本植物,叶子线形,籽实淡黄色,去皮后叫黄米,比小米稍大,煮熟后有黏性,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,籽实可以酿酒、做糕等。一说这种植物的籽实,称作“黍米”。丹经则以“黍米”来形容金丹之状貌。食如大黍米,他本或作“食如大稻米”。
[3]自然之所为兮,非有邪伪道:炼成金丹,皆要禀自然之法而为,如行邪伪之道则不能有所成。自内丹言之,修丹之法,至简至易,其神机妙用,不假作为,不因思想,故谓之“自然”。当然,在这个过程中,要做到收视返听,潜神于内,一呼一吸,悠悠绵绵,不疾不缓,勿令间断,才能神归炁中,炁与神合,交结成胎;所以,要先存神入于炁穴,而后与之俱忘,如是久之,则神自凝、炁自聚、息自定。待时至炁化,又有烹炼、进火、退符等诀,此亦合于自然、无为的法则。
[4]若山泽气相蒸兮,兴云而为雨;泥竭遂成尘兮,火灭化为土:《周易·说卦》谓:“山泽通气。”川泽之水汽蒸而上升,至于山顶之天上,化而为云,待阴阳和洽则降下为雨,又复回到地面、川泽之中,所降之雨即川泽所蒸云气而化。山泽通气能兴云致雨,丹道之理亦如此。铅、汞等药物在鼎中,被炉下火气相蒸,翻来覆去,上下沸腾、滚动,如云行雨施,从而阴阳得以交媾。泥土潮湿,性本重滞而居下,及得曝晒则干燥而裂,化为尘土;火乃炎上之物,其燃烧时,烟焰向上升扬,待火灭煨烬则亦化为灰土,殊途而同归,故知炼丹所用药物虽阴阳性质不同,然皆可以归本于丹。自内丹言之,“蒸”而上升意味着先天元阳之炁行周天运转,至于头顶泥丸峰顶;化而为“雨”意味着先天元阳之炁化为玉浆,降下十二重楼,入于黄庭中宫。在这个过程中,精、炁为神识之火所烹,由浊转清、由重转轻,沿身后之督脉逆而升于头顶,犹如炼外丹时铅金为火所煅,化为窗尘,飞浮而上,此以“泥竭遂成尘”喻之;人的神识之火得精、炁相摄,不再纷乱、杂陈,于其中现出清静元神、真意,所谓“制心一念”而得“心死神活”,犹如炼外丹时,离汞为铅金所擒,烟消烬灭、汞死化归厚土,故以“火灭化为土”喻之。兴云而为雨,他本或作“兴云为风雨”。“泥竭遂成尘兮,火灭化为土”二句,他本或作“泥竭乃成尘兮,火灭自为土”。
[5]若檗(bò)染为黄兮,似蓝成绿组;皮革煮成胶兮,麹糵(qū niè)化为酒;同类易施功兮,非种难为巧:炼丹当以同类之物为原料,如以汞配铅,则各自气类相感、妙合而凝,犹夫妇之相配偶,此谓之“同类”;类同则易于施功,如染黄用黄檗,染绿丝绳用蓝靛,煮皮革以成胶,以麹糵作酵以酿酒,不劳于力,自然能成。若舍此而别求他物,则非其种类,徒费功夫。丹道亦如此。以汞投铅,黄芽自出;以芽投汞,还丹自成,因其种类相同;若非其类,徒施功巧,终无所成。自内丹言之,精、炁与神同类自相匹配,自然结成丹宝。虽有所作,实则无为,俱出于天然。檗,也称“黄檗”、“黄柏”,落叶乔木,树皮淡灰色,羽状复叶,小叶卵形或卵状披针形,花小,黄绿色,果实黑色;其茎可用来制作黄色染料。炼丹以汞投铅,色由白而变黄,如物为檗染成黄色一般。蓝,即靛青。炼外丹所用之铅,其色蓝白。绿组,即绿丝绳。麹糵,“麹”指用曲霉(真菌的一类,菌体由许多丝状细胞组成,有些分枝的顶端为球形,上面生有许多孢子。可用来酿酒、制酱油和酱等)和它的培养基(多为麦子、麸皮、大豆的混合物)制成的块状物,用来酿酒或制酱;“糵”即酿酒的曲。若糵染为黄兮,他本或作“若糵以染黄兮”。皮革煮成胶兮,他本或作“皮革煮为胶兮”。
[6]惟斯之妙术兮,审谛(dì)不诳语;传于亿世后兮,昭然自可考;焕若星经汉兮,昺(bǐng)如水宗海:作者经过审慎、仔细思忖后,将《周易参同契》所载金液还丹之妙术和盘托出于经文之中,句句详审、字字谛当,其间没有任何欺骗、诳人之语;作者所述此文,将可以流传亿万世之后;其法昭然明白而可考,后学者可于此作种种探讨,既悟者亦可于此得到印证;其理焕然晓畅,如星星在天河中移动那般显明昭著,又似百川之水归宗于大海那样顺理成章。审,审慎。谛,仔细之意。诳语,诳有欺骗之意,诳语即骗人的话。昭然,很明显的样子。焕,光明,光亮。汉,河汉,即银河。昺,明亮、光明之意。传于亿世后兮,他本或作“传于亿后代兮”。昭然自可考,他本或作“昭然如可考”、“昭然而可考”。昺如水宗海,他本或作“昺如水带海”。
[7]“思之”十句:必须深思、熟读此书,将经文上下、前后各部分内容的义理贯通起来;读之千遍,于其理则灿然明白,理解适宜而恰当;读之万遍,则其理如在眼前;好像有神明来告诉自己一样,忽然得心灵自悟、妙理自明的效果。通过探究丹道之理的端绪、纲领,乃能得见深入丹道的门户、路径,因为天道无亲,常将其理付与贤善之人。千周,读书千遍之意。彬彬,适宜、恰当之意。乍,忽然。端,事物的开始。绪,本意指丝的头,借指事物的开端。适(dí)莫,指用情的亲疏厚薄。《论语》:“子曰:‘君子之于天下也,无适也,无莫也,义之与比。’”(《里仁》)千周灿彬彬兮,他本或作“千周灿灿兮”。心灵乍自悟,他本或作“心灵忽自悟”、“魂灵乍自悟”。
【译文】
流汞在常温下呈现银白色闪亮的色泽,故说“先白”;其与铅金化合之后,颜色开始转为黄色,故说“后黄”;又继续以火煅烧,则变为红色;火足丹成,丹从外到内、由表及里,其色由红转变为紫、黑,此即所谓“赤黑达表里”。如此所得金液还丹,称为“第一鼎之丹”;每日服食如黍米般大小的一粒金丹,时至则能道成。炼金丹要禀自然之法而为,如行邪伪之道则不能有所成。铅、汞等药物在鼎中,被炉下之火相蒸,翻来覆去,上下沸腾、滚动,如云行雨施,从而阴阳得以交媾而成丹。犹如泥土潮湿、性本重滞而居下,及得曝晒则干燥而裂,化为尘土;火乃炎上之物,其燃烧时,烟焰向上升扬,待火灭煨烬,则亦化为灰土,潮湿之泥土与炎上升扬之火都能殊途而同归,故知炼丹所用药物虽阴阳性质不同,然皆可以归本于丹。当然,炼丹当以同类之物为原料。犹如染黄用黄檗,染绿丝绳用蓝靛,煮皮革以成胶,以麹糵作酵以酿酒,不劳于力,自然能成,因为其类相同,故易于施功;若舍此而别求他物,则非其种类,徒费功夫,机巧亦难成。丹道亦如此。以汞投铅,黄芽自出;以芽投汞,还丹自成,因其种类相同;若非其类,徒施功巧,终无所成。《周易参同契》所载金液还丹之妙术,句句详审,字字谛当,其间没有任何欺骗、诳人之语。此文将可以流传亿万世之后,其法昭然明白,读者自可详考;其理焕然晓畅,如星星在天河中移动那般显明昭著,又似百川之水归宗于大海那样顺理成章。读者务必深思、熟读此书,将经文上下、前后各部分内容的义理贯通起来;读之千遍,于其理则灿然明白,理解既适宜而又恰当;读之万遍,则其理如在眼前,好像有神明来告诉自己一般,忽然得心灵自悟、妙理自明的效果。通过探究丹道之理的首尾与端绪,读者必能得见深入丹道的门户、路径,因为天道无亲,常将其理付与贤善之人。
补塞遗脱章第八十四
【题解】
本章说明作者在著述《周易参同契》之后,又撰《五相类》的原因。
此章之前,原为《鼎器歌》;彭晓注解《周易参同契》时分九十章,并将《鼎器歌》移于文后。
《参同契》者,敷陈梗概,不能纯一,泛滥而说,纤微未备,阔略仿佛[1]。今更撰录,补塞遗脱;润色幽深,钩援相逮;旨意等齐,所趣不悖[2]。故复作此,命《五相类》,则大《易》之情性尽矣[3]。
五位相得而各有合
甲 三 乙
沉石 木 浮石
丙 二 丁
武火 火 文火
戊 五 己
药物 土 药物
庚 四 辛
世金 金 世银
壬 一 癸
真汞 水 真铅[4]
【注释】
[1]《参同契》者,敷陈梗概,不能纯一,泛滥而说,纤微未备,阔略仿佛:《参同契》这部书笼统陈述了修炼金液还丹之道的梗概,通过旁引、曲喻,泛泛而谈,并没有直接、纯粹、详尽地披露丹道之玄机;一些炼丹的细节也没有揭示,而只是将炼丹之纲要疏阔、简略地通过譬喻大致有所说明。《参同契》,一些注家认为,参,即三,指大《易》、黄老、炉火;同,相同或相通之意;契,相契、相类之意。道生育天地,长养万物,造化不能逃,圣人不能名,伏牺由其度而作《易》,黄、老究其妙而得虚无自然之理,炉火盗其机而得烧金、干汞之方,事虽分三,道则归一。作者借《周易》之理以言道家黄、老之学,而又与金丹、炉火之事相类;三者论阴阳造化,其理皆同而无所异,故命名其书为《参同契》。敷陈,“敷”有铺开、摆开之意;“陈”有叙述之意。纯一,纯粹、直接、精一之意。泛滥,原意指江河湖泊之水溢出、四散流趟,此处指泛泛而谈的意思。纤微,细节、精微之处。仿佛,类似之意。泛滥而说,他本或脱此四字。阔略仿佛,他本或作“缺略仿佛”。
[2]今更撰录,补塞遗脱;润色幽深,钩援相逮,旨意等齐,所趣不悖:现在此基础上,再撰写、记录一些经文,凡《周易参同契》篇中文辞有所遗漏、脱落的地方,皆于此补足、充实之;《周易参同契》义理过于幽深之处,对之也作出文字修饰,使经文所述之意能够上下相贯通,其意旨能够前后等齐,旨趣也不至于相互悖乱。润色,对文字进行修饰。幽深,深奥的道理。钩援,或谓即“勾梯”,也称“云梯”,可以用之攀爬上城墙;此处指钩玄提要,使前后之文意相互关联、贯通。钩援相逮,他本或作“钩援相连”。所趣不悖,他本或作“所趋不悖”。
[3]故复作此,命《五相类》,则大《易》之情性尽矣:因此,作者在原有基础之上重新有所撰述,将之命名为《五相类》,则《周易》阴阳之情性与金液还丹之理尽皆完备、无所遗漏。《五相类》,即五行相类之意。或谓《五相类》即此篇所属五章的内容,包括:一《参同》,二《太易》,三《象彼》,四《郐国》,五《委时》,称《五相类》。或谓《五相类》,即五行生成图所说之先天数相配合所喻的丹道之理。或谓《五相类》当作《三相类》,意指《大易》、黄老、炉火三者阴阳造化之理相通、相契。或以《五相类》作《互相类》。大《易》之情性,《周易·系辞》说: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《易》以道阴阳,故一阴一阳即大《易》情性;丹道遵之以炼药,然后丹可成,药可就,而成神化莫测之功。命《五相类》,他本或缺“命”字。大《易》,他本或作“太《易》”。他本此句后尚有“各如其度”句。
[4]“五位相得”以下几句:十天干起于甲、乙,终于壬、癸;十天干配五行,则甲、乙属木,丙、丁属火,戊、己属土,庚、辛属金,壬、癸属水;按汉代五行生成之说,天三生木,故甲、乙配三数;地二生火,故丙、丁配二数;天五生土,故戊、己配五数;地四生金,故“庚、辛”配四数;天一生水,故壬、癸配一数。此图有称之为洛书者,但朱熹等则以之为河图。又因为甲、丙、戊、庚、壬在十天干中属阳干,乙、丁、己、辛、癸在十天干中属阴干,故以“庚、辛”喻世金、世银;以“丙、丁”喻炼丹的武火、文火;戊、己为土,外丹要将药物炼之成土状,故以“戊、己”喻药物;壬、癸为水,铅、汞入鼎炼化而熔为液,皆如水之状,故以“壬、癸”喻铅、汞;甲、乙为木,因炼丹要将丹砂等矿石炼化,丹砂如火之色赤,而五行中木能生火,故丹家称“丹砂”为“木精”;因此之故,甲、乙之木可喻炼丹所用之矿石,经文则以浮石、沉石代表之。值得注意的是,因阴性隐而不显,阳则显现于外,故也有注本认为,乙当配沉石,甲当配浮石。其谓“五位相得而各有合”,指炼丹时,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各有其相生、相克者,如金得火炼则可以化水,木得金克则能成材;土镇水而能使之不泛滥成灾;水制火而能使之进退有时。如此等等。内丹则借“五行颠倒术”之说,明还丹须五行颠倒,如木本生火,性本生情,然内丹修炼要逆之而行,即求取所谓“火中木”,由妄情、妄识复返于清静本性,此即“东三南火同成五”,“龙从火里出”;金本生水,炁能化精,然内丹修炼要逆之而行,即求取“水中金”,炼精以化炁,此即“北一西将四共之”,“虎向水边生”。故水与金合,木与火合,然此皆不离真意戊己之土的作用,真意呈现则杂识罢去、元神澄明,如此方能产药,故戊、己以药物言之,实皆药物所由而生之条件。浮石,是一种多孔、轻质的玻璃质酸性火山喷出岩,其成分相当于流纹岩,又称“轻石”或“浮岩”,因其气孔较多容重小(0.3—0.4)、能浮于水,因此而得名。现在,浮石主要用在园艺中,用作透气、保水材料以及土壤疏松剂,浮石亦可用作排水材料。历史上,“浮石”常与“沉木”相关联,“浮石沉木”有是非颠倒之意,如汉代陆贾《新语·辨惑》中说:“夫众口之毁誉,浮石沉木,群邪所抑,以直为曲。”经文则将“浮石”与“沉石”相对,大概为炼丹所用的两种原料,或矿物在鼎中浮动、沉降的不同性质。又,“己”下“药物”,《道藏》彭晓本缺“药”字,据他本补。
【译文】
《参同契》这部书笼统陈述了修炼金液还丹之道的梗概,通过旁引、曲喻,泛泛叙说,并没有直接、纯粹、详尽地披露丹道之玄机;一些炼丹的细节也没有揭示,而只是将炼丹之纲要疏阔、简略地通过譬喻大致有所说明。现在此基础上,我再撰写、记录一些经文,凡《周易参同契》篇中文辞有所遗漏、脱落的地方,皆于此补足、充实之;《周易参同契》义理过于幽深之处,对之也作出润色,使经文所述之意能够上下相贯通,其意旨能够前后等齐,旨趣也不至于相互悖乱。因此,我重新作一些补充撰述,将之命名为《五相类》,如此则《周易》阴阳之情性与金液还丹之理于此书中尽皆完备、无所遗漏。
五位相得而各有合:
十天干起于甲、乙,终于壬、癸;十天干配五行,则甲、乙属木,丙、丁属火,戊、己属土,庚、辛属金,壬、癸属水;按汉代五行生成之说,天三生木,故甲、乙配三数;地二生火,故丙、丁配二数;天五生土,故戊、己配五数;地四生金,故庚、辛配四数;天一生水,故壬、癸配一数。因炼丹要将丹砂等矿石炼化,丹砂如火之色赤,而五行中木能生火,故丹家称丹砂为木精;因此之故,甲、乙之木可喻炼丹所用之矿石,经文则以浮石、沉石代表之。又因为甲、丙、戊、庚、壬在十天干中属阳干,乙、丁、己、辛、癸在十天干中属阴干,故以庚、辛喻世金、世银;以丙、丁喻炼丹的武火、文火;戊、己为土,外丹要将药物炼之成土状,故以戊、己喻药物;壬、癸为水,铅、汞入鼎炼化而熔为液,皆如水之状,故以壬、癸喻真铅、真汞。所谓“五位相得而各有合”,指炼丹时,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各有其相生、相克者,如金得火炼则可以化水,木得金克则能成材;土镇水而能使之不泛滥成灾;水制火而能使之进退有时,如此等等。丹道通过五行相生、相制,配合药物,将之炼成金丹。
大《易》情性章第八十五
【题解】
本章阐明道的一阴一阳之理具有普遍性。
大《易》因一阴一阳之理而作;黄、老究一阴一阳之妙理以御政、修身;丹道炉火据阴阳配合之法而修丹,三道虽殊途而实则同归于一。
大《易》情性,各如其度;黄老用究,较而可御;炉火之事,真有所据;三道由一,俱出径路。[1]
【注释】
[1]“大《易》情性”八句:“大《易》情性”即一阴一阳,阴阳升降往来,各有其天然度数;此阴阳之情性及往来度数,贯通于天、地、人三才之道,化育天地万物,天、地、人三才俱合于其理,各如其度而无所逾越。黄帝、老子探究、法则阴阳之道,倡导清静、无为,以御政、处事、修身、养性,阴阳之理得以彰明、显著。丹道之炉火亦取法药物阴阳配合之理,并非强作妄为,乃真有其根据所在。大《易》、黄老与丹道炉火三道总不离阴阳之理,俱以此而为所出之路径。自内丹言之,“大《易》情性”的一阴一阳可喻指坎、离药物,也即精、炁与神,其实则修炼人之身与心;身、心两者相配合,则精、炁与神打成一片,其间升降往来,各有其火候、法度,故说“各如其度”。“黄老用究”虽明言黄帝、老子清静、无为之旨,于内丹功夫则喻中宫黄庭正位、先天元始祖窍内,清静元神居于其中;识得祖窍所居之清静元神,得其真意,则可以和合身心,如把柄在手,故说“较而可御”,其中指出了炼丹鼎炉之所在。而炉火不离伏食,药物相互制约谓之“伏”,相互汲取、交融谓之“食”;内丹修炼身、心,以真意和合身、心,身与心一伏一食,乃成丹道炉火之事,其理确然有所据,于其中又暗含火候之事,故说“炉火之事,真有所据”。药物、鼎炉、火候三者虽名称各有所别,其妙用则仍然可合而为一体。情性,外在之情形与内在之性质。度,度数。黄老,汉代黄老新道家所推崇的黄帝、老子。用究,探究、使用之意。较,明显、显著之意;如人们所说“彰明较著”,其“较”即有显著之意。炉火,喻指炼丹之事。三道,通常以“三道”指大《易》、黄老、炉火。或谓“三道”指“三五”,即东三南二之五、北一西四之五与中央戊己之五,三五相合为一则丹成;或谓“三道”指铅金、流汞与炉火,也即金、木、火;或谓“三道”指大《易》、黄帝《阴符》、老子《道德》,三经同此一理。一,或以此“一”为道、为丹、为理,等等。径路,即路径。他本于此或缺“大《易》情性”一句。
【译文】
“大《易》情性”即一阴一阳,阴阳升降往来,各有其天然度数;天、地、人三才均循其度而无所逾越。黄帝、老子探究、法则阴阳之道,倡导清静、无为以御政、处事、修身、养性,使阴阳之理得以彰明、显著。丹道炉火亦取法药物阴阳配合之理,乃真有其根据所在,并非强作妄为。总之,大《易》、黄老与丹道炉火三道总不离阴阳之道,俱以此而为自己所出之路径。
枝茎华叶章第八十六
【题解】
本章借树木花草有其根株方能有枝、茎、花、叶、果、实的自然发生,以之说明丹道亦有其根本,进而有道为万化之根基的寓意。
枝茎华叶,果实垂布;正在根株,不失其素;诚心所言,审而不误。[1]
【注释】
[1]“枝茎”六句:春季时树木花草抽茎、发枝、开花、展叶,秋季时则果实累累、垂挂枝头,探究其发生之源,皆不离其根株之本;故树木花草虽繁生华叶、果实垂布,然皆不失其本然之天性。道为万化之本,犹树木之根株;循道而行,则能洞晓阴阳、深达造化,识万物生化之理;而修金液还丹,亦当先认根株,根株既得,则可以返本还源,结就金丹。作者认为其说皆出于诚心、诚意,读者深思、详审,方知其所言不误。自外丹言之,真铅为药之根株,“不失其素”指真铅能擒真汞,不失真水银之意。真铅与真汞配合,则自然发而为枝茎、散而为花叶,繁生果实,结成丹宝。自内丹言之,冬至时节,元阳之炁潜藏于地中,此一阳初动乃见天地之心,造化生成之妙,俱源于此,故其为修道之“根株”;修行人蓄养此一阳,则能由此而抽茎发枝、开花发叶,得秋收之果实累累。枝茎花叶,他本或作“枝茎花叶”。不失其素,指不失其本然之天性。他本此句或作“不识其素”。
【译文】
春季时树木花草抽茎、发枝、开花、展叶,秋季时则果实累累、垂挂枝头,探究其发生之源,皆不离其根株之本;故树木花草虽繁生花叶、果实垂布,然皆不失其本然之天性。凡修金液还丹,亦当先认根株,根株既得,则可以返本还源,结就金丹。作者此说皆出于诚心、诚意,读者深思、详审,方知其所言不误。
象彼仲冬节章第八十七
【题解】
本章阐释丹道一阳火候之秘,明修丹者若谬误、妄动则得自取伤败之咎。
自外丹言之,冬至时节天寒、地冻,竹、木摧残,此喻阳火退后,鼎炉中药物趋于安静的状态;然鼎炉中又非一片死寂,其中尚留存有一阳,故要固塞鼎器,保持鼎中药物之余温;以土填实鼎盖与鼎身之间的缝隙,不使鼎口张开,以防药物逃逸。当铅金、流汞等药物入鼎之时,尚各有其形,此即“匡郭”;得火烹炼后,铅、汞等熔解、化合,其原有之形容、匡郭消亡。鼎内药物变化多端,最后凝结、化合成丹。如果在炼丹过程中操作出现谬误,则将偏离、失去铅金、流汞等药物化合之原理、纲要;如此则会令炼丹之事遭到失败,丹亦损伤而不能结。
自内丹言之,冬至可以用来比喻身内一阳来复之机;然一阳之炁虽复,其生机尚微,故当归藏于丹田而养之。此时,修炼之士宜收视返听、虚静安神、澄心守默,以佐身内阳炁之生;神不外驰,敛藏于内,如此则神凝炁聚。修炼者息心忘虑,入于混沌、鸿濛,心境犹如天道之浩广;身内真机发动,其妙在于窈冥、恍惚、无形、无象之时。如果违背天道之理,于一阳来复之际,不能志于静默,务夸夸虚谈而不务实行,则是自取其伤败。
象彼仲冬节,竹木皆摧伤;佐阳诘贾旅,人君深自藏[1]。象时顺节令;闭口不用谈[2]。天道甚浩广,太玄无形容;虚寂不可睹,匡郭以消亡[3]。谬误失事绪,言还自败伤[4]。别序斯四象,以晓后生盲[5]。
【注释】
[1]象彼仲冬节,竹木皆摧伤;佐阳诘贾(gǔ)旅,人君深自藏:农历十一月的冬至节气,地面之上阴气强盛,摧残、伤害竹木等物,万物皆归根复命;然而此日一阳复生起于地中,为保护此一阳,以前的君王们通常都关闭城门,不接纳商旅,也不视察邦国,以顺应节气的变化。丹道所谓“冬至”,比喻阴极阳生之时。以一年言之,则如仲冬之节,竹木索然而摧尽;以一月言之,则如月晦之夜,月光索然而灭藏。此时,当顺应天道之法则,安静以养其阳。以外丹言之,修丹火候,或文、或武,或进、或退,其开启、关闭皆要顺时,与节气相适应。冬至时节天寒、地冻,竹木摧残,此喻阳火退后,鼎炉中药物趋于安静之时;然鼎炉中又非一片死寂,其中尚留存有一阳,所谓“佐阳诘贾旅”,象征固塞鼎器,保持鼎中药物之余温;“人君深自藏”喻指鼎中所炼得的真阴、真阳,因其乃众药之精华,故以“人君”喻之;此真阴、真阳非常宝贵,当设法令其安处于鼎器深处、不令漏泄。自内丹言之,此以冬至发明一阳来复之机。当仲冬之节,竹木枝叶皆摧伤,此时人君顺时令而闭关,禁商旅之行,自己亦不外出视察邦国,此喻一阳之炁虽复,然生机尚微,当归藏于丹田而养之。修炼之士宜虚静安神、澄心守默,以佐身内阳炁之复发;所谓“佐阳诘贾旅”,即要收视返听,塞兑垂帘;所谓“人君深自藏”,因神乃身之主宰,神不能外驰,当使其敛藏于内,如《周易·系辞》所说“圣人以此洗心,退藏于密”,如此则神凝炁聚,阳炁复生、复盛。内丹还返妙用,无出一阳子时,修炼者但知一阳之用,则其后身内自然变化,非假人力。或谓以身为竹、为木,以元炁为根,竹、木华叶摧落,必收藏以粪其根株,乃能积聚阳炁,复返生机活力。仲冬,指农历十一月。节,指冬至。佐,辅助、辅佐之意。诘,盘诘、责问之意。贾旅,商人的通称。古时候,“贾”一般指坐商;“旅”于此指行商。此句源出于《周易·复》之《象》:“雷在地中,复。先王以至日闭关,商旅不行,后不省方。”竹木皆摧伤,他本或作“草木皆摧伤”。佐阳诘贾旅,他本或作“佐阳诘商旅”。
[2]象时顺节令,闭口不用谈:修丹者当法象天地之道,顺应节气、时候之变化而进火、退符,此乃不待言之事。自外丹言之,退火之后,炉中尚有余温,炼丹者当以土填实鼎盖与鼎身之间的缝隙,不使鼎口张开,以防药物逃逸。所谓“闭口不谈”,即喻指当密闭鼎中胎养金丹之室。自内丹言之,“象时顺节令”即要忘情息虑,顺应天地间与一身之内阴阳炁机之消长;此时当罢弃言辞、以返本复原。象时顺节令,他本或作“象时顺令节”。
[3]天道甚浩广,太玄无形容;虚寂不可睹,匡郭以消亡:天道苍苍,浩然广大,无边无际;天道之理幽深而玄远,无形无容,至虚至寂,视之而不得见,故无法像城市、垣郭之四方匡正那样被明确勾勒出来而立以为范。自外丹言之,“天道甚浩广”喻指鼎内药物变化多端,如天道之无涯、无际;“太玄无形容”喻指铅金、流汞在鼎中融会贯通,潜运无极,神化无方,不得见其形容;铅金、流汞等药物入鼎之时,尚各有其形,此即“匡郭”;得火烹炼后,铅、汞等熔解、化合,其原有之形容、匡郭消亡,然后药物方能凝结、化合成丹。自内丹言之,“天道甚浩广”意喻修炼者息心忘虑,入于混沌、鸿濛,心境犹如天道之浩广,如此神、炁方能归根、返本以还源;“太玄无形容”喻身内真机发动,其妙在于窈冥、恍惚、无形、无象之时;故当身内一阳来复之时,修炼者必先闭塞其各种感觉器官之功,收心守默,使精、炁与神同归于丹田之中,如日、月合璧之时隐藏其匡郭,沉沦于洞虚,则神凝炁聚,金液还丹可结。因大道运育,真宰无形,只有调和阴阳药物,合以天机,方能使神与炁、精相牵引,留连于身中,而成其妙化。故有注以“匡郭消亡”为坎、离交媾,神与炁、精混沌交结,清虚、湛寂而不可睹之意。虚寂不可睹,他本或作“虚空不可睹”。
[4]谬误失事绪,言还自败伤:一些人不知丹理便妄言丹法,其所言既不识炼丹之头绪、原理,故错谬、失误在在皆是;其虽有所言说,然一方面错引他人,另外连带自己也受牵连而受失败、伤害之困扰。或谓天道玄微,难可察睹,修炼之事自此而始,丹之头绪自此而出;既然天道之理虚寂而不可见,立匡郭以为范围尚且不可,若勉强谈论之,必有谬误,失天道浩广、虚寂流行之事绪,不足以揆方来,故言之反而自败其德,不如不言为妙。自外丹言之,如果在炼丹过程中操作出现谬误,则将偏离、失去铅金、流汞等药物化合之原理、纲要;如此则会令炼丹之事遭到失败,丹亦损伤而不能结。自内丹言之,如果违背天道之理,于一阳来复之时,不能志于静默,务夸夸虚谈而不务实行,则是自取其伤败。
[5]别序斯四象,以晓后生盲:因天道与丹道之理难以察知,无形可睹,故欲测造化之机、形阴阳之理、成还丹之功,作者特别序说乾、坤、坎、离此“四象”之文义,以一年中乾、坤阴阳之来往,一月中坎、离日月之合离,显露天道之理,以开示、晓悟后来那些不明丹理的人。四象,或谓即《周易参同契》所说的乾、坤、坎、离,其中,“乾、坤”喻鼎器,“坎、离”喻药物;或谓“四象”即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,以喻炼丹所用之金、木、水、火;或谓“四象”即七、八、九、六,以喻丹道文、武火候的进退消长。或谓“四象”明丹道之药物,炼丹所用之真铅、真汞以“壬、癸”为喻,“壬”乃乾中之离,“癸”乃坤中之坎,合之则为“四象”。其他如子午卯酉、子申寅戌、春夏秋冬、分至启闭、昼夜晨昏、还返归居等,皆有可能为“四象”之义。
【译文】
农历十一月的冬至节气,地面之上阴气强盛,摧残、伤害竹木等物,万物皆归根复命;然而此日一阳复生,为保护此一阳,以前的君王们通常都关闭城门,不接纳商旅,也不视察邦国,以顺应此冬至节气的变化。丹道则以“冬至”比喻阴极阳生之际,此时当顺应天道之法则,安静以养其阳;故要固塞鼎器,不令药物漏泄,使其安处于鼎器之内,并保持鼎中药物之余温。修丹者当法象天地之道,顺应节气、时候之变化而进火、退符,此乃不待言之事。然天道苍苍,浩然广大,无边无际;天道之理幽深而玄远,无形无容,至虚至寂,视之而不得见,故无法像城市、垣郭之四方匡正那样被明确勾勒出来而立以为范。丹道之理亦如此,鼎内药物化合之时,变化多端,如天道之无涯、无际;铅金、流汞在鼎中融会贯通,潜运无极,神化无方,若“太玄”之不得见其形容。当铅金、流汞等药物初入鼎之时,尚各有其形,此即“匡郭”;得火烹炼之后,铅、汞等熔解、化合,其原有之形容、匡郭消亡,然后药物方能凝结,化合成丹,其“虚寂”意味着药物相凝结时的安静,“不可睹”意味着其原有状貌的消解。一些人不知丹理便妄言丹法,其所言既不识炼丹之头绪、原理,故错谬、失误在在皆是;其虽有所言说,然皆不足以揆方来,故言之反而自败其德,不如不言为妙。作者于此特别序说乾、坤、坎、离“四象”之文义,以一年中乾、坤天地阴阳之来往,一月中坎、离日月之合离,显露天道之理、丹法之要,以开示、晓悟后来那些不明丹理的人。
会稽鄙夫章第八十八
【题解】
本章为作者之自序或后记,明己之志及作书之意。
会稽鄙夫,幽谷朽生;挟怀朴素,不乐欢荣;栖迟僻陋,忽略利名;执守恬淡,希时安平;宴然闲居,乃撰斯文[1]。歌叙大《易》,三圣遗言;察其旨趣,一统共伦[2]。
【注释】
[1]“会稽(kuài jī)鄙夫”十句:我本是会稽这个边远地区的一名见识粗浅之人,居于深山幽谷之中,于世无用,以朴素为怀,不羡慕欢娱、权力和荣华富贵,甘于栖身、游息在偏僻、简陋之地,不追逐利禄与功名;恬淡守素、养志虚无,希望时世安乐、平和。于安乐、闲居之时,我撰写了这篇文章。会稽,古地名,因绍兴会稽山得名。相传夏禹时即有会稽山之名,如《史记》说:“或言禹会诸侯江南,计功而崩,因葬焉,命曰会稽。会稽者,会计也。”东汉顺帝永建四年(129),析会稽郡中的十三县另置吴郡,原会稽郡治吴县属吴郡;另移会稽郡治到当时较偏远的山阴县(今浙江绍兴);永和三年(138),会稽郡领有山阴、诸暨、上虞、余姚等十五县。东晋葛洪《神仙传》认为,魏伯阳为东汉会稽上虞人。另外,《道藏》托名阴长生注本“会稽鄙夫”作“鲁国鄙夫”,认为此指汉北海郡徐从事,因《周易参同契》之作与他有关。“从事”乃汉代官名,徐或即地名、或即其姓。朱熹《考异》本、俞琰《发挥》本“会稽”作“郐国”,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杜预注:“古郐国,在密县东北。”据说,周武王灭商纣后,将祝融的后代封到郐,即今河南密县,后建立了郐国;到春秋时期的周平王二年(前769),郐国被郑武公所灭。之所以说“郐国”而不说“会稽”,旧注认为魏伯阳不欲人知其本来籍贯,故借“郐国”以寓“会稽”;朱熹则认为,或是“魏”隐语作“郐”。鄙,谦辞,用于自称。另外,亦有浅薄、粗俗或边远之意。挟怀,“挟”本意为用胳膊夹住;“挟怀”为心里怀着某种情感之意。栖迟,栖息迟缓,有优游、从容之意。宴然,安乐、安闲之意。朱熹《考异》本此句完整作“远客燕间”,而南宋曾慥《道枢》等一些史料也说魏伯阳曾远游长白山。会稽鄙夫,他本或作“鲁国鄙夫”、“郐国鄙夫”。不乐欢荣,他本或作“不乐权荣”。忽略利名,他本或作“忽略令名”。宴然闲居,他本或作“宴然间居”、“晏然闲居”、“燕然闲居”、“远客燕间”。
[2]歌叙大《易》,三圣遗言;察其旨趣,一统共伦:《周易参同契》此书以诗歌的体裁,表述大《易》之道;继承的是伏牺、周文王、孔子三位作《易》圣人所遗留之言辞与志趣。通过考察三圣作《易》的主旨与精神趣向,作者发现三圣之遗言、遗志可以一以贯之,其精神实质皆不离一阴一阳之道。而炼丹亦必得其阴阳配合之妙,方可以制伏铅、汞而成丹,故虽异名却同出一旨。歌,有韵之文,谓之“歌”。大《易》,指《易》之道。三圣,指伏牺、文王、孔子。关于《易》之作,《汉书·艺文志》提出“人更三圣”之说,即伏牺画卦;文王系辞以明吉凶;孔子又赞之以《十翼》。共伦,同类、同等之意。歌叙大《易》,他本或作“歌咏大《易》”、“歌吟大《易》”。察其旨趣,他本或作“察其所趋”、“察其所趣”。一统共伦,他本或作“一统共论”。
【译文】
我本是会稽这个边远地区的一名见识粗浅之人,居于深山幽谷之中,于世无用,以朴素为怀,不羡慕欢娱、权力和荣华富贵,甘愿栖身、优游于偏僻、简陋之乡,不追逐利禄与功名;恬淡守素、养志虚无,希望时世安乐、平和。于安乐、闲居之时,我撰写了这篇文章。《周易参同契》以诗歌的体裁,叙述大《易》之道;继承了伏牺、周文王、孔子三位作《易》圣人所遗留的言辞与志趣。通过考察三圣作《易》的主旨与精神趣向,作者发现三圣之遗言、遗志可以一以贯之,其精神实质皆不离一阴一阳之道。而炼丹亦必得其阴阳配合之妙,方可以制伏铅、汞而成丹,故虽异名却同出一旨。
务在顺理章第八十九
【题解】
本章论炼丹中和顺阴阳之理的重要性。
一阴一阳之谓“道”,阴阳不测之谓“神”。人们若能得阴阳配合之妙,不仅炼丹有成;依之推衍、制定历法,可以用万世之长久;依此治理政事,亦简易而不繁难、复杂;依此修身、养性,可以合于黄、老自然之法则。
务在顺理,宣耀精神;神化流通,四海和平[1]。表以为历,万世可循;序以御政,行之不繁[2]。引内养性,黄老自然;含德之厚,归根返元[3]。近在我心,不离己身;抱一毋舍,可以长存[4]。配以服食,雄雌设陈;挺除武都,八石弃捐[5]。
【注释】
[1]务在顺理,宣耀精神;神化流通,四海和平:炼丹者务必要和顺阴阳之理,奋迅其精神,如此则天地间阴阳不测之神机流转、变化趋于圆通,从而可以得己之身心与自然界万化的和谐、平安。自外丹言之,炼丹之火候务必顺阴阳之理,如此方能使鼎中药物神、精宣发,光明闪耀、流布于鼎中,遍满于金胎神室,鼎室中一片和畅、安平。自内丹言之,修炼者务必要顺应天地阴阳相参之理,如此则能精、炁充盈于一身之内,流转、布宣而无碍,神思清明而通达,人身的四肢八脉舒适安和,生起种种神妙而难以形容的变化。
[2]表以为历,万世可循;序以御政,行之不繁:将此法则表现出来,依之推衍、制定历法,可以用万世之长久;依此法则来治理政事,其行政亦不繁难、复杂。历,即历法,乃根据日、月等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,计量较长的时间间隔,判断气候变化,预示季节来临的法则。任何一种具体的历法,首先必须明确规定时间的起始点,即开始计算的年代,这在古代中国叫“纪元”;以及规定一年的开端,这叫“岁首”。此外,还要规定每年所含的日数,如何划分月份,每月有多少天等等,以方便人们的生产、生活。世,一个时代的通称,有时特指为三十年。行之不繁,他本或作“行之不烦”。
[3]引内养性,黄老自然;含德之厚,归根返元:黄帝、老子以此法则向内用于修身、养性,此合于天地自然之道。通过含养自己深厚的道德,保精惜炁,将其引而归藏于生命之本根;使其神明返还而居处于其所当处的本来之所。此从内丹修养之角度而言。自外丹言之,养铅、汞于鼎中,如同黄帝、老子含其德于内之象;铅、汞自然相化合,亦合于黄帝、老子所倡导的自然之道。之所以能炼铅、汞以成丹,实因铅、汞本身所禀受自然之性厚,故炼丹旨在归铅、汞之本根,返其本初之性。黄老,指黄帝、老子。自然,此“自然”非“自然界”之意,而是自己化生、不假外力,自然而然之意;故“自然”与“人为”相对,道家倡导“自然”,必然要求“无为”。《道德经》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(二十五章)德,与“道”相对应的一个概念;“道”为形上本体,“德”即万事万物得自于道而寓之于自身的性质。或谓道德皆本于一炁,普遍在宇宙间的谓“道”,寄存在人身中的谓“德”;统而言之谓“道”,分而言之谓“德”;此处所谓“含德”,即一炁而寄于人之身,人当使其所含受的先天一炁深而且厚,如此则自然而然归根返元,与道合真。此句源出于《道德经》:“含德之厚,比于赤子。”(五十五章)“致虚极,守静笃,万物并作,吾以观复。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,归根曰静,是谓复命,复命曰常,知常曰明,不知常,妄作凶。”(十六章)“载营魄抱一,能无离乎?”(十章)
[4]近在我心,不离己身;抱一毋舍,可以长存:此理就存在于我们心中,不离于自己的身体;只要我们在行动中坚持此理,一以贯之而不舍弃,就可以获得长生久视之功效。自外丹言之,“我心”喻铅;汞不离铅,故说“不离己身”;铅、汞化而为液,相抱而不离,就能炼就金丹而长存。“一”为水之生数,化为液则如水之状。自内丹言之,内养之道,切近于自己的心性,不离于自己的身体,但将精、炁、神三者抱合而为一,执守而不舍弃,则可以长生而永存。近在我心,他本或作“近在我形”。
[5]配以服食,雄雌设陈,挺除武都,八石弃捐:因配合有服食之说,故以雄、雌等文字来设定、陈述;然作者所谓“雄雌”,只是借之以明阴阳配合之妙,并非实指武都所产之雄黄、雌黄,故朱砂、硼砂、硇砂、雌黄、雄黄、硫黄、砒霜、胆矾之类的“八石”亦当弃去不用。服食,又名“服饵”,指服食金丹、药物以养生。道教认为,世间有某些物质,可以配合成丹或药物,人食之可以祛病延年,乃至长生不死;道士们在这种信念的驱动下,在实践中逐渐积累起一套采集、制作和服食金丹与药物的方术,此即是“服食”。一本作“伏食”,认为炼丹药物阴阳五行属性相克制为“伏”,药物五行相合、相吞为“食”。挺除,排除的意思。武都,古代地名,在今甘肃省,盛产雄黄;或谓炼药封闭鼎口时,常用武都山紫泥。八石,或谓即指朱砂、硼砂、硇砂、雌黄、雄黄、硫黄、砒霜、胆矾;一本作“五石”,即云母、礜石、磁、硫、雄黄之类。弃捐,舍弃,抛弃。他本或夺“配以服食,雄雌设陈”此二句。八石弃捐,他本或作“五石弃捐”。
【译文】
炼丹者务必要和顺阴阳之理,宣化、光耀其精神,如此则天地间阴阳不测之神机流转、变化,趋于圆通,如此便可以得己之身心与自然界万化的和谐与四海的安平。如果将此法则表现出来,依之推衍、制定历法,可以用万世之长久;依此法则来治理政事,亦可以使政事简易而不繁难、复杂。黄帝、老子法道之自然,将此法则引而向内,用于修身、养性,通过含养自己深厚的道德,保精惜炁,使其归藏于生命之本根,神明亦返还而居于其所当处之地。因此,此理实际上就近存于我们心中,不离于我们自己的身体;只要我们坚持此理,一以贯之而不舍弃,就可以获得长生久视之功效。因为此文中尚配合有服食之说,故行文时也以雄、雌等文字来设定、陈述;然作者所谓“雄雌”,只是借之以明阴阳配合之妙,并非指实为武都所产之雄黄、雌黄,故文中出现朱砂、硼砂、硇砂、雌黄、雄黄、硫黄、砒霜、胆矾之类的“八石”亦当如此处理,弃去不用。
审用成物章第九十
【题解】
本章阐明作者将此文命名为《参同契》的原因,认为《参同契》文辞虽简而寓意却很恢弘,含藏有真意于其中;后之学者遵之而行,可得安稳、长生。
很多注家认为,此段文字亦隐喻有《参同契》作者的姓名。
审用成物,世俗所珍;罗列三条,枝茎相连;同出异名,皆由一门;非徒累句,谐偶斯文;殆有其真,砾硌可观;使予敷伪,却被赘愆;命《参同契》,微览其端;辞寡意大,后嗣宜遵[1]。委时去害,依托丘山,循游寥廓,与鬼为邻;化形而仙,沦寂无声,百世一下,遨游人间;陈敷羽翮,东西南倾,汤遭厄际,水旱隔并;柯叶萎黄,失其华荣,吉人相乘负,安稳可长生[2]。
【注释】
[1]“审用成物”十六句:审察其理,用之而为炉火之术,则能变世银而为黄金,干水银而为白银,此黄白之术亦为世俗之人所珍重;作者于《周易参同契》中叙述大《易》之道、黄老养性、炉火服食,虽罗列有三件事,然三者之间其实枝茎相连、相络;道理可以前后贯通,皆同出于一门而异其名称而已;作者于此并不是想单纯累叠一些文辞,使辞句音声和谐,形式排比、对仗;应该看到,文中确确实实蕴藏有至真之理,此理明白显露,可以为人所理解;如果文中所叙说、陈述的皆是伪道理的话,作者愿意为此多余而无用的叙述承担罪责;文章既成,作者将之命名为《参同契》,于此中略微透露一些金丹大道的端绪;言辞虽寡,而其所承载之道、所蕴涵之意则实实在在是宏大的,后世有志于丹道者对之应当遵循、奉行。成物,物之成熟而可用。炼外丹不离铅金、流汞、火三物,三物共成还丹;还丹既成,则世俗之人以之为珍宝。三条,或谓指铅金、流汞、火;或谓指前文所言之青龙、白虎、朱雀,即木、金、火;或谓“三条”为精、炁、神;或谓指大《易》、黄老、炉火;或谓指前文所说“三五”;或谓指《周易参同契》上、中、下三篇;或谓即承上文所说大《易》、内养、服食三事,或养性、伏食、用物三事,等等。枝茎相连,指前文所说“三条”,即如大《易》、黄老、炉火等三者皆源出于一道,犹如草、木之枝茎、花叶、果实,三者皆与“道”这个根株之本相连贯。谐偶,“谐”有和谐、协调之意,指文中所用字词音相近或相同;“偶”有成双、成对出现,或双数的意思,此指文中所用辞句多有排比的用法。合而言之,指文中辞句音声和谐,形式排比、对仗。砾硌(lì luò),“砾”指小石块、碎石头,“硌”指山上的大石,“砾硌”指明白显露之意。敷伪,“敷”有铺开、摆开、涂抹之意,于此作“叙述”、“陈述”之意;“敷伪”即所叙说、陈述者皆是伪道理的意思。赘愆(qiān),“赘”有多余、无用之意,此处指多余而无用的叙述;“愆”指罪过、过失,合而言之,指因多余而无用的叙述而导致罪过、过失。审用成物,他本或作“审用成功”。同出异名,他本或作“俱出异名”。“使予敷伪,却被赘愆”二句,他本或作“使余敷伪,披却赘愆”。微览其端,他本或作“唯览其端”。
[2]“委时去害”十六句:修炼此金丹大法,当知全身、远害之道,故要不为时用,远离各种祸害,入山隐修,择地安居;游心于旷渺之乡,托志于虚无之所,与天地合德,与日月合明,与四时合序,与鬼神合其吉凶;返本还元而神灵莫测,脱尽阴质而形化为仙,隐身于大道寂寞之乡,不事声色、华音,长生久视,自在逍遥;然为济度群生,虽历百世之久,还当入俗济世,遍游人间,指示丹之玄要;丹道既成,服之便如云中之鹤,可以振翮高飞,羽化成仙;虽天倾西北,地缺东南,可一览而无余;又因能与天地同其长久,故尧之洪水、汤之旱灾,依世俗眼光看来虽悬隔久远,但得道之人任彼沧海桑田、历经陶铸而无变;历观草木枝茎花叶之荣枯而无倾危,因其得众仙真所扶持,故能安稳获长生久视之功。大多数《周易参同契》注本认为,此段话为廋辞、隐语,寓本书作者姓名于其中。如《道藏》所收托名汉阴长生所注《周易参同契》,提出虞翻认为“委”边着“鬼”是“魏”字。南宋储华谷注《周易参同契》,认为此段话实为“魏伯阳造”四字隐语,具体解说则见于其《前叙》,然《道藏》本储华谷注《前叙》缺失未收。宋末元初学者俞琰认为,此段话乃“魏伯阳”三字隐语,“委”与“鬼”相乘负为“魏”字;“百”之“一”下为“白”,“白”与“人”相乘负为“伯”字;“湯”遭旱而无水为“昜”,俞琰认为“湯遭厄际”句应为“湯遭阨际”,因为“阨”之厄际为“阝”;“阝”与“昜”相乘负为“陽”字。清陶素耜进一步认为,此段话隐“魏伯阳歌”四字。“魏伯阳”三字取俞琰之解;后四句,柯失华荣、去木成“可”;“乘”有相叠加之意,两“可”相乘为“哥”;“负”有“欠”之意,“哥”旁加“欠”为“歌”,而《周易参同契》本有“歌序大《易》”之说。清朱元育取南宋储华谷之说,认为“委时去害”以下四句,合成“魏”字;“化形而仙”以下四句,合成“伯”字;“陈敷羽翮”以下四句,合成“阳”字;“柯叶萎黄”以下四句,合成“造”字,言《周易参同契》全文乃魏伯阳所造。所谓“造”,可能取“人”字之上乘负有“告”则为“造”字,或“吉”乘“人”之上为“造”。当然,亦有人不持此立场。如清李光地即认为,“委时去害”以下,文不可解,如“陈敷羽翮,东西南倾”与前文“三者俱来朝”之意相仿佛;“汤遭厄际”与前文“九年被凶咎”之意相近;“柯叶萎黄”与前文“象彼仲冬节,竹木皆摧伤”之意相关,凡此皆丹经譬喻、取类之语。羽翮(hé),“羽”指鸟类或昆虫的翅膀,或指鸟的羽毛;“翮”指鸟羽的茎状部分,中空透明;亦指鸟的翅膀。东西南倾,或谓炼丹之旨,唯在使东木、南火、西金三物归于一家,如前篇“三者俱来朝”之说。而中国古代的一种地理观,则认为天倾西北、地缺东南。柯(kē)叶,“柯”指草木的枝茎,有时也指斧子的柄;此处“柯叶”指草木的枝茎花叶。吉人,得道的众仙、真人。委时去害,他本或作“委时去世”。化形而仙,他本或作“化形而亡”。百世一下,他本或作“百代一下”。“陈敷”,他本或作“敷陈”。东西南倾,他本或作“东西奔倾”。汤遭厄际,他本或作“尧汤厄际”、“阳遭厄际”、“汤遭阨际”。“吉人相乘负,安稳可长生”二句,他本或作“吉人乘负,安稳长生”、“各相乘负,安稳长生”。
【译文】
审察其理,用之而为炉火之术,则能变世银而为黄金,干水银而为白银,此黄白之术亦为世俗之人所珍重;作者于《周易参同契》中叙述大《易》之道、黄老养性、炉火服食,虽罗列有三件物事,然三者之间其实枝茎相连、相络;道理可以前后贯通,皆同出于一门而异其名称而已。作者于此并不是想单纯累叠一些文辞,使辞句音声和谐,形式排比、对仗;应该看到,文中确确实实蕴藏有至真之理,此理明白显露,可以为人所理解;如果文中所叙说、陈述的皆是伪道理的话,作者愿意为此多余而无用的叙述而承担罪责;文章既成,作者将之命名为《参同契》,于此中略微透露一些金丹大道的端绪;言辞虽寡,而其所承载之道;所蕴之意则实实在在是宏大的,后世有志于丹道者对之应当遵循、奉行。修炼此金丹大法,当知全身、远害之道。故要不为时用,远离各种祸害,入丘陵、山地隐修,择地安居;游心于旷渺之乡;托志于虚无之所,与天地合德,与日月合明,与四时合序,与鬼神合其吉凶;返本还元而神灵莫测,脱尽阴质而形化为仙,隐身于大道寂寞之乡,不事声色、华音,长生久视,自在逍遥;然为济度群生,得道之人虽历百世之久,亦应入俗济世、遍游人间,为后之学者指示丹之玄要;丹道既成,服之便如云中之鹤,可以振翮高飞、羽化成仙;虽天倾西北、地缺东南,亦可一览而无余;又因能与天地同其长久,故尧之洪水、汤之旱灾,依世俗眼光看来其时相隔久远,但得道之人任彼沧海桑田、历经陶铸而无变;历观草木枝茎花叶之荣枯而无倾危,因其得众仙真所扶持,故能安稳获长生久视之功。
附 录
鼎器歌
【题解】
五代彭晓将《周易参同契》并《补塞遗脱》四篇,共分为九十章,以应《周易》阳爻称九之数;另有《歌鼎器》一篇,也即《鼎器歌》,本来在《补塞遗脱》之前,彭晓认为其辞理钩连、字句零碎,故单独将其列出,放在他所整理的《周易参同契》三篇、九十章之后,以应五行生成之数的水一之数。
《鼎器歌》乃备言修丹之次第,总括《周易参同契》上、中、下三篇之要旨。
文章首言炼丹鼎器之法度、安炉立鼎之规模;次言炼丹阳火、阴符之运用,行持、用功之法则;再次则言升降玄牝、配合药物以结丹,以及结丹后的温养之功,于此当防护谨密,方能返本还源而丹渐长成;又言好道之士当寻究丹之根源,深藏其理,莫轻传妄泄;终则言道成丹就,则可以位列仙班,号称“真人”,如此则修炼之事方告圆满。
圆三五,寸一分[1]。口四八,两寸唇[2]。长尺二,厚薄匀[3]。腹齐三,坐垂温[4]。阴在上,阳下奔[5]。首尾武,中间文[6]。始七十,终三旬;二百六,善调匀[7]。阴火白,黄芽铅[8]。两七聚,辅翼人[9]。赡理脑,定升玄;子处中,得安存[10]。来去游,不出门;渐成大,情性纯[11]。却归一,还本原[12]。善爱敬,如君臣;至一周,甚辛勤;密防护,莫迷昏[13]。途路远,复幽玄;若达此,会乾坤[14]。刀圭霑,静魄魂[15]。得长生,居仙村;乐道者,寻其根[16]。审五行,定铢分[17]。谛思之,不须论;深藏守,莫传文[18]。御白鹤兮驾龙鳞,游太虚兮谒仙君,录天图兮号真人[19]。
【注释】
[1]圆三五,寸一分:自外丹言之,炼丹鼎器的腹圆之处,围成一周有一尺五寸的周长,其径则为五寸,圆三径一,故称“三五”;鼎器之壁其厚则为一寸一分,或谓“寸一分”指鼎器之口阔一寸一分。或谓此即炼外丹之太一炉,其炉周圆一尺五寸,中虚五寸,厚一寸一分。鼎居上,形圆而象天;鼎下为炉灶,炉灶呈方形而象地,鼎、炉与一般做饭的锅、灶其形相似,锅亦圆而居上、灶则呈方形而处下。自内丹言之,“三五”指圆三径一,喻人身中之丹田、宝鼎。精、神、魂、魄、意此五者在人身之中,常常容易分散而不聚集,导致其亏折损耗、丧失殆尽,必收敛、攒簇,使之归于丹田、宝鼎。修炼者变自身精、神、魂、魄、意五行为“三五”,所谓“三五”,指东三之木、南二之火,此为“一五”,喻人之魂与神;中宫之五,喻脾土真意,此为“二五”;北一之水、西四之金,喻人之魄与精,此为“三五”;精、神、魂、魄、意归于丹田圆熟、固结,外无所摇、内无所役,复还太极之圆融,也即合此“三五”于太极“〇(原文此处为圆圈)”之中,如此则圆成、圆满。太极即所谓“天心”,虚而中正,范围不过径寸;然亦只借此以显明太极、天心而已,论太极、天心之大,其可以弥纶、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,论其小则退藏于秘,视之不见、听之不闻、搏之不得,故实无所谓径寸、范围之可言。三五,外丹指鼎身周围一尺五寸;内丹则以之象“三五”之数。《周易·系辞》谓:“参伍以变,错综其数,通其变,遂成天下之文。极其数,遂定天下之象。非天下之至变,其孰能与于此!”故《周易参同契》多次言及“三五”,如“三五既和谐”、“三五与一,天地至精”、“三五不交,刚柔离分”、“本之但二物,末而为三五”,如此等等。圆三五,他本或作“围三五”。寸一分,他本或作“径一分”,因鼎圆之围为三五,则其径长为一五,故说“圆三五,径一分”。
[2]口四八,两寸唇:自外丹言之,鼎器之口向上张开如锅,其周长为一尺二寸;鼎口之上覆压有鼎盖,鼎盖与鼎口相接之处为鼎之唇吻,唇之厚为二寸。或谓炼丹之鼎炉从鼎口之上至于炉器之下,其距离有一尺二寸;鼎唇厚二寸,如两层之状,象乾坤两仪橐籥之形,亦如人有上下两重之唇。或谓炼丹鼎炉,圆者为乾鼎,方者为坤炉;炉方形而周长八寸,则其四边径长各为二寸,即所谓径一而围四,二四得八,故说:“口四八,两寸唇。”或谓鼎器乃贮藏丹药之所,故有药之入口处,其入口外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象具于内,而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八卦环列其外,故说“口四八”;鼎既然有口,必有其唇,上下二唇以象阴阳两仪,唇厚二寸,故说“两寸唇”。自内丹言之,“口”主吐纳,“唇”主阖辟,皆通气之处,此可喻指内丹的玄关或玄牝之门;“四”与“八”得十二,可喻一日之十二时辰、一年之十二月等等。玄关出入、吐纳,一呼一吸、一阖一辟,当与十二时、十二月阴阳消长之节序相合;然究其实,则不过与阴阳升降之序相合,故“两寸”即喻阴阳而已。或谓“两寸唇”,即阴阳二气的界分,如同前文所说的“玄沟”或“互沟”;四象、八卦合之为十二,鼎口周围一尺二寸,以象精、炁与神一日十二时循环身中十二位,皆以丹田、鼎口而为其根基。
[3]长尺二,厚薄匀:自外丹言之,炼丹之鼎通身高为一尺二寸,鼎上下厚薄均匀,不可使其有偏颇不均之处。或谓鼎长一尺二寸,以应一年十二月周天火候;自农历十一月鼎底阳生一寸,至一周年则阳火满鼎;鼎上下厚薄均匀,则表示安炉立鼎无偏颇不均之处。或谓“长”即“常”,“二”即阴阳二气,“长尺二”言鼎器中阴阳二气之往来实乃鼎器功能之常态,气之轻清而浮者为阳为薄,气之重浊而沉者为阴为厚,“厚薄匀”即喻鼎中药物阴阳浮沉相均平之意。自内丹言之,“长尺二”即十二寸,可以喻一年之十二月、一日之十二辰、《易》之十二辟卦、历之十二律吕;炼丹火候,从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至于巳为六阳,乃进火之候;从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至于亥为六阴,乃退火之符;阴阳火符刚柔不偏、寒暑合节,即所谓“厚薄匀”,如前文所说“周旋十二节,节尽更须亲”。或谓此言精、炁于一身中运行之节度,后自尾闾升而至于头顶泥丸,历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六宫,前自泥丸降归下丹田土釜,分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六宫,则精、炁循环运转于一身,分历十二节点。厚薄匀,“厚”指多,“薄”指寡,“匀”即均平,指调停六阴、六阳火候,使之配合均匀,以内丹修炼来说,则念不可起,意不可散,念起则火燥,意散则火寒。或谓心神与精、炁相融,神随精、炁而动,纯一不杂,无有妄念,亦无厚此薄彼之区分,保持其均匀、均平。长尺二,他本或作“长二尺”。厚薄匀,他本或作“厚薄均”。
[4]腹齐三,坐垂温:自外丹言之,炼丹前要安炉置鼎,于鼎器的腹部外面、上下居中的部位,安装三个圆孔,使之在同一圆周面上,三个圆孔彼此间距离相齐整、阔狭相均匀;然后,以铁穿入圆孔之中,将之固定而为鼎器之足;空中悬物谓之“垂”,鼎器于炉中,当悬之而不使之接触到地面;因鼎之三足固定,如此则进火之际,鼎器不至于因药物沸腾、翻滚而摇动。或谓鼎器自鼎口、鼎腹至于鼎底上、中、下皆要均匀、通直;鼎悬于炉灶之中,要使之不接触到地面,此即所谓“悬胎鼎”。或谓安置鼎器需要平正,要使鼎口齐鼎心,鼎心齐鼎腹,三者既齐,鼎器始无倾侧之患。自内丹言之,修行之人于静坐之时,以眼对鼻,以鼻对脐;三者既齐,则身平正而不倚侧;此谓“腹齐三”;眼要垂帘,息要深长而不可粗短,息粗则意念杂乱、纷飞,如此则火炽而药不凝结;通过凝神、静心,温温之阳炁、真种于玄关之内便能生成、发动,此谓“坐垂温”。或谓“齐”即“脐”字,“腹齐三”在人身为腹脐下三寸或腹里脐中三寸,此乃阳炁发动之所,即通常所说的下丹田,丹经或谓之玄牝之门或玄关;所谓“坐垂温”,指收心静坐,目光垂帘、内照,守中温养,用火不必太猛,也即意念不能太紧,当绵绵若存、用之不勤,以保持丹鼎温温。或谓鼎“腹”乃贮药之所,内丹喻指丹田;“三”喻指精、炁、神上药三品,“腹齐三”喻指鼎腹之内精、炁、神三药齐备;“坐”指安其位而不动不摇,“垂”指眼目垂帘,“温”即精、炁、神冲和而凝聚一处,一意不散则腹内温温而真种产生。或谓“腹”即丹田内室,“三”指月初三日一阳生之时,“齐”指身内一阳之生与月初三生明其理相齐;“坐”有坐待之意,“垂”有至之意,“温”有阳炁发动之意,修行人静而坐待身内阳炁之发动,阳炁动则急采之而炼丹。或谓修行人凝神于腹内玄关、一窍空洞而无涯;如此则神与炁、精相会于中宫,三家相见,此谓“腹齐三”;当其交会之时,修行人勿忘勿助,候其神明自来,如此则神与炁、精调燮得中,方觉丹田温温然而真种发生,此谓“坐垂温”。腹齐三,他本或作“腹三齐”、“腹齐正”。
[5]阴在上,阳下奔:以外丹言之,鼎器居上,药物则安处鼎中,此谓“阴在上”;欲运火以炎上鼎,当使炉火居鼎之下,此谓“阳下奔”。或谓“阴在上”,指鼎器中注入水;“阳下奔”指鼎器下有火,通过密塞炉缝,则炉火之焰沿悬胎鼎往下奔。自内丹言之,精、炁之水本润下,逆而使之升华,此谓“阴在上”;思虑之神火纷杂,外逸而炎上,当使其凝而在内,思不出其位,如此则炎上之火降而入于炁海,此谓“阳下奔”,合于《周易》“水火既济”之旨。或谓心中扫除嗜欲,归于虚静,此为“阴在上”;下丹田聚集阳所,厚其发生,此为“阳下奔”,合于《道德经》“虚心实腹”之义。
[6]首尾武,中间文:自外丹言之,炼丹之初及丹成之终,皆要用大火,也即武火;中间则用小火,也即文火。外丹煅炼之时,拉动风箱,加足煤炭,火旺而盛,即为武火;不动风箱,炉中火力平和,即为文火。或谓首、尾即月之晦、朔,中间喻指月望之时。晦、朔乃阴极阳生之时,故用武火;月望乃阳极阴生之时,故用文火。或谓进阳火,则子、丑、寅为首,辰、巳为尾;退阴符,则午、未、申为首,戌亥为尾;首尾俱用武火,至中宫沐浴,即卯、酉之时则用文火。或谓巳、午是阴阳二气之分界,巳为阳气之尾,午为阴气之首,故用武火;至于巳、午两向的中间也即卯、酉之时,则阴阳进退,各得其中,故用文火。或谓子时为阴之尾、阳之首,午为阳之尾、阴之首,俱用武火;唯中间卯、酉之时沐浴,则用文火。自内丹言之,火不离神与炁,其可以药言,亦可以火言;于呼吸之中,必有事焉、存意用心为武火,安静无心、勿忘勿助长为文火;打起精神、驱除杂念为武火,温温不绝、绵绵若存为文火。首为始生而未旺,尾为既旺而将衰,此时用武火;中间为旺时,安静无为、慎防其旺,故用文火;武火主烹炼,文火主沐浴。此与前文所说“始文使可修,终竟武乃陈”不同。因古丹经向来传药不传火,火之不传实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所致;故火虽有赖于师传,然亦要修炼者自己根据情况作出调整。
[7]始七十,终三旬;二百六,善调匀:自外丹言之,炼丹之初,七十日皆用武火;炼丹之终,三十日还用武火;中间的二百六十日,则用文火。一个太阴历年,通计三百六十日,文、武火候要如此调匀。自内丹言之,七十、三十合而为一百,一百与二百六十合之则为三百六十,应一年周天之数。修行人通过百日筑基,则灵胎始结;灵胎既结,此后二百六十日要善于调匀火候,常使丹田之内暖气不绝,则丹功自成。或谓内丹以炼己为始,因人心放荡已久、积习已深,最难降伏,故炼己之初以武火居多;及灵丹已结,则以文火养之;养之既久,至于丹成,于此当防危虑险,稍有懈怠,则成而复败,故亦当用武火。或谓一年三百六十,首尾除去七十、三十,余二百六十;二百六十日再分成首尾两个一百与中间一个六十,前一个一百与此前的七十合为一百七十,后一个一百与后之三十合为一百三十,合计为三百,比喻灵丹十月胎圆之期。中间尚余六十日,比喻卯、酉两月,应春分、秋分沐浴火候。三旬,一旬十日,“三旬”则三十日。所谓“调匀”,即令火候不寒不温,调和得中;此时,念不可起,意不可散。善调匀,他本或作“善调均”。另外,一本或夺此四句。
[8]阴火白,黄芽铅:自子至巳为阳火之候,自午至亥为阴火之候。炼丹时,一般先以武火煅炼铅,使铅熔化成液;再加进汞,汞之色白,其性活跃,此时一般要改以文火,也即阴火烹炼,此即“阴火白”;铅、汞相化合,结成“黄芽”,“黄芽”乃铅中所出,铅乃黄芽之母,故说“黄芽铅”。自内丹言之,离中真汞也即后天识神中所现清静元神,谓之“阴火”,又号称“白雪”;坎中真铅也即后天之精的根基——先天元精、元炁,谓之“黄芽”。丹头和合之际,用清静元神之火烹炼有“黄芽”之称的先天元精、元炁,虚室生白,故说“阴火白,黄芽铅”。或谓欲产“黄芽”之药,修行人当以己本性中一点虚灵之神火注入坤腹下丹田之内,如《悟真篇》所说“蟾光终日照西川”,因为后天八卦方位中,坤居西南,“西川”可喻坤腹;又西川属金方,五行金之色白;而“蟾光”指月亮之光,其光较弱,不及太阳,故以“蟾光”喻绵绵若存之“文火”、“阴火”,故说“阴火白”;久之则精、炁与神氤氲自结,黄婆真意呈现,坎中真铅即先天一炁自得,此即“黄芽铅”的一种解释。黄芽铅,他本或作“黄牙铅”。
[9]两七聚,辅翼人:自外丹言之,东方青龙七宿之气与西方白虎七宿之气也即铅与汞合聚,辅翼而生成丹胎;丹胎以“真人”为喻。自内丹言之,“两七”喻指东方苍龙七宿也即魂、性、神等,西方白虎七宿也即魄、精炁、情等;《易》三才之道,中央为“人”之位。“两七聚,辅翼人”即龙蟠虎跃,龙虎会聚于中宫黄庭,于中宫结成玄珠宝象,也即魂与魄,精、炁与神,性与情相融、相合,于中宫黄庭结成灵丹。“两七聚”喻青龙七宿之气与白虎七宿之气即铅与汞合聚,如《周易参同契》下卷八十二章所说:“青龙处房六兮”、“白虎在昴七兮”。或谓“两七聚”为以硇砂密固鼎器之口,如此,则鼎中铅金、流汞不至于飞走。内丹则以“两七”喻指东方苍龙七宿也即魂、性、神等,西方白虎七宿也即魄、精炁、情等。或谓此以五行生成之数言“两七聚”,如地二生火,天七成砂,此阴火成数是为“一七”;天一生水,地六成铅,此黄芽之合数是为“一七”,以铅、火之数合,则为“二七”。或谓肾位居脊柱第七椎,心在头项之下第七椎,“两七聚”或即言心肾交媾之义。辅翼人,因为炼丹之鼎器亦法《易》天、地、人三才之道,其中,鼎器圆而居上为天,炉灶方而居下为地,药居鼎器神室中宫喻人;铅、汞辅翼而生成丹胎,丹胎以“真人”为喻,如《周易参同契》中篇六十六章:“真人潜深渊,浮游守规中。”内丹借《易》三才之道中央为“人”之位,以“人”喻灵胎处中宫黄庭。辅翼,有辅助、羽翼之意。人,即丹之圣胎,以“真人”为喻;或谓“辅”有辅助之意,“翼人”即成仙之“真人”。两七聚,他本或作“两七窍”。
[10]赡(shàn)理脑,定升玄;子处中,得安存:自外丹言之,以理石、石脑、硇砂等密固鼎器,药物得火烹炼,一定会在鼎器中升华、发生玄妙的化合反应;药所凝结成的丹胎定会居处于鼎器之中,优游而安存。自内丹言之,大药初生,产在坤腹下丹田;及其烹炼,却须上升至乾鼎也即头顶之上丹田,脑为上丹田之所在,人身之百脉总汇于此,此即“还精补脑”之功。一般说来,时至机发则药生;药生之时,还要以真意采之,以神照顾,令其升而至于上丹田,因为脑为人的元神所居之宫,人能藏元神于内,使之安栖于本宫,则下丹田之精、炁自然能升而上,“还精”以“补脑”,如此,则一窍开而百窍齐开,大关通而百关尽通,此即“赡理脑,定升玄”。精、炁与神于上丹田交媾之后,旋即降下中宫黄庭,归于下丹田温养,其状若赤子处胞中,优游而安存。赡,丰富、充足之义;一本作“缮”,有修补、修缮之义。脑,外丹以之为理石、石脑之类的矿石、药物;内丹以之为头顶泥丸之宫。子,外丹以之为外药之丹胎;内丹则以之为精、炁与神所凝结之圣胎。赡理脑,他本或作“缮理脑”、“瞻理脑”。
[11]来去游,不出门;渐成大,情性纯:自外丹言之,因为鼎器坚固、密闭,故铅、汞等药物得火之烹,变而成液,来来回回,优游于鼎器之中,而不至于溢出于鼎器之外;铅金、流汞渐凝渐结,变化而成纯质之大还丹。自内丹言之,“门”指玄牝之门、玄关;“来去游”喻指呼吸之往来,往来之息皆不离玄牝之门,则息息归根,阴阳炁足而发起神妙变化;开始时,只一黍之珠,修行之人不论行、住、坐、卧,皆绵绵若存,则日复一日,渐凝渐聚,从微至著,充实长大,如此则婴儿显相,情返为性,纯粹至精,愈加纯熟。或谓修行人闭固微密,使无漏泄之虞,则圣胎渐大而情性愈纯。或谓此指丹道之“初阳神”,其初阳神不能轻出,恐其迷失故宅;待其渐渐长大,性情纯一,本身坚固,方许远游。渐成大,他本或作“渐成土”。情性纯,他本或作“性情纯”。
[12]却归一,还本原:自外丹言之,丹之基为金,金性长久而不朽;宇宙开辟后,金性则散在万物之中;通过炼铅、汞等药物,得其纯粹不朽之金性,是谓金丹,也称“还丹”,如此则归一而还元,故说“却归一,还本原”。自内丹言之,丹之真种乃自无极、太极中来,本为一物,分而为阴阳则成二,阴阳冲和则为三,再分则有四象、五行,此在丹家看来,乃降本流末、顺而生物之道。修丹之法,在于交媾阴阳,会合三家,和合四象、五行,通过抱元守中,返本、还元,复归于一,至于混沌之太极、无极,此谓“却归一,还本原”。一,道之根源,道之本源。还本原,他本或作“还本源”、“还本元”。
[13]善爱敬,如君臣;至一周,甚辛勤;密防护,莫迷昏:自外丹言之,还丹之功,历一周年方完成,在这个过程中,对于鼎室中的丹胎,要如君爱、臣敬一般珍惜、爱护;一年之中,修丹人要昼夜辛勤、防护,使鼎器固济、坚牢,不能有所懈怠。自内丹言之,圣胎既结,还须温养,一年火候甚是辛勤;在这个过程中,修行人夙夜不能懈怠,对所结之圣胎,尤宜密加防护,要如君爱、臣敬般对待之,抽添运用,昼夜防危,百刻之中,无有间断,如此则修炼之士神常惺惺而不迷昏,从而能有效防止走失。然于勤苦之中又当不勤,只是悠闲养己之元神。君臣,君爱与臣敬相应,爱属阳舒、敬属阳敛,与前文之“喜怒”皆养丹之法。内丹则以先天祖炁为君,以后天精、炁为臣;鼎中先天祖炁既得,要以后天精、炁哺乳、护卫之,彼此之间相得益彰。“善爱敬,如君臣”二句,他本或夺此两句。
[14]途路远,复幽玄;若达此,会乾坤:丹炼须九转,从百日筑基至十月结胎,从三年哺乳至九年丹成,路途漫长而悠远;其间终始变化,其理幽微、玄深;若能明了丹道此理,用之于实践,则能和合阴阳,从而乾坤在手、日月在心。自内丹言之,欲使身内精、炁与神和合,运转于头顶昆仑与海底会阴之间,其后有尾闾、夹脊与玉枕三关,前有上、中、下三丹田及十二重楼之喉管,故其途路艰辛而玄远;修行之人于杳冥恍惚之时,神与精、炁相抱,其大无外,其小无内,迎之不见其首,随之不见其后,其境界极为幽玄而神妙。若能达此境界,则可以颠倒阴阳,和合自身之乾坤,而盗天地之化机。或谓大道幽深而玄妙,难以一蹴而就,故修道之程期亦无定数,唯在修行人自己之勤与怠。若能通达丹道内修之理,则可以会乾、坤为鼎器,合坎、离为药物,烹炼成丹。复幽玄,他本或作“极幽玄”。
[15]刀圭(guī)霑(zhān),静魄魂:自外丹言之,金液还丹既成,取一刀圭服下,丹稍微与体内五脏相沾,人即神明气清,魂安魄静,改换肉体凡骨,变化而为仙真。自内丹言之,还丹入口,只须一刀圭,则阴魄尽消,阳魂亦冥,虎伏而龙降。如前文所说“休死亡魄魂”、“刀圭最为神”。刀圭,原为中药的量器之名,如晋葛洪《抱朴子·金丹》有:“服之三刀圭,三尸九虫皆即消坏,百病皆愈也。”此所谓“刀圭”,即量药之具;《本草纲目·序例》引南朝梁陶弘景《名医别录·合药分剂法则》说:“凡散云刀圭者,十分方寸匕之一,准如梧桐子大也……一撮者,四刀圭也。”认为“一刀圭”约如一个梧桐子大小的量;或谓“刀圭”即一黍或一稻米之量,或刀头、圭角一些子之义;或谓“刀圭”即汤匙,如近人章炳麟于《新方言·释器》中说:“斟羹者或借瓢名,惟江南运河而东,至浙江、福建数处,谓之刀圭,音如条耕。”“刀圭”亦可指药物本身,如唐王绩《采药》诗云:“且复归去来,刀圭辅衰疾。”或谓“刀圭”,即丹头。霑,稍微碰上或挨上一点。刀圭霑,他本或作“片子霑”。静魄魂,他本或作“净魄魂”。
[16]得长生,居仙村;乐道者,寻其根:服食金丹,可以得长生久视,居仙村、位列仙班之效;因此,那些好道、乐道之士,要寻究金丹、神药之根源而炼之,勿误用杂类之物。内丹则认为,此所谓“根”,乃丹之基、天地之根;乐道、好道之士,有能寻而得此,则何其幸甚!“得长生,居仙村”二句,他本或夺此两句。
[17]审五行,定铢分:凡修金液还丹,要审察药物之五行,分析、区别药物用量之铢两,通过探究药物阴阳之情性,明阳火、阴符之火候,方能得药物阴阳相配、五行互用,配合成丹。金液还丹,非阴阳五行、真铅真汞,合和成药,没有其他路径可走。自内丹言之,五行顺则生人,逆则成丹,其法度不可不审察清楚。故好道参玄之士当审五行之细微,定药物铢两之轻重,如火数盛则燥,水铢多则滥,若铢两分数一错,定不结丹。五行,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;内丹通常以精、神、魂、魄、意为五行。铢,古代重量单位,二十四铢等于旧制一两;一斤为十六两,为三百八十四铢;此亦可以应《易》之三百八十四爻。
[18]谛思之,不须论;深藏守,莫传文:对于此丹道之理,修炼者当精研覃思,但勿轻易论说之;要将之深藏于书箧之中,或缄藏于己心之内,不要妄自传文与非道之人,导致轻慢泄漏天机。然正如《道德经》七十九章所说: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”道何尝远人,人自远道罢了。谛,仔细之义。
[19]御白鹤兮驾龙鳞,游太虚兮谒仙君,录天图兮号真人:丹成之后,功德圆满,此时的境界,犹如跨上白鹤,乘上飞龙,游于太虚清静之境,拜谒得道之仙君;从此膺箓受图,位证大罗天仙,而有真人之号。自内丹言之,胎圆功成之后,可以调神出壳,从此逍遥快乐,与天地同其长久,而号称为“真人”。当然,所谓龙、鹤,实乃自身之元精、元炁;所谓“太虚”,即自己的玄关虚无之窍,或谓玄牝之门;“仙君”即自己清静之元神,“真人”即自己的本来面目。若不知积功、累行,只是妄想求真,昼夜翘思而待天诏,则流于荒谬。御白鹤兮驾龙鳞,他本或作“御白鹤兮驾龙麟”。游太虚兮谒仙君,他本或作“游太虚兮谒元君”。
【译文】
炼丹鼎器的腹圆之处,围成一周有一尺五寸的周长,其径则为五寸,圆三径一,故称“三五”;鼎器之壁其厚则为一寸一分,故说“寸一分”。鼎器之口向上张开如锅,其周长为一尺二寸;鼎口之上覆压有鼎盖,鼎盖与鼎口相接之处为鼎之唇吻,亦如人有上下两重之唇,唇之厚为二寸。炼丹之鼎通身高为一尺二寸,鼎上下厚薄均匀,不可使其有偏颇不均之处。炼丹前要安炉置鼎,鼎器被安置于炉中加热时,当悬之而不使之接触到地面;鼎口与鼎心齐、鼎心与鼎腹齐,三者既齐,鼎器始无倾侧之患。鼎器居上,药物则安处鼎中,此谓“阴在上”;欲运火以炎上鼎,当使炉火居鼎之下,此谓“阳下奔”。炼丹之初及丹成之终,皆要用大火,也即武火;中间则用小火,也即文火。具体说来,炼丹之初的七十日皆用武火,炼丹之终的三十日还用武火,中间的二百六十日则用文火;一个太阴历年,通计三百六十日,文、武火候要如此调匀。炼丹时,通常先以武火煅炼铅,使铅熔化成液;再加进汞,因汞性活跃,此时一般要改以文火,也即阴火烹炼,因汞之色白,此即“阴火白”;铅、汞相化合,结成“黄芽”;“黄芽”乃铅中所出,铅乃黄芽之母,故说“黄芽铅”。丹砂与汞以东方青龙七宿喻之,铅则以西方白虎七宿喻之,铅与汞合聚,辅翼而生成丹胎;丹胎以“真人”为喻。以理石、石脑、硇砂等密固鼎器,药物得火烹炼,在鼎器中升华、发生玄妙的化合反应;药所凝结成的丹胎居处于鼎器之中,优游而安存。因为鼎器坚固、密闭,故铅、汞等药物得火之烹,变而成液,来来回回,优游于鼎器之中,而不至于溢出于鼎器之外;铅金、流汞渐凝渐结,变化而成纯质之大还丹。金性长久而不朽,宇宙开辟后,金性则散在万物之中;通过炼铅、汞等药物,得其纯粹不朽之金性,是谓金丹,也称“还丹”,如此则归一而还元,故说“却归一,还本原”。还丹之功,历一周年方完成,在这个过程中,对于鼎室中的丹胎,要如君爱、臣敬一般珍惜、爱护;一年之中,修丹人要昼夜辛勤、防护,使鼎器固济、坚牢,不能有所懈怠。丹炼还须九转,其路途漫长而悠远;其间终始变化,理实幽微、玄深;若能明了丹道之理,用之于实践,则能和合阴阳,从而乾坤在手、日月在心。金液还丹既成,取一刀圭服下,丹稍微与体内五脏相沾,人即神明气清,魂安魄静,改换肉体凡骨,变化而为仙真。因服食金丹,可以得长生久视,居仙村、位列仙班之效,故那些好道、乐道之士,当寻究金丹、神药之根源而炼之,切勿误用杂类之物。凡修金液还丹,要审察药物之五行,分析、区别药物用量之铢两,通过探究药物阴阳之情性,明阳火、阴符之火候,方能得药物阴阳相配、五行互用,配合成丹。对于此丹道之理,修炼者当精研覃思,但勿轻易论说之;要将之深藏于书箧之中,或缄藏于己心之内,不要妄自传文与非道之人,导致轻慢泄漏天机。丹成之后,功德圆满,此时的境界,犹如跨上白鹤,乘上飞龙,游于太虚清静之境,拜谒得道之仙君;从此膺箓受图,位证大罗天仙,而有真人之号。
赞 序
【题解】
此章乃《周易参同契》之《赞序》。朱熹认为,此《赞序》可能是后人注《周易参同契》所作之《序》,注亡而《序》存。因彭晓《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·序》中提及,魏阳伯作《周易参同契》,密示青州徐从事,令其笺注,徐隐名而注之,至东汉桓帝时,复传授于同郡淳于叔通,《周易参同契》得行于世。故朱熹等推断此《赞序》可能是徐从事之语,其注已不复存,仅留有此篇《赞序》。此可备一说。
《赞序》一章赞《周易参同契》之为书,辞虽简而道却深,其理合于天地自然之法则、日月运行之盈亏;循其道、理而行,御政可得太平,修身养性可得长生久视;若不循其度,则御政、内养、服食三者皆废,故后之贤达当悉心留意此书。
《参同契》者,辞隐而道大,言微而旨深;列五帝以建业,配三皇而立政[1]。若君臣差殊,上下无准;序以为政,不至太平;服食奇法,未能长生;学以养性,又不延年[2]。至于剖析阴阳,合其铢两,日月弦望,八卦成象,男女施化,刚柔动静,米盐分判,以经为证,用意健矣[3]!故为立法,以传后贤;惟晓大象,必得长生;为吾道者,重加意焉[4]。
【注释】
[1]《参同契》者,辞隐而道大,言微而旨深;列五帝以建业,配三皇而立政:《周易参同契》这部经书,其所用辞语非常隐晦,但其所承载之道则非常宏大;其所用皆含畜、微妙的言辞,然所述之理则非常精深、切要;其可以与“五帝”所建立的功业相并列,与“三皇”所确立的政治相匹配。五帝,指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五位圣明君主。《大戴礼记》、《史记》认为“五帝”指的是: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;《战国策》认为“五帝”指的是:庖牺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;《吕氏春秋》认为“五帝”指的是:太昊、炎帝、黄帝、少昊、颛顼;《资治通鉴外纪》认为“五帝”指的是:黄帝、少昊、颛顼、帝喾、尧;《尚书序》认为“五帝”指的是:少昊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,这种说法比较流行。三皇,指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三个圣王,通常指燧人氏(燧皇)、伏牺氏(羲皇)、神农氏(农皇)或天皇、地皇、人皇。一种说法以“三皇”为:伏牺、神农、黄帝,如《庄子·天运》说:“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。”成玄英对此疏曰:“三皇者,伏牺、神农、黄帝也。”一种说法以“三皇”为:伏牺、神农、女娲,如《吕氏春秋·用众》:“此三皇、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。”高诱注此说:“三皇,伏牺、神农、女娲也。”一种说法以“三皇”为:伏牺、神农、燧人,如汉班固《白虎通义·号》:“三皇者,何谓也?谓伏牺、神农、燧人也。”另外,《白虎通义·号》又云:“《礼》曰:伏牺、神农、祝融,三皇也。”则又提出“三皇”为:伏牺、神农、祝融。一说“三皇”指:天皇、地皇、泰皇,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说:“古有天皇、有地皇、有泰皇。泰皇最贵。”一说“三皇”则指:天皇、地皇、人皇,如《艺文类聚》卷十一引《春秋纬》:“天皇、地皇、人皇,兄弟九人,分九州,长天下也。”辞隐而道大,他本或作“辞陋而道大”。
[2]若君臣差殊,上下无准;序以为政,不至太平;服食奇法,未能长生;学以养性,又不延年:如果不循《周易参同契》之法度,则阴阳不能和谐,这在政治上表现为君主与臣民的意见差异很大、上下不一致,若用此以指导政事,就不可能达到天下太平;炉火炼养与修身养性亦同此理,若烧炼外丹失其阴阳相和之法度,所用之法奇怪而异于常道,服食这种外丹就不能获得长生久视之效;若阴阳失和,以之修身、养性,亦不能达到长寿、延年的目的。服食奇法,他本或作“服食其法”。
[3]“至于”九句:至于《周易参同契》这部经书,剖析天地阴阳之理,配合丹道炉火阴阳药物的剂量之数,取法日月运行、弦望盈宿的阴阳进退、消长之则以为火候,并取八卦阴阳刚柔之卦象、爻意佐证其理;乃至所谓男女阴阳施化之情,阳刚而动、阴柔而静之理,皆如白米与青盐分判那般清楚、明白,皆可以《周易》等经典之义为其印证,故此书之用意,真可谓雄健而坚实啊!以经为证,他本或作“以《易》为证”。
[4]故为立法,以传后贤;推晓大象,必得长生;为吾道者,重加意焉:《周易参同契》所建言立论,实包含天道自然、御政太平、修身养性、炉火服食之理,因此之故,当为其立法、将之留传后世贤达之人。后之学者只要能推阐、通晓其大象中所蕴无形之妙理,必可获长生久视之功效!希望那些与我同爱此道的人,一定要重视此书,对之悉心留意、研读!立法,朱熹认为当作“立注”,可能因传抄、转写而误作“立法”。故为立法,他本或作“故为立注”。推晓大象,他本或作“惟晓大象”。“必得长生”后,他本或衍“强己益身”一句。为吾道者,他本或作“为此道者”。
【译文】
《周易参同契》这部经书,其所用辞语非常隐晦,但其所承载之道则非常宏大;其所用皆含畜、微妙的言辞,然所述之理则非常精深、切要;其可以与“五帝”所建立的功业相并列,与“三皇”所确立的政治相匹配。如果不循《周易参同契》之法度,则阴阳不能和谐,这在政治上表现为君主与臣民的意见差异很大、上下不一致,若用此以指导政事,就不可能达到天下太平;炉火炼养与修身养性亦同此理,若烧炼外丹失其阴阳相和之法度,所用之法奇怪而异于常道,服食这种外丹就不能获得长生久视之效;若阴阳失和,以之修身、养性,亦不能达到长寿、延年的目的。《周易参同契》这部经书剖析天地阴阳之理,配合丹道炉火阴阳药物的剂量之数,取法日月运行、弦望盈宿的阴阳进退、消长之则以为火候,并取八卦阴阳刚柔之卦象、爻意佐证其理;乃至所谓男女阴阳施化之情,阳刚而动、阴柔而静之理,皆如白米与青盐分判那般清楚、明白,皆可以《周易》等经典之义为其印证,故此书之用意,真可谓雄健而坚实啊!《周易参同契》所建言立论,实包含天道自然、御政太平、修身养性、炉火服食之理,因此之故,我当为其立法,将之留传后世贤达之人。后之学者只要能推阐、通晓其大象中所蕴无形之妙理,必可获长生久视之功效!希望那些与我同爱此道的人,一定要重视此书,对之悉心留意、研读!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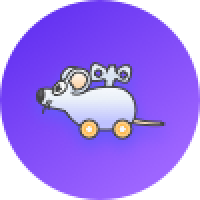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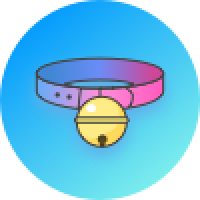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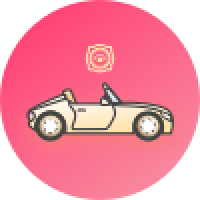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